这是 Summertime 的第 28 篇 闲情译事
时隔四年 决心重启这个专栏
自由译员的工作
让我认识了许多令我敬仰 和发自内心喜欢的同行
迫不及待地想请他们来书写自己
分享翻译故事 和不同的人生解法
隔周周日 不见不散
本期作者:提亚
某外事单位工作者
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学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文学学士
小红书:@提亚的书库
我小学时就喜欢英语了。不过更准确的说法是,相较于其他科目,我小时候学英语更不费力。这一“成就”助长了我在英语方面的自信心,其影响悄然延续至往后的漫长岁月里。
初、高中虽然学英语需要费点劲了,但是英语仍旧是我最骄傲的科目。高考后我坚定地选择英语作为本科专业也好像是当时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当时的四个志愿批次学校的专业序列上,我填报的第一专业全部都是英语。是的,我甚至根本不在乎英语是不是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也不在乎自己的分数是不是可以读更吃香的专业。典型的“有情饮水饱”(笑)。一路到研究生——意料之中的,读的也是与英语强相关的口译。
这个过程称得上典型,很多同僚可能也是这样满怀热爱地走向口译的。在我找到跟口译相关的工作后,我曾暗暗想,这份热爱可算瓜熟蒂落了。
这种“痴情”是一种幸运吗?毕竟很多人会觉得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是很幸福的。可能是吧。我也确实怀抱这种绝对的意义感充实快乐地度过了一段时间,我努力求学,努力工作。这期间,翻译带给我无数关于心流、交流、成长的喜悦时刻,这种热爱慢慢称为我的生活、我的自我的一部分。
一些口译笔记
驱动我们选择某条路的不是冲动,更不是玄学,而是生活经验和当下的心理框架。大三确定要读研究生后,其实我曾一度在专业方向上犹豫不决:当时我对语言学和口译都有点兴趣。喜欢前者是因为当时颇有人格魅力的语言学老师,喜欢后者是因为口译带给人的挑战和兴奋感。那到底要选择哪个方向呢?
当时的各种想法已不可知,站在现在的时空节点上,我想我最终的选择的背后不单是当时热情和喜爱,还有一些独属于我的“背景知识”(就像前文的脉络揭示的):我天生对语言和文字感兴趣,英语基础扎实并始终热爱语言,对语言之间的转换抱有些许兴趣,以及(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刚好认识一位通过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该专业保研考试的学姐。于是我毅然决然地选择口译作为我的努力方向。
我读的是学硕,也就是学术硕士,相比专业硕士,学硕更侧重理论学习,我们的课表里除了占比不大的口、笔译实战课,还有口、笔译理论。学硕的培养目的不是“专业的译员”(当然你要是想做译员,也没人拦你),而是立足口译、深入研究一门语言的“学者”。
尽管我读的是学硕,但是我每周都能通过上实战课、口译社团培训、小组练习、同行交流获得大量的练习机会。读研期间,我的翻译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研一通过了catti二级口译的考试,研二开始接翻译兼职。我和许多客户因翻译而结缘,每次在结束工作后我都会因为“自己被需要”而获得成就感与获得感;和同专业的朋友们凌晨夜话,我发现大家虽然追求不同,但都同样热爱生活,这也让我不断感叹参差多态的美好。
不论是和客户还是和朋友,我们凭借一个叫做“翻译”的纽带在充满偶然的世界上缔结关系、建立默契。或许再细想一番,我们振动声带,活动舌头,就可以传情达意,拉近本不相识的两者的心理距离,这件事情本身不就很神奇吗?我们沉浸在那一个小时里,调动所有的脑力、注意力和表达力,帮助实现无数个沟通闭环,让人与人的距离更亲近,让这个世界又少了一桩烦心事,这真的是一件很值得赞美的事情。
2020年春夏是我的求职季,我铁了心要做翻译相关的工作。数次多番投简历、线下线上笔试、坐高铁去面试等等体验都成了热爱的注脚。
最后我在体制内(某政府单位)成功着陆,成为一名外事翻译。
外事单位的工作时间是比较标准的朝九晚五。在没有重要任务的情况下,工作量不会很大。不过呢,作为地方外事单位的翻译,一般要身兼数职(地方外事单位不同于外交部翻译司,其职能和地方实际情况限制了外事翻译无法单纯做翻译。
虽然可能以翻译的身份被招录,但是不可避免要从事一些行政工作),除了翻译,还会有一些重复性的行政工作和沟通协调工作,难度不高,但是很杂、很繁琐,也很锻炼耐心。如果赶上任务多的时候,条理性、逻辑性就显得非常重要:需要罗列好工作清单,明确各事项时间节点以及各个环节的痛点、难点,沟通时做到简明扼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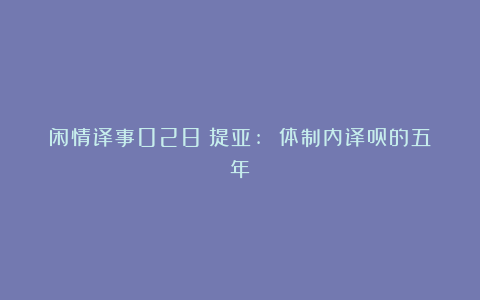
当然,这也是我工作2-3年后才练就的本领。工作初期的我其实也是莽莽撞撞的,犯过不少令自己啼笑皆非的错误,比如说函件内容写错了,结果几十份的材料要重新打印,或是由于心急,多头对接,结果局面被我弄成一锅粥。
后来,为了更准确高效地完成行政工作,我会遵循「问题是什么——什么场景——以后如何做」这样的框架随手记录工作心得。再之后犯错率就低了很多,这招对行政方面的沟通协调工作尤其适用。
虽然不加班,但是有些行政工作还是很劳心的。午休就变成了必不可少的心理调节港湾。单位有食堂,提供一日三餐;12点半左右吃好午饭,就可以利用14点前的这段时间休息一下,当然也有很多同事选择闲逛到上班时间。
其实在工作头几年,我对于行政工作还没有这么“成熟”的思维体系,仍旧对翻译最上心。做好每日行政工作及时不时产生的翻译任务之余,我一般会把时间用来练习翻译。头两年工作对我翻译能力的影响主要是翻译方法的改进。
我是学口译出身的,同时又是一个“脑子停不下来”的人,体现在翻译上就是总会思考怎样翻译比较地道、比较好理解。口译的时候我倾向于概括和paraphrase,这套方法在我读研期间被打磨成型,并逐渐成为属于我翻译的“第二天性”。即使是笔译,我起初也沿用的是口译的方法:在通读一遍之后一通键盘输出,边输出边调整句型和字词。
直到我在工作中接到越来越多的笔译任务,尤其是致辞稿和发言稿的笔译,我逐渐发现大多数情况下“释义”并不合适,于是我改变方法,着重学习精准表达,也就是不断增强对字词的辨析能力,放弃对短语的执着,并适当“抑制”自己调整的冲动。后面为了减少错误,我也会用DeepL先跑一遍,再去审校。整体而言,笔译学习的过程让我逐渐体会到精准之美,但也少了很多属于口译的乐趣。
在工作中我意识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反馈的重要性。上学期间,因为我接的都是口译任务,正反馈还是相当及时的。这里所提的反馈并不仅仅是客户的认可,还有参与感、交流感。工作后就不一样了,为领导翻译其实并不会让你产生很强烈的交流感(可能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的想法)。
因为首先,政府机关有自己的话术,这限定了表达的灵活程度,其次,分管外事的领导和外宾会见时的交流内容有限定的范围,对译员来说,翻译时面临的考验与其说是“翻不翻得出”,不如说是“政策懂不懂”。最后,外事活动,尤其是接待活动,其主要目的一般有两个,一是增进感情,即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二是推动直接利益方的后续交流,即活动之后做什么是目的。
大多数情况下,外事接待本身不会见证任何成果落地,交流本身的意义因为政策的宏大语境而被稀释。
至于笔译,我们一般在拿到任务、完成初稿后会给同事交叉审核,翻译完、交叉审核完便报给任务派送人员(对于笔译来说,没有反馈就是正反馈吧)。因为笔译相比口译更纯粹,没有社交、没有接待,我觉得更让人自在一点,且你是你唯一的责任人,这种情况下即使内耗也是争取翻译尽善尽美方面的内耗,做得到自得其乐。虽然和口译的乐趣迥然不同。
单位附近摄得的一次落日
目前,因为工作调整,加之前文提到的地方政府单位的现实,我已经很少做翻译了,可能一年也就三到四场比较重要的口译活动,加上零星的一些笔译文件,其余时间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对政府事务越来越熟悉的同时,翻译能力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在这之前大约两年,由于工作内容的转换,我产生过比较严重的内耗,困惑不外乎:我是不是做不好翻译、(无法充分实战的情况下)练习翻译的意义是什么、我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以及抛掉我差不多驾轻就熟的行政事务,我到底还能做什么?所有这些问题像吸水的海绵一样逐渐膨胀,占据我越来越多的心理空间,越来越让我无法回避一个更大的问题:翻译之于我到底是什么?
研究生时期,翻译是我的生活主线,我的学习以它为中心,生活也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时间里,它以间接及直接的方式带给我充实和快乐,我围绕翻译,培养起步入社会所需要的初步的社交能力和心理素质。
归属感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通过归属于一个集体,不论这个集体松散与否,人都会获得安全感和克服不确定性的自信与勇气;而获得集体的认同又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归属感。就是在这种确定且安全的以“译员”自居的环境中,我获得归属感,建立了自己的心理支持系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自我”。
但其实,围绕翻译建立的这种“自我”在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的支点只有“翻译”。一旦围绕这个支点潜移默化形成的认知系统或者说身份认同变形甚至“崩塌”,自我可能就会“崩塌”,然后面临痛苦的重建。
“翻译”的身份认同曾经无疑是令我幸福的。毕竟当一个人专注于一件自己热爱的事,人生的起起伏伏好像都被蒙上一层名为“passion”的滤镜。可是现实的复杂性限定了没有人是思特里克兰德。
家里的书架
上个月看到一本书叫《小镇做题家》,对我产生了挺大的冲击。严格意义上不算小镇做题家的我,好像在这些做题家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一个概念:生存心态。在某种场域中长大,便意味着习得一种与之对应的“生存心态”,它是一种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心智结构,是个体习得的看待周遭世界和付出行动的倾向和方式。它对个体的行动如此重要,以至于社会学家布尔迪瓦将其称为人的“第二本能”。
至于题目里的“小镇做题家”,它指的不仅仅是一类人,也是一种个体在实现阶级跨越过程中的独特心态:从农村和乡镇考到985高校的学子们,他们是如何看待新生活、新世界的?当他们失去曾经习惯的场域,当外在的社会结构突然消失,摆脱是必然的结果时,他们怎样走出迷茫?
习得的力量太过强大,这种力量像塑造小镇做题家的惯性思维一样塑造了我的一部分认知。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围绕翻译建立的单一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是我唯一确定的事,我紧紧攥住它以获得我在新环境中缺乏的安全感。
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我企图牢牢攥住这一确定性的时候,我也是在给自己设限?不去想社会学的文化资本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通过认定一件事,我抹去了其他数百种可能?面临新的客观环境,在挣扎于译员和行政人员双重身份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自我调试中,我找到了一个初步答案。
那就是把翻译看做一种可能。
这会让我失去一部分自己,但也会滋养另一部分自己。失去的那部分自我会以新的形式留下,比如说翻译所需的理解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仍旧会在我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滋养的那一部分自我会逐渐长大,在我疲惫时成为更温和的支撑力量。我就像一个有无数可能性的花园,时不时给从前遗忘的一棵树、一朵花浇浇水,观察它们如何花繁叶茂。
之前听说过一句话:教育就是你忘掉所学的所有知识所剩下的东西。那么类似的,将翻译作为工作的部分去除,它在你身上留下的东西其实同样弥足珍贵——所谓的“翻译素养”,所谓的镌刻内心的难以擦除的印记,它成为我探索世界的出发点,也是未来不设限生活的开始。
龟背竹的新叶 · 永远不乏新始
文字 / 图片:提亚
封面:Unsplash
编辑 / 排版:Oli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