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里的永根叔,就坐在树下的磨盘上,吧嗒着旱烟,眯眼看着他家那条肥壮的黄狗“虎子”在院子里耀武扬威。永根叔对虎子的宠,是全村出了名的。吃饭时,肉骨头尽着它先啃;谁家小孩要是扔石子吓着了虎子,永根叔能杵着烟杆骂上门去。
“永根,你这狗,快宠得上灶台了!”路过的邻居常这样打趣。
永根叔总是嘿嘿一笑,浑浊的眼睛里漾着满足:“一条狗嘛,通人性,疼它才知道看家。”
他这话,有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另一半,是说给那个在城里落了脚的独子——宝柱听的。宝柱是永根叔夫妻俩快四十岁才得的儿子,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时候宝柱要摘星星,永根叔绝不敢给月亮。地里的活再累,也没让宝柱沾过手;家里再穷,宝柱的吃穿用度也是村里头一份。
后来,宝柱争气,考上了大学,留在了省城,成了永根叔最大的骄傲。可这份骄傲,随着年月,渐渐变了味。
宝柱刚工作时还常回来,后来就成了电话,再后来,电话也少了,只在要钱的时候响得格外急促。永根叔和老伴儿种地、捡山货、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血汗钱,几乎都填进了宝柱买房、买车的“大窟窿”里。老伴儿去得早,临走前还拉着永根叔的手,念叨着:“咱宝柱……在城里不容易,别苦着他。”
老伴儿一走,永根叔的院子就彻底空了,只剩下他和那条被宠得没边儿的虎子。
那个下午,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发蔫。永根叔拖着病体从镇上卫生院回来,咳得直不起腰。他刚想进屋躺会儿,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在了门口——
灶台上,那只肥硕的黄狗虎子,正旁若无人地舔着锅里早上剩下的半碗米粥。它庞大的身躯占据了大半个灶台,爪子上的泥巴沾在擦得锃亮的锅沿上,格外刺眼。
“宠狗上灶……”
这句听了半辈子的玩笑话,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扎进了永根叔的心口。他浑身的气力仿佛瞬间被抽空,没有像往常一样抄起扫帚赶狗,只是无力地靠在门框上,呆呆地看着。
就在这一刻,口袋里的老年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是宝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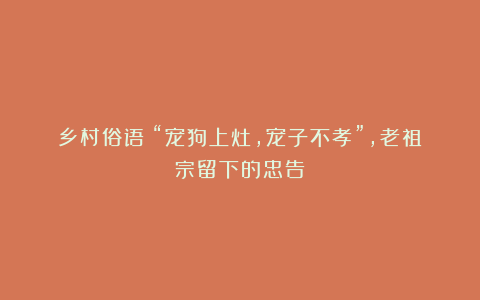
永根叔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接起来,声音带着咳喘后的沙哑:“柱儿啊……”
“爸,”电话那头的声音不耐烦地打断他,“这个月房贷马上要扣了,我手头紧,你再给我打三千块钱过来。对了,下周末你孙子过生日,非要个什么进口的玩具车,得好几百,你一块儿打了。”
没有一句问候,没有一句关心,只有理所应当的索取。
永根叔握着电话,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他抬眼,看看灶台上那只因为被惯坏而肆无忌惮的狗,再听着电话里那个因为被溺爱而冷漠自私的儿子。
两个身影,在他模糊的泪眼里,竟然奇异地重叠了。
一股巨大的悲凉和悔恨,像冬天的河水,瞬间淹没了他。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堵了块滚烫的石头,最终,他用尽全身力气,对着话筒嘶哑地吼出了一句:
“没钱!我……我这条老命,也不值钱了!”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随即是宝柱更高的斥责声。但永根叔已经听不清了,他缓缓地蹲下身,把脸埋在粗糙的掌心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像受伤老兽一样的呜咽。
院子里,那只叫虎子的狗,似乎终于觉察到气氛不对,从灶台上跳下来,凑到老人身边,依旧用头亲昵地蹭着他的裤腿。它不明白,为什么今天主人没有像往常一样摸摸它的头。
夕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一个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疤,印在沉寂的院子里。灶台上的爪印还在,电话里的余音还在,而那份无原则的、倾其所有的宠爱,最终结出的苦果,正由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独自吞咽。
被溺爱的孩子容易形成自私、任性、脆弱的性格。他们习惯于索取,而不懂得付出和感恩。
作者 | 鸿雁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