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陶刻艺术初论(二)
徐秀棠
紫砂陶刻艺术初论
一、陶刻艺术特点初探
若从艺术角度来深谈紫砂陶刻的艺术性,如果要全面、详尽地展开,对我来说还未具备充分的条件。因为受到现有资料及本人伏案时间的限制,现在只能从我从业陶刻这个优势谈些见解。
陶刻的本源,出自制陶者之手,是制陶者完成整个成品的一个组成部份。为了使观赏者、使用者,便于体会作者的艺术感受,作者采用了最合适陶坯上标记出来的方法-一镌刻。由于镌刻者是制陶者本身,它可以在坯体未干前或适当进行,镌刻的工具可以用竹尖刀(亦为制陶工具)和铁制刀镌刻。在“供春”时期之前的紫砂器上的陶刻是在坯体未干时划的,刻纹的二边有微高出坯而泛出型高埂,与刀刻痕有明显区别。当然在陶制品上留上名也只在上流制陶者中时行,这种时行势必受到当时艺术潮流的影响,受到砂壶爱好者评赏观点的制约,迫使当时的制壶高手在镌刻时要讲究书法、书体的水平。最初的镌刻大多位于壶底或稍等非显见面上。随着书法的讲究逐步推广到壶体上来,这时还是以铭文书法为主,画面较少,从传器刀痕可断:这时已有专造的刻刀,是在泥坯未干将干时镌刻的,因走刀处泥受挤压,有上泛之泥痕迹。此段时期已很少出现作者随意用制坯工具划压的陶制品了。
时大彬 腰圆提梁 延安博物馆藏
到清嘉、道年间以曼生为首的一批文学仕人的介入,尤其在陶刻装饰上是一次飞跃性的升华。凭借他们各个方面的学识素质,作出总体设计要求。造型形致特别讲究,施工制作以形而定。或需精工细作,或求粗犷豁达,选泥或粗或细,或调砂或铺砂,与形、工协调色泽相宜。铭刻中注以贴切的铭文,文学艺术性及他自成一格的书法,布局独具,装饰趣味不拘一格,镌刻的刀法与当时刻碑效果同宗。我认为曼生壶的特点不单在于书法、文学,更重要的还在于有完整的总体设计。对曼生壶的研究当作专题才行。
曼生壶 石铫提梁
具有高文学素养的金石、书画家的介入,对紫砂陶器向艺术的升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曼生同时代的梅调鼎,在秤砣式型制的“秦权”砂壶上题铭:“载船春茗桃源卖,自有人家带秤来。”这样的铭文确实气韵味无穷,再加上书法之功力,布局之高雅,才是真正的中国书法绘画纳于壶体,铭文款融与壶中。是壶、字、情、景皆切的完美上品。
韵石制 梅调鼎刻 秦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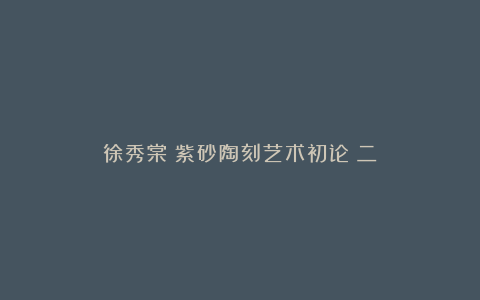
瞿应绍(子冶)饰一石铫壶,身、盖几片竹叶,题名曰:“翡翠婵娟,春风荡漾”,“置壶竹中,新落壶上。”署款曰:“子冶竹中画竹,适日移阴,因写其意”于盖上。这又是情趣横生,切情切境的一件陶刻自在之作,当为楷模之例。
瞿应绍 子冶石瓢 上海博物馆藏
近代唐云先生的很多切茗、切壶、切情,人称“三切”的饰壶佳作亦极精湛。
顾景舟制 唐云书画 井栏壶
文人介入,有偶有兴趣的,稍试即辞的,有把制壶陶工请入门槛的,有直接参与设计制作的,有短期的,也有长时期的,但他们俱“文人介入”的艺术特点,“极重玄博学识的铭文的撰写,自在挥毫的书法功底,饰壶移局的适纳多变,画面少,铭文书法多。陶刻只是在极少的范围内施展,品格高,量极少。历来学砂虽因时局兴衰而跌宕,但书画、文人名流至今从未绝缘”。以我之见,就艺术风格而论,这不能与以后的紫砂陶刻装饰风格混为一谈。
范静安制 北岩(邵云如)刻 碗灯
由于名流镌刻紫砂,确具高雅绝伦的艺术魅力,无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兴趣。这使生产发展的组合起了相应的调整,紧砂陶商们也聘请宜兴当地的书画名家,参与陶刻的书画,这是陶刻专业化的先导。这时的陶刻装饰风格也逐趋定局、定格化,切壶、切情的铭文款识减少,常是壶身一面书词、一面绘画。诗词内容大多节自茶经茶句或唐宋诗词有关茶事章节,还有抄录曼生、石梅等前人铭文的。画面大多参考木刻印本画谱,以四君子、山水、花鸟、人物、积古斋钟鼎款识铭文等,并在很多画面上有仿新罗山人笔意、仿白阳山人、仿大涤子……等。他们笔法老辣,技艺浑熟,讲究布局的程格化与完整性(开始时的镌刻可能由碑刻手韩泰完成或赐教),亦极风采,雅俗共赏,凭借他们在当地的艺术地位,每画一壶也几倍加价。
杨彭年制 朱石梅刻 井栏
太平洋战争之前,自邵云如开始专注于陶刻。陈少亭、任淦庭等原从卢兰芳先生学习,器成自立,也为陶刻之专业者,自然地形成了陶刻行业。有了专业者就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高档的壶请人来书画,就是一般的产品只要有人喜欢,也可由刻字先生来镌刻。自此也就自然地分工,技艺高的刻上等品,中档的刻中档品,差的于脆刻“万货”(如贡灯壶,贡壶每天可刻三、五百件)。这样,陶刻产品的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关于陶刻者的笔名的署刻亦极受陶商的制约,署名以商号及笔名居多,且可随时具名。也有几人署同一笔名的。故不易确切说清来龙去脉。
任淦庭刻 云肩瓶 宜兴陶瓷博物馆藏
在大量的“万货”产品的镌刻中,在逐步规范的画面上,产生了极富民间味道的装饰味,刻划线的组合装饰性强,刀法简练,这倒是一个重要的陶刻传统部份,不可在研究陶刻传统时被遗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