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 击 上 方 蓝 字 “ 心 香 文 艺 ” 关 注
心 香 文 艺
心香文艺音频已入驻喜马拉雅
在住院的日子里
吃五谷杂粮,
哪有不生病的?
岁月如流,年岁渐长,
病痛悄然叩响门扉。
十月十三日,
我住进了中美医院神经内科一科,
不请自来,却也避无可避。
这一日,是命运的转折,
还是生命的警示?
当我静静躺在病床上,
点滴一滴一滴流入血管,
仿佛时间也在缓慢流淌。
就在此时,
我的住院医师——徐微微主任,
轻步走进病房。
她面容和蔼,笑意温润,
像一缕晨光驱散阴霾。
她拿着核磁报告,
与我细说病情。
“情况并不乐观,”
她语气平和却坦诚,
颈动脉狭窄,慢性脑血栓,
字字如石,沉入心底。
我心头一紧,
不禁问道:
“颈椎已放支架,怎还会出问题?”
徐主任耐心解释:
“病变随时可能发生,
但不必惊慌,我们有办法。”
她提议先做造影检查,
若确有狭窄,再行支架植入,
并详述利害,条理分明。
我沉默良久,
最终点头同意。
为确保万无一失,
她请来外科一科会诊。
马陈建医生走进病房,
目光沉稳,语气温和。
他回顾我的病史,
分析当前状况,
再次强调:若造影确认狭窄,
支架手术势在必行,
为的是保障脑部供血,
防患于未然。
我未立即应允,
心中翻涌如潮。
手术无大小,
每一次刀锋落下,
都伴随着风险。我思虑再三,
甚至萌生前往北京大医院的念头。
那一夜,辗转反侧,
思绪如麻,难以入眠。
护士苑雪娜察觉我的焦虑,
轻轻走近,与我攀谈。
她言语风趣,笑容明媚,
像春风拂过心田。
她宽慰我,开解我,
用温柔化解我的不安。
我心中重压,
竟在谈笑间悄然减轻。
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护士们,
她们脚步轻盈,动作细致,
每一针、每一片药,
都倾注着责任与关怀。
她们用无声的行动告诉我:
你并不孤单。
一夜辗转,百转千回,
我终于下定决心——
就在本院手术。
我找到徐主任,她如释重负,
随即开导我:
“马陈建医生曾任职三零一医院,
师从知名专家,
临床经验丰富,
多年手术零失误。”
她的话语如定心丸,
让我放下心头巨石。
她告诉我:“医患同心,方能共克难关。”
我望着她真诚的眼神,
终于相信:在这里,我也能获得最好的救治。
在神经内科完成最后一轮输液,
我于当日下午,
转入神经外科。
住院医师张雁南热情接诊,
她询问病情,
聊起家常,
言语间透着亲人般的关切。
她的温柔与热忱,
让我卸下防备,
安心托付。
十七日清晨,
马陈建医生再次来到床前,
一句句鼓励,
如暖流注入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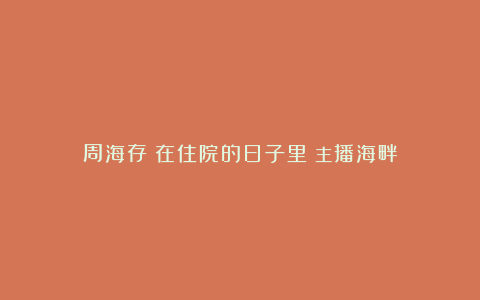
九时许,
我被缓缓推进手术室。
几位护士早已等候,
协助我完成术前准备。
麻醉开始,
是局部麻醉,我全程清醒。
麻醉师聂乾坤一边操作,
一边大声与我交谈——
因我耳聋,他必须提高音量。
我问些琐碎甚至幼稚的问题,
他从不厌烦,
一一耐心解答。
那一刻,
我心中涌起敬意:
这不仅是技术,
更是仁心。
马陈建医生上台,
先与家属沟通造影结果,
再俯身与我轻语。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
声音微颤却坚定:
“我完全相信您,
您大胆做,
我的性命,交给您了。”
马医生笑了,
温和而从容:
“别紧张,没那么严重,
您放心。”
随后,他在我的大腿根部切开小口,
我略有感觉,却不觉剧痛。
约两小时后,
他轻轻握住我的手:
“成功了。”
我眼眶一热,
只说了一句:“谢谢您。”
他回握我,
我们相视而笑,
那是劫后余生的释然,
是信任与托付的回响。
我被推出手术室,
回到病房。
护士们早已准备妥当,
牛子叶、于欣雨,
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白衣天使,
忙碌而有序地照料我。
牛护士技术娴熟,
话语温柔,
像家中晚辈般逗我开心,
只为减轻我的心理负担。
于欣雨年纪轻轻,
却沉稳如大人,
一句句贴心话,
说得我心头暖暖。
我躺在床上,
二十四小时不能翻身,
强忍不适,
她们便一次次轻声安慰,
一次次细心调整。
张雁南医生查房时特意来看我,
叮嘱术后注意事项,
语气如长辈般慈爱:
“听话,别乱动。”
我像个孩子般点头。
后来见到马陈建医生,
他笑了,我也笑了,
那笑容里,
有欣慰,有感激,
更有生命的重燃。
他说:“手术很成功,
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
我望着他,
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情感。
我由衷敬佩这位年轻的医生,
他的技艺精湛,
远超我的预期。
我爱他,
不是私情,
而是对医者仁心的崇敬。
我要记住他,
更要将他的名字,
传给更多人知晓。
终于出院了。
回望住院的这段日子,
心潮久久难平。
病痛曾让我恐惧,
但医者的温暖与专业,
让我重拾希望。
千言万语,
最终凝成一句:
向全体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尤其感谢我的主刀医生——
马陈建医生,
请接受我由衷的敬礼。
在这段与病魔交锋的时光里,
是你们,用双手托起生命的重量,
用仁心点亮黑暗的长夜。
以文会友,推广交流、相互促进,我在这里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