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闻一多先生讲唐诗是世无第二人,那么,钱锺书先生贯通古今中外的才学,不但是前无古人,就是以后恐怕也难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
╜
作者|许渊冲
来源|《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不一样的记忆》中有一篇对我的采访,题目是《许渊冲眼中的钱锺书》,里面有不少的问题,现在我来再谈一谈。
《不一样的记忆 与钱钟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
钱锺书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嘉勉后人。
首先,他考清华大学,国文和英文得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这给我的启发是: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上大学时,喜欢的课程就好好学,不感兴趣的就敷衍了事,不想做梅贻琦校长要求我们做的通才。
钱锺书上课时不大听讲,考试成绩常是全班第一。这点我只学到他的缺点,却学不到他的优点。例如我听中国通史时,雷海宗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年代数字,滚瓜烂熟,使同学们赞不绝口;但他讲的史实很少超越我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所以我听时心不在焉,而考试成绩也只及格而已。但是也有例外,上法国文学史时,全班同学都选了法文,只有我选的是俄文,结果考试时,学俄文的居然胜过了全班学法文的,这就使我洋洋得意,自以为学到了钱锺书的九牛一毛。
其实,清华才子,后来当了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说过:“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所以不但他的同学,就是他的老师,也无不对他刮目相看。据说他在清华毕业时,学校希望他升研究院,他却说道西洋文学系没有一个教授能做他的导师。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看他,后生小子怎能望其项背呢?
《不一样的记忆》154页上说:钱锺书“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妙,因此,记者采访我时问道:“据说钱锺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杨绛先生、李赋宁先生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作为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一个学生,您怎么看待这句话?”我当时回答说:“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而我看这个公式也可以算是一个警句。”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冯先生化复杂为简单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警句,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长处。例如他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礼乐”二字,又把“礼”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外在的秩序”,把“乐”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这些都可以说是警句。
这些警句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用英文解释“礼乐”的时候,就用了duty and beauty两个词。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
记者问到杨绛先生等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我却说有无此事我不敢肯定或否定,因为说有易,说无难。但我觉得这话像是钱先生的口气,评论也不无道理。
其实他不但是对教师,就是对当时的世界文豪,批评起来也是一针见血,毫不容情的。例如他说:“萧伯纳的伎俩,是袭取新出的学说,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借以欺世盗名;威尔斯则总抱着几个老调弹个不休。”(《不一样的记忆》105页)即使对他的父亲和父执章士钊,也是实话实说:“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不一样的记忆》141页)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考证对叶吴陈的评语是否出之于他的口,不如研究这三句话是否言之有理。
叶公超
第一句话,叶公超是不是太懒?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那么,钱锺书会不会说他的老师“懒”呢?《不一样的记忆》211页记下了他的一段话:“我在《围城》中所笑的,是模仿《荒原》体的劣诗,并不是《荒原》本身。像30年代的卞之琳、戴望舒等诗人介绍了法国象征派的诗,40年代的乔治·叶(即叶公超)介绍了Eliot(艾略特)和伍尔芙夫人等人,一时在中国很起了一阵激动,我在《围城》里所写的,就是这样拙劣的歪诗人。”
既然他能说叶公超是“拙劣的歪诗人”,那说他“懒”还是客气的了。
吴宓
第二句话,吴宓是不是太笨?《吴宓日记》1941年5月29日说:“我是一个奇特的人,不可以常情测的。我的性情是热烈而真诚,其缺点是急躁而笨拙。”吴宓先生自己承认“笨拙”,这恐怕不是谦虚吧!就以刚才谈到的选课而论,吴先生站着而叶先生坐着,我还以为他是系主任的助手呢!如果一个代表清华,一个代表北大,那也应该平起平坐呀!如以年龄而论,吴先生比叶先生大十岁,那更应该是他坐着。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这恐怕只能解释为“笨拙”。后来读了《吴宓日记》,更觉得吴先生未免太笨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5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30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超之所为,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宓完全在其掌握……又命宓与叶柽、杨西昆同为超治家具,于其迎妻子归抵昆明之日,烹茶热水以俟,俾一到可以喂小孩乳。”
这样看来,吴宓为叶公超买家具,买汽油箱,烧开水,热牛奶,不但是系主任的助手,简直是家中的用人了。
吴宓宴请叶公超不计其数,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是笨到家了吗!
钱锺书是如何评论吴宓的呢?他在一篇英文文章中说:“Mr.Wu Mi’s pageant of a bleeding heart, his inclination to wash occasionally his dirty linen in public, his sense of being a grand incompris, his incessant self – flagellation”,《为钱锺书声辩》21页的译文是:“吴宓从来就是一个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
这样看来,说“吴宓太笨”像是钱锺书的口气,不过比讥笑的观众多一份同情而已。
记得钱先生讲大一英文时说过一句妙语:To understand all is to pardon all.(理解就是原谅。)可见同情的基础是理解。其实,理解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例如叶公超懒于开外文系会,柳无忌却认为是无为而治,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那么钱锺书不也是懒于听课,因为他已经博览群书了吗?他考大学时数学不及格,不正是有所不为而后能在文史哲方面大有作为吗?所以关于懒与笨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又使我想起了钱先生讲大一英文时的另一句妙语: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stop.看来懒和笨也是一个问号,而不是一个句点。
说叶公超太懒就不是个句点,而是一个问号。只要看看他的历史,1920年十六岁的时候去美国,1921年考入大学,四年后毕业,192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得文学硕士学位,又在巴黎大学研究。六年之内,从美国中学生到英法研究生,如果说懒,恐怕也是和钱锺书差不多的有所不为吧。
他二十二岁回国,就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任教,比钱锺书回国时还小六岁呢。他的学生赵萝蕤、王辛笛等对他评价很高,他的同事胡适、吴宓等对他也有好评。如《吴宓日记》1926年10月3日说:“叶崇智(即叶公超)君邀同Winter至东城,王府井大街151公司楼上,进西式茗点。二君于美国现今文学极熟!所论滔滔,宓多不知,殊愧。”又如浦江清《清华园日记》1931年1月23日说:“晚六时归,公超即在余处面食,饭后同至公超处闲谈。谈英国小说,公超谓现代几个小说家学问皆极博,H.G.Wells(H.G.威尔斯)无论矣,Aldous Huxley(阿道司·赫胥黎)生物学极好,Virginia Woolf历史学极好。”
可见叶公超对英美现代文学知识广博,但是博而不精。他虽然在英国认识了艾略特,并且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但却没有写出一本专著。比起钱锺书来,那就差得远了。所以要说他懒,似乎也无不可。
钱锺书对现代英美文学家如萧伯纳和威尔斯都评价不高,对艾略特的《荒原》却比较宽容。在我看来,他对萧伯纳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到《荒原》上:艾略特的伎俩,是袭取古代和外国的典故,“生吞活剥地硬塞到自己的作品里去,借以欺世盗名”。
说吴宓太笨是不是一个问号呢?我们也来看看他的学历:1900年他七岁时已经认字三千,能读懂报章诗文,被誉为“神童”;1908年十五岁时,他作了《思游》诗和《咏史二首》。而钱锺书却是在1930年二十岁时才代父为钱穆写《国学概论序》的。1911年吴宓十七岁时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1917年二十四岁赴美留学,1921年二十八岁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而钱锺书则是1929年十九岁时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1935年赴英留学,1937年二十七岁得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后又在巴黎大学研究一年的。两人的学历差不多。
吴宓1921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教过吕叔湘、浦江清等著名学者,得到梁实秋等的好评。1925年回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名师;后代西洋文学系主任,提出了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指出了叶公超、钱锺书等一代学人所走的道路,做出了上半世纪的宏观规划,贡献实在不小。
吴先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了欧洲文学史、浪漫诗人、中英诗比较、文学与人生、翻译等课程。
上欧洲文学史时,他讲了柏拉图“一与多”的哲学,一指理想,多指现实。吴先生往往从理想出发来看现实,从一看多,所以矛盾很多。钱锺书先生却是从现实出发,能够多中见一,所以反能解决矛盾。
吴先生讲浪漫诗人时,盛赞雪莱的“泛爱论”,说爱情如灯光,照两个人和照一个人一样亮,并且将理论付之实践,结果生活中矛盾重重,显得笨拙,这大约是说他太笨的根源吧。看来这是宏观和微观的矛盾。
从宏观看来,他开中英诗比较课,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奠下了一块基石,几乎可以算是大智若愚了。他讲文学与人生时,说文学中包含的真理多于历史;讲翻译时,他认为模仿真境重于模仿实境。
但从微观看来,他把理想看得重于实际,结果理论往往脱离实践,就不免显得太笨了。例如他讲浪漫诗人时,说济慈一行诗中有声色香味等五种感觉词,我拿出一本《济慈诗集》来,请他举个例子,他翻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可见他的理论不一定有实例能证明。
他很重视原则,但却不太了解实际情况。例如他把师道尊严看成神圣不可侵犯,有一次他的讲桌没有搬回讲台上,他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把全班同学大骂了一顿,不知道同学们正是为了尊敬他,为了抄他贴在墙上的讲义,才搬动讲桌的。后来看到《吴宓日记》1939年11月25日中说:“下午2:30—3:30上’欧文史’课。为Outline(讲义)事,责学生嫌太急。”但是印象已经留下,可见他的笨拙往往是因小失大造成的。
陈福田
这样说来,吴宓太笨和叶公超太懒都不是句点,而是问号;只有陈福田太俗可能是个句点,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和吴宓、叶公超、钱锺书三位博雅之士都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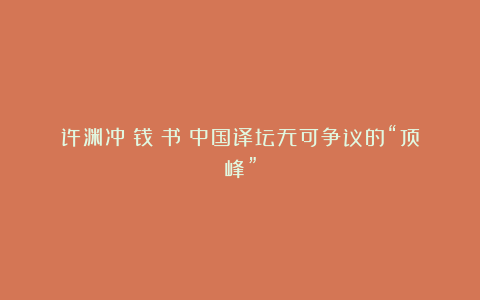
吴宓的风流雅事流传很广;钱锺书的雅言妙语令人叫绝;叶公超的雅致生活不同凡俗。如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他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证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香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说的文化就是一种雅趣。
而陈福田呢?他生在美国檀香山,得过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但却没有读过一本中国古书,毫无中国文化素养,这和比他大一岁的吴宓截然不同。他的美国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惊人的妙语,这和博学多才的钱锺书又截然不同。他的生活随俗,学生在昆明街上边走边吃东西,他也边吃边走。因为联大在农校时厕所不够,学生吃稀饭后下了课就在墙角小便,他也站在墙角小便。这和摆教授架子的叶公超也截然不同。总而言之,陈福田只有一个“俗”字了得。
但是“俗”字好不好呢?一般说来,俗人重利,雅士重义。其实,雅士也不是不重利,只是不能见利忘义而已。雅如叶公超,吴宓却说他“好利”,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俗气……
不要对每一个泛泛的新知滥施你的交情……
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
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
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
话虽如此,陈福田还是愿意借钱给穷学生的,甚至回到夏威夷去,向华侨募捐,设立檀香山奖学金,帮助成绩优秀而有困难的学生。所以他虽然语不惊人,但是行不逾矩,得到梅校长的重视,当上了外文系主任。关于这点,《吴宓日记》1937年6月27日记下了学生的意见说:“谓宓为本系学生人心所归,一切均胜陈福田,校长何以不命宓为系主任,殊属不平云云。”这也可以算是雅俗之争了。
陈福田对吴宓的看法,《吴宓日记》1929年9月16日有记载:“陈福田谓宓乃浪漫派中最浪漫之人。”也就是说,吴宓重情轻利。叶公超的看法却不同:“叶君亦力言宓之离婚,乃本于execution of ideas(信念的实施)。”这就是说,吴宓重义轻利。但据1933年9月22日《朱自清日记》:“叶公超曾说:吴宓的朋友除了他叶公超一人外,没有不骂吴宓的。”叶公超知道不知道吴宓对他的不满呢?
对钱锺书的看法,吴宓和叶公超、陈福田都有矛盾。《吴宓日记》1940年3月8日说:“随超、F.T.(陈福田)、徐锡良陪侍梅校长同归。梅邀至其宅(西仓坡)中坐,进茶与咖啡。宓倦甚思寝。而闻超与F.T.进言于梅,对钱锺书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
但吴宓对钱锺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吴宓日记》1937年6月28日说:“文学院长冯友兰来……拟将来聘钱锺书为外国语语文系主任云云。宓窃思王(文显)退陈(福田)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由此可见雅俗义利之间矛盾重重,但陈福田太俗恐怕还是一个句点。
陈福田先生最大的贡献可能是他编的《大一英文读本》,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对西南联大几千学生散布了西方的世俗思想。上学期给我讲大一英文的是叶公超先生,他对《读本》似乎并不满意,所以也懒得讲解。记得他讲过的课文有毛姆描写中国忍辱负重的苦力,赛珍珠叙述中国农村的苦难,兰姆听说的原始社会放火毁林烧死野猪吃烤肉的故事,胡适的文章和林语堂的《人生的目的》等。
陈福田最喜欢的美国当代小说是史坦贝克写美国落后农村的《愤怒的葡萄》,中国小说则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所以他选了这几篇课文。但是叶公超的兴趣不同,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我却觉得把毁林烧猪写成论文只是小题大做,不过可笑而已,算不得什么幽默。倒是林语堂引用了辛弃疾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反能引起会心的微笑。可见关于幽默,也是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就是雅俗义利之争,陈福田虽然俗,这些课文也不能算是重利轻义吧!
许渊冲在翻看钱钟书写给他的信
采访记者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有没有讲错的时候?”
钱先生讲大一英文用的也是陈福田编的读本,讲的内容和大家差不多,上学期主要讲中国的现实;下学期则多讲美国的政治(如《自由与纪律》)、社会(如《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如《经典为什么是经典?》)、生活(如《习惯》)、科学(如《一对啄木鸟》)、文学(如欧文的《孤儿寡母》、爱伦·坡的《凶手的自白》)等。
钱先生讲课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英国音,因为以陈福田为首的大一英文教师说话都是美国音,大家听惯了,对标准的伦敦音反而觉得别扭。钱先生讲课不用中文,而隔壁教室潘家洵先生把课文翻译成汉语,结果大受学生欢迎。但钱先生说的妙语,却不是别的教授说得出的,如他说过:“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等等。
1939年5月8日,钱先生讲解的课文是《打鼾大王》,说卧车上有人鼾声如雷,吵得旅客一夜不能入睡,大家怒气冲冲想要报复。不料清晨车厢门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千媚百娇的妙龄少女,大家顿时怒气全消,敌意变成笑脸,报复变成讨好。钱先生讲到这里,自己笑了起来。我也冲着坐在旁边的女同学笑了一笑。
5月11日的英文作文题是《吃得太多的一个好结果》(One Good Effect of Overeating),我就模仿这篇课文写道:一个人吃得越多,就睡得越死,打鼾也越厉害。即使他的妻子在隔壁和人偷情也不知道。他在梦里和他的妻子谈话,却听不见她在隔壁和人谈情说爱。等到他的妻子听见他不打鼾了,立刻从隔壁房间跑过来,给他一个甜吻,他感到非常满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我希望我的作文能够博得钱先生一笑,但改作文的是助教,钱先生看也没有看到。
大一英文期末考试时,周基坤坐在我右边,看得见我的答案,他就在我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结果考试成绩比我还好,把我气得要命。我本想在钱先生班上考第一,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不料改考卷的还是助教,钱先生学期一结束,就离开联大了。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从周基坤那里也学到了加工的一手,后来把外国人用散体翻译的中国诗词改成韵体,结果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记者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钱先生在离开联大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我回答说:钱先生到蓝田师范学院的事,我当时只是听说,后来读了《围城》,才明白一点详细的情形。
我非常喜欢妙语如珠的《围城》,曾打算把它翻译成英文。但一开始就在序言中碰到了一句:“人是两腿无毛的动物。”“无毛”的英文是hairless(没有头发的),怎么能说人是秃头的呢?于是我去查了一下Voltaire的原文,才知道“毛”是指羽毛,就译成featherless了。第二个问题是:方鸿渐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怀抱剧有秋气。”气字一般译成air,但在这里,钱先生会用什么英文词汇呢?我想起了雪莱《西风颂》第一句中有breath of Autumn’s being(秋天的呼吸),这里用breath不是正好吗?我想写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就作罢了。
钱先生到上海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教过杨必和孙探微。孙探微后来和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结了婚,朱启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跟随美军采访,并在美国密苏里军舰上亲眼目睹日本投降仪式的唯一中国记者,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他说钱先生和孙探微的师生关系很好,到过北京后海他们家中,和他们作中外古今谈。
钱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教过一个华侨学生刘新粦。刘也和我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同事,据他告诉我,钱先生在谈到他的学生时,说过许国璋写的英文比王佐良好。
但《吴宓日记》1947年10月13日却说:“煦(周煦良)议裁减复旦校阅人,已而11:00钱锺书、杨绛夫妇来谒。赠宓、煦中央图书馆聘锺书所编撰之《书林季刊》二、三、四期各一份。又赠宓锺书著小说《围城》及绛著五幕剧《弄真成假》各一册。锺书力言索天章、许国璋二君之不可用。”
索天章是清华大学外文系1936年毕业的,比钱锺书低三级;许国璋比索天章低三级,我又比许国璋低三级。他们二人当时都在复旦大学任教,并兼任吴宓主编《字典》的校阅人。许国璋英文虽然写得好,但并不可用为校阅人,可见钱先生对学生是一分为二的。
索天章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请教钱先生一个问题,钱先生不能当场解决,还是回去查了一下书才答复的。
王佐良也说过:“钱先生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并不见得比别人突出。只有许国璋和周珏良(周煦良的弟弟)对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周珏良读清华研究院时,要请钱先生做导师,但钱先生到蓝田去了。”
许国璋在《回忆学生时代》一文中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他英文写得好,主要是因为学了钱先生。
记者又问:“您再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
我说:“是195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家里,那时钱先生负责清华研究生的工作,同夫人杨绛到吴先生家来。”
我发现钱先生胖了(见1953年在北京大学中关村的照片),他们谈到邻居林徽因家的猫叫春,吵得他们一夜没有睡着,钱先生就爬起来拿根竹竿去打猫,讲得津津有味。我觉得钱杨二位这么高雅的人,怎么会对这种俗气的事感到兴趣?可见我对钱先生只是敬佩,并不了解。
其实,钱先生早在1933年写的《论俗气》一文中就说了:俗本与雅对立,但求雅过分,也会转为俗。而俗人附庸风雅就更俗。如果俗人俗得有勇气,“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对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那倒反而是雅。而钱先生打猫就是转俗为雅了。
钱先生在清华大学带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黄爱,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黄雨石。据说论文答辩的时候,把北京大学的朱光潜先生等人也请了来。朱先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指出了一些错误。不料钱先生在作结论时,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意见,反而指出了朱先生的错误,这就仿佛是魔鬼反对上帝了。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钱先生调北京大学,后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又借调到《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同时借调的有金岳霖、王佐良、熊德威、王仲英等人。熊德威是我的表弟,从小在英国读书,在牛津大学毕业,据他告诉我,钱先生非常谦虚,不耻下问。
王仲英是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诉我,金岳霖翻译《毛选》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锺书,不料钱锺书脱口而出答道: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还有一句成语:“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钱锺书译成: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于是传诵一时,钱锺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