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传统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法理”,是中国法理学与法律思想史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传统中国“法理”的具体内容,但却甚少留意近代以降诸多中外学人开始重新诠释传统“法理”的历史语境。20世纪20年代,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讨论达到一个高潮,而这一时期也恰与华盛顿会议后的撤废治外法权运动相重合。无论是爱斯嘉拉、宝道等在华西人,还是梁启超、吴经熊等本土学者,其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论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着彼时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存废问题;而他们在此问题上的相异立场,也间接塑造了其笔下传统中国“法理”的不同形象。梳理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法理”论说兴起背后的深层动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讨论。
作者简介
吴景键,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目 录
引 言
一、治外法权论争与传统中国“法理”的问题化
二、超越法治主义:梁启超的传统中国“法理”观
三、转向实用主义:吴经熊的传统中国“法理”观
结 语
传统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法理”?这种传统“法理”对于中国法律的现代发展又有何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梁启超早在百廿年前即于其名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指出,“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既有法系,则必有法理以为之原,故研究我国之法理学,非徒我国学者所当有事,抑亦全世界学者所当有事也”。而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外学者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近代重释,也已成为当代中国法理学与法律史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在部分法理学者看来,20世纪初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讨论,特别是其中对于先秦法家思想的新诠,实构成中国法理学史的开端。相较之下,法律史学者则更多是将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阐释置于论说者的个人思想谱系中,围绕梁启超、吴经熊等法学名家的传统中国“法理”观展开具体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降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重新阐释虽然始自20世纪初,但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达到一个高潮。梁启超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代表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便是在1922年正式出版,其后不久(1926年)又在爱斯嘉拉(Jean Escarra)与宝道(Georges Padoux)两人的主导下被节译成法文本;而吴经熊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几篇经典论述亦在同一时段内相继问世。这不禁引人思考,为什么上述中外学者会在这一时期开始集中关注传统中国“法理”?换言之,传统中国“法理”何以在此阶段得以成为一个问题?其背后的动因显然并非单纯的学术兴趣所能解释。正如同一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实以探索中国之未来为旨归一样,此阶段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种种诠释背后亦有相当明确的现实关切,也即治外法权的存废问题。既有关于治外法权的研究虽然对华盛顿会议后社会各界的讨论多有关注,但却甚少留意其与彼时传统中国“法理”论说兴起之间的隐秘关联。
事实上,宝道在其为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所作“序言”中便明确指出,梁启超所阐释的传统中国“法理”看似遥远,实则与所谓的“太平洋问题”,即治外法权交涉问题息息相关。梁氏原书虽未直接提及这一点,但从时间来看,则正创作于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举国讨论治外法权存废的舆论氛围之中,与此问题之间可以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现实关切在吴经熊的相关论述中同样有所体现,在其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首篇论述中,吴氏即清楚表示,他的目的是“希望治外法权可以在这个自由与正义的古老之邦中废除”。要言之,梁启超、吴经熊与宝道等人的传统中国“法理”重释,都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撤废治外法权的现实背景紧密相连;与之相应,各人对于治外法权及其背后西方“法治”话语的相异立场,也间接塑造了其笔下传统中国“法理”的不同形象。
本文第一部分将首先从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入手,重构传统中国“法理”论说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治外法权存废问题间的关联性;第二部分回到梁启超的相关作品,以期展现前述译本在何种程度上误读了梁氏本人的传统中国“法理”观;第三部分则以吴经熊为例,探讨本土学者重释传统中国“法理”的另一种进路;结语部分将简要分析传统中国“法理”的近代重释对于当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借鉴意义。
(一)从法权到法理:在华西人与治外法权论争
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治外法权的存废便一直是国人与在华西人共同关注的焦点。 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通过《关于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决议案》、同意组成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后,国内各界关于治外法权问题的讨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与此同时,在法权讨论委员会的主持下,旨在宣传中国法制状况的法律外译工程也相继展开。面对中国国内废除治外法权的舆论声浪,部分在华西方侨民则试图从批评中国司法现状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两个方面论证维持治外法权制度在现阶段的合理性。受此影响,1926年正式成立的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最终建议,在中国法律改革取得进一步成果以前,暂缓撤销治外法权。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专门提到,治外法权制度的设立最初是“因中外法律及司法观念之根本不同”,“俟中国法律及法律观念逐渐演进后始不适用”。这表明,治外法权的存废背后,不仅关乎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所直接考察的立法与司法现状,亦牵涉到更深层次的、对于中国法律理念——也即传统中国“法理”——的评价问题。申言之,如果传统中国“法理”与西方法理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那即便中国当下的法律改革已达到所谓的西方标准,西人也可以进一步主张这种改革因为缺乏观念层面的支撑而难以持续。而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外籍顾问爱斯嘉拉与宝道二人,无疑便是上述观点的重要支持者。
1922年,爱斯嘉拉被北洋政府聘为修订法律馆顾问,参与天津、上海等地的风俗习惯调查,并主持起草《商法法典草案》。在起草过程中,爱斯嘉拉便已提出要留心“中国国民之本能”与“旧有之习惯”。 1923年,爱斯嘉拉在其所作《治外法权问题:致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的备忘录》(The Extra-territoriality Problem: Being a Memorandum Presented to the Commission for Extra-territoriality)一书中专门谈及传统中国“法理”与治外法权存废间的关联性。在分析完中国的政治现状、司法机构与立法进展后,爱斯嘉拉笔锋一转表示,“为了结束对此问题的讨论,我们需要处理一个此前很少被提到的主要论点,它牵扯到复杂的法理学问题”。此处所谓的“法理学问题”,核心便是现代立法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之间的张力。在爱斯嘉拉看来,“现代立法,无论其内容多么保守、多么尊重中国人的感情,都难以在这一国度的土壤上扎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将与这个国家历久不衰的传统习俗之间存在鸿沟”。这种传统习俗反映在法律层面,便是“一种在其他地方已无处可寻的、形而上的法律理念”,这种“本土的法律是一种自然法,抑或’天理’。正如梅因所言,这种法律或存在于云端之上,或存在于法官的良知之中,却不会具体化为真正的成文法条文”。也正因为中国传统“法理”与现代法律之间的这种“扞格”,爱斯嘉拉进一步提出,“在法律进化的初期,进化的方向、持续的长度甚至是否能够持续都无法预料;因此在司法和法律事务方面,中国尚无法为外国人提供他们在各自国家历经多个世纪才获得的保障”。
与爱斯嘉拉的情况相似,宝道亦是在治外法权问题讨论正炽之时活跃于中国法界。早先在暹罗政府担任法律顾问的经历,让宝道对于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方面,他试图以暹罗废除治外法权之经验,“予中国以有益之指导也”;另一方面,宝道也明确表示,“中国之地位,不能媲美暹罗”。在他看来,由于治外法权问题最严重的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并为中国旧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触后刷新之渊源”,文明冲突尤剧,因此中国撤废治外法权的进程相较暹罗更需迟缓。换言之,正是“中国旧文明”的持久影响让宝道认为,治外法权的废除需从长计议。随着1926年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正式成立,宝道与爱斯嘉拉等人也最终决意以翻译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方式,系统表达其对于中国旧文明“法理”的认识,进而借此回应彼时已愈发迫切的治外法权存废问题。
(二)自然法与传统中国“法理”:以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为中心
1926年,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关于法家的部分由爱斯嘉拉与热尔曼(Robert Germain)二人译作法文,以La conception de la loi et les théories des légistes: à la veille des Ts’in(《法律观念与法家理论:先秦时期》)之名在北京出版,宝道和爱斯嘉拉二人分别为此译本作了长篇的“序言”和“导读”。在“序言”中,宝道首先即点明此书所讨论之传统中国“法理”与彼时治外法权交涉问题间的关联性。他认为,虽然“乍看之下,没有什么比梁启超关于先秦时期法律观念的研究距离我们当下更遥远的了”,但“只需要读一读爱斯嘉拉为此译本所作的导言就能明白,梁启超的观点与当下是何等相关,又能给今日诸多媒体所聚焦的时事带来怎样的启示”。而此处所谓“诸多媒体所聚焦的时事”,正是因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的一系列考察而备受关注的治外法权撤废问题,宝道称之为“中外之间的困境”。在其看来,这一“困境”能否得到解决,需要分析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当下的现状,二是中国人民的思维结构。”
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翻译梁启超的作品,显然更多在于揭示“中国人民的思维结构”。更具体而言,便是中国人的法律理念。根据宝道的理解,梁启超的作品表明,中国传统“法理”在两个方面迥异于西方:一是法律背后的宇宙观,二是法律背后的思维逻辑。首先看宇宙观,宝道认为:“从其历史的黎明时期开始,中国就相信自然界存在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涵盖宇宙的所有部分,并使它们彼此协调、和谐运作。这种秩序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一直存在,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人类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也必须遵循它。”这种自然秩序也就构成一种最高意义上的自然法,它“排斥成文法的主导地位,因为后者被视作人类经验与智慧的产物”;相比之下,成文法的任务“仅限于将自然秩序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如果这种表达准确无误,成文法便是良法,具有效力;但若表达有误,比如君主或政府在立法过程中误读了自然秩序,那么该成文法便无效”。为了进一步突出这种自然法观念与成文法之间的张力,宝道甚至不无夸大地写道:“对中国人而言,一个行为是否被允许、是善是恶、公与不公,绝不会脱离其内在的道德属性而仅为掌权者的意志所决定。”
其次是法律背后的思维逻辑。在宝道看来,中西法律在“形而上学观念方面的本质分歧,又因为思维方法层面的巨大差异而更加无法弥合”。西方的法律逻辑能够“将推理的对象还原为严格定义的某一单元或类别,而同一律原则使我们能够将它们彼此明确区分”;与之相比,中国人在进行法律推理时所使用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就并不那么清晰和精确。这些概念仿佛被一层模糊的半影所笼罩,使其边界不甚分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宇宙观与思维逻辑上的本质“差异”,宝道认为,“废除治外法权非但无法化解分歧,反而可能加剧误解,因为它将导致两种根本无法调和的思维方式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发生正面冲突”,而想要真正废除治外法权,唯一的可能便是复兴被儒家思想所边缘化的法家观念,“正如梁启超的正文所示,法家所构建并发展的法律概念,与西方公、私法大厦所奠基其上的基本原则颇为相似”,“如果全新的中国能够从中汲取灵感,那么这个妨碍东西方和解的重大障碍就将被消除”。
相较于宝道,爱斯嘉拉的“导读”则更关注传统中国“法理”观背后的儒法之争。事实上,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选择仅节译原书关于法家的内容,本身就代表了译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在爱斯嘉拉看来,“尽管被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所掩盖,但法家学派作为一股持续不断的思想潮流,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不容小觑”。也正因此,虽然儒家才是真正塑造传统中国“法理”的思想源头,但爱斯嘉拉却舍弃了梁启超原书关于儒家思想的阐述,转而借梁氏之笔宣扬法家的法律观念。为了进一步突出法家的意义,他还专门引用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的论述解释道:“儒家以外思想学派的复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唯有在这些学派之中,我们才有希望找到一块理想的土壤,用以移植西方哲学与科学中最优秀的成果。”
虽然选择放弃翻译《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关于儒家的内容,但爱斯嘉拉出于对比的目的,也同样在“导读”中对儒家的“法理”观进行了简要总结。与宝道相似,爱斯嘉拉亦将儒家影响下传统中国“法理”的核心归结为自然法。爱斯嘉拉认为,“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法律观念的考察,将会得出一个让浸淫于罗马法的西方法律学者感到意外的结论。中国的宇宙观将人仅仅视作宇宙中微小的齿轮——这一观念广泛体现在中国社会对于巫术、星象以及五行等自然力量的信仰之中——进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自然法观念:天道(la loi du Ciel)”。而这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理”观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对于成文法普遍的漠不关心”,成文法的“社会意义与技术价值也相应未被准确理解”,“人们对严格的法律裁决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同时更倾向于用折中的方法来达成妥协与事情的解决”。受此影响,传统中国“法理”的另一个特点则是一种“本质上的刑罚性”,因为法律的意义仅在于作为刑罚来保护礼乐所维系的自然秩序。
在爱斯嘉拉看来,儒家对于自然法的推崇以及对于成文法的贬抑,实构成中西“法理”的关键差异所在。儒家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法理”“与古希腊罗马的观念可谓天壤之别”,因为“在后者看来,成文法是最有力的绝对命令。正如品达所言:’法律乃是众神与众人之王!’”爱斯嘉拉虽然并不否认这种儒家“法理”作为一种“理想”有其价值所在,但“这一理想只适用于黄金时代(age d’or)”,而“对于我们当下的黑铁时代(age de fer)来说,法家才是正确的”。他甚至由此进一步设想,“倘若当初是法家胜出的话”,中西方的法理或许就会迈向相同的发展道路,而未来的中国只需将法家的法律观稍加完善,“便能在这一领域取得与西方相当的成就”。更具体而言,爱斯嘉拉认为,法家所强调的法律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在罗马自始即被视为法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法家对于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的主张,则可与“奥古斯丁所设立的法学家公开评论法律的制度(ius publice respondendi)相提并论”。要而言之,爱斯嘉拉在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导读”中,一方面试图将儒家“法理”等同于自然法,并批判其对于中国法律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则试图将法家思想与古罗马法理相比附,进而主张中国法学家以此为基础接纳、吸收西方法理学,逐渐消弭中西法律观念的根本性分歧,以期未来达成撤废治外法权的最终目的。
(一)以法救时:梁启超早期思想中的传统中国“法理”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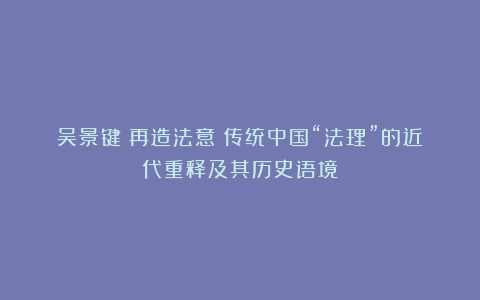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爱斯嘉拉与宝道二人笔下,梁启超的传统中国“法理”观主要呈现为一种对于先秦法家法律理论的推崇,以及通过复兴法家实现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期冀。这种对于梁启超思想的“重塑”,也间接影响了部分外国读者对于梁启超传统中国“法理”观的理解。如法国政治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1927年阅读完法译本《先秦政治思想史》后即表示,“译者(大概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出版此书的时候,都追求现实的政治目标:在’法家’学说中寻找亲西方的中国思想”,进而“使新的中国的建设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接近变得更容易”。然而,爱斯嘉拉与宝道的解读,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梁启超本人在传统中国“法理”认识上的重要变化。套用梁氏自己的说法,即将其“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相混同。要言之,梁启超的早期思想中确实存在以复兴先秦法家来接榫西方法理学的倾向;然而在1919年欧游之后,梁启超的传统中国“法理”观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并直接反映在后来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因此,爱斯嘉拉、宝道二人的阐述或许与梁启超早期思想中的传统中国“法理”观相近,但却与梁氏后期转向后的“法理”观截然相反。
梁启超对于传统中国“法理”最早的论述来自1898年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在该文中,梁启超将“法律之学”与“文明”相等同,提出“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这种观念背后显然预设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等级秩序,即西方国家因“治法家之学”而跻身“文明之国”;而中国虽亦曾有圣人立法,但“秦汉以来,此学中绝”,终沦为“相率视法律如无物”的“野蛮之国”。在这种文明等级论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虽然也关切治外法权问题,视之“为国体之大耻辱”;但却又主张“平心论之,此诸地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章章不可掩也”,盖因治外法权制度间接保护了《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的出版,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文明普及不可缺之条件,尽人知之”。
“文明”演进的标准此后也成为梁启超评价传统中国“法理”的一个重要参考。在1906年所作长文《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便依此对由儒、道、墨、法等四家所代表的“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系统分析。这里所谓的“法理”,实则更接近一种秩序观,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凡持旧主义者,又率皆崇信’自然法’。其所设条件,殆莫不有其理由,其理由之真不真、适不适且勿论,要之谓非一种之法理焉不得也”。儒、道、墨三家的法理俱以某种“自然法”为根基,故构成“中国法理学”的旧学派;而以实在法为中心的法家,则相对应构成“中国法理学”的新学派。
事实上,“旧学派”和“新学派”的区别,本身便已预设了一种进化论的观念。在梁启超看来,三种旧学派之中,儒家的礼治主义体系最为完整,该体系“崇信自然法,而思应用自然法以立人定法,其所立之人定法,则礼是也”,但礼治主义的缺点在于形式上规定得太过具体,难以与社会变化相适,“故在昔可为社会进化之助者,在后反为社会进步之障”。也就是说,从“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以自然法与礼治为核心的儒家“法理”属于一种落后的、停滞的旧法理。与之相对的则是法家的法治主义,它以富国强兵的“救世”目标而非自然法为直接依归,代表着一种进步的、发展的新法理,“实应于当时之时代的要求,虽欲不发生焉而不可得者也”。在这样一种文明等级论的视域下,中国“退化复退化”的原因便被归结为秦汉时期“法治主义之学说,终为礼治主义之学说所征服”;而在“万国比邻,物竞逾剧”的当下,中国想要求得生存,则“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换言之,早年的梁启超与爱斯嘉拉、宝道等人一样,认为现代中国的希望即在于复兴先秦法家的法治主义。
(二)由法返儒:梁启超后期思想中的传统中国“法理”观
民国建立以后,梁启超的主要精力转向政界,其间更是一度担任司法总长一职。这一阶段,梁氏的主要观点依旧是按照西方的“文明”标准改造中国法律,以期最终收回法权,只是其关注点由法理转向了制度。在出任司法总长后的首次政见陈述中,梁启超即提出:“领事裁判制度本为国际上之奇耻大辱,欧、美各国之得有此权,惟在中国与土耳其也。此权不能收回,终为损失法权之要点,故将来司法制度日臻完美,必欲与各国更定废弃之条件也。”在主持司法整顿时,梁氏亦曾致信其下属表示:“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收回法权之要图。”要言之,梁启超此阶段内主要致力于通过司法改革,在西方所设定的“法治”标准下提升中国的地位;与之相应,传统中国“法理”问题也相对淡出其视野。
然而,1919年至1920年间的欧游之行,不仅重新激活了梁启超对于传统中国“法理”问题的兴趣,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其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既有判断。如前所述,梁启超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评价原是以文明演进为标准,将儒家“法理”视作中国文明落后之根源,而“欧游后的梁启超已倾向将中西文化视为二元而非两个阶段”。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即不再主张以西方的“文明”标准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中西文明置于同等地位,一方面“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另一方面“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证明了以物质为主的西方文明之弊病,因此以精神为中心的中国文明就更有了几分救西方文明之弊的意味。思想史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即敏锐地观察到,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保存中国精神不再仅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盲目的责任。当西方精神不但成了不好的东西,而且很坏,中国精神就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好的”。而文明等级论的弃置,也进一步影响到了梁氏对于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期待。与彼时部分中国知识精英仍寄希望于美国所主导的新国际秩序不同,梁启超明确表示,“现在外国人在中国管理的事已经不少,那一桩说得上真有好成绩来”,因此“不能望外人,只好望自己”。针对自己此前所亲身参与的诸项法政改革,梁启超也反思称:“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换言之,欧游之后的梁启超已清楚意识到,按照列强所设定的标准进行相应的司法改革,或许并不是中国法律发展的真正出路所在。
前述“文明”观念的转变,由此也构成梁启超1922年写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的主要思想语境。在此书“序”中,梁启超感慨,“还治所业,乃益感叹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并进一步表达了希望通过此书补西方文明之弊的愿望:“书成后,徐志摩拟译为英文,刘文岛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拟译为法文,倘足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斯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虽然同样是翻译,但梁启超本人的期待与爱斯嘉拉及宝道二人的愿望实大相径庭:后者意图借此发现先秦政治思想与西方相同之处,而前者却恰是努力寻找先秦政治思想超越西方之点。更具体则反映在双方对于法家思想的评价之上。爱斯嘉拉与宝道试图通过抬升法家思想以对接西方法理学,而此时的梁启超一反其早年对于法家的溢美,转而以儒家“法理”批评法家“法理”。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关于法家的章节中,梁启超明确指出:“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申言之,法家“以治者与被治者为画然不同类之两阶级,谓治者具有高等人格,被治者具有劣等人格”,故一方面对上允许君主任意行使立法权,而不加任何限制;另一方面对下则“以权衡尺寸喻法而以被量度之物喻被治之人也”,排除民众对于立法的参与。法家这种对于普通民众“人格”的贬抑,在梁启超看来,实与彼时北洋军阀所谓“国民程度不足”之说相类。与之相对,儒家则主张“全人类各个人格之交感共动互发而骈进”。因此,儒家的“法理”非但不再是一种旧法理,反而构成一种对于法家“法理”的超越:“儒家以活的、动的、生机的、唯心的人生观为立脚点,其政治论当然归宿于仁治主义,即人治主义。法家以道家之死的、静的、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为立脚点,其政治论当然归宿于法治主义,即物治主义。两家孰优孰劣,以吾侪观之,盖不烦言而决也。”
(一)“法律化的儒家”:吴经熊的传统中国“法理”批判
1920年夏,就在梁启超刚刚结束其欧游之行后不久,21岁的吴经熊正式开启自己的海外求学生涯,负笈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其赴美后的学术处女作《中国古代法典、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料辑录》(Readings from Ancient Chinese Codes and Other Sources of Chinese Law and Legal Ideas)一文中,吴经熊希望通过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阐释,“向世界证明,中国的法律思想已经为接受现代社会法理学做好充分准备,并且希望治外法权可以从这个自由与正义的古老之邦中废除”。
在这篇论文里,吴经熊首先将传统中国“法理”置于比较法的框架之中,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资料的梳理将进一步扩展“比较法理学的研究范围”,而“各个时代的法律相汇总,定然比某一特定时代的法律,更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也能赋予法律理念“更为强大的力量”。从中可见,吴经熊理想中的法理学,不仅应该在横向空间维度上包纳中西,更需要在纵向时间维度上跨越古今,这也就赋予了传统中国法律思想一种法理学意义上的特殊价值:因为“中国是当今繁荣于世的国家中最古老的一个”,“若没有健全的法律原则作为基础,没有正义之源泉为其不断地提供营养以实现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延续如此之久的”。随后,吴经熊借鉴考克雷克(Albert Kocourek)的理论指出,法律的演进可以划分为“法律与宗教混同期”“非伦理时期”以及“法律与道德再融合期”三个阶段,而传统中国“法理”大体对应于“法律与宗教混同期”到“非伦理时期”的过渡阶段,具体又包括“以老子为创始人的自然法学派,以孔子为领袖、文王为典范的人文主义学派,以商鞅为代表的实证法学派,以及以班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上述学派所阐发的四种元素,即纯粹理性、行政正义、确定性与清晰性以及历史发展的观念”,如果能够被很好地“结合与协调”的话,便能够极为接近20世纪的法律观。换言之,传统中国“法理”的几大学派,只要经过适当的整合,便可达至最新的“法律与道德再融合期”,也即“为接受现代社会法理学做好充分准备”。
这篇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处女作为吴经熊在国际法学界奠定了初步声誉,也让其结识了忘年交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后者在读罢此文后表示:“非常欣赏其所从事的工作,并期待读到未来的续篇。”然而,这一“续篇”却让霍姆斯等了将近十年之久。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吴经熊先后前往法、德留学,回国后又相继任职于东吴大学法学院与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直到1929年底卸任赴美后才重新捡拾起自己关于传统中国“法理”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吴经熊的传统中国“法理”观相较十年前却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如果说十年前,儒家“人文主义学派”与法家“实证法学派”均被吴氏视作可以被有效整合为现代法理学的传统资源;此时,吴经熊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阐述则转而以对于儒家的批判为主。在1930年1月所作题为《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The Struggle Between Government of Laws and Government of M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的演讲中,吴经熊表示,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法律理论代表了法律思想演进中的更高阶段”,而“儒家在汉代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它“使中国的法律科学整整封印、僵化两千年之久”,“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法律思想才从儒家思想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在吴经熊看来,造成这种悲剧的核心,便是一种“法律化的儒家”(legal Confucianism),即“儒家思想渗入并最终淹没了整个法律体系”,使得“整个法律体系沦为儒家思想基础的上层建筑”。自唐代以降,传统中国的法律“仅仅是道德的婢女,成了无足轻重的事务”;与他此前所说的“法律与道德再融合期”不同,“中国法律的情况却是道德的过度饱和与泛滥,最终造成了一种集体的陶醉与梦游状态”。要言之,此时的吴经熊转而认为,汉代以后的“独尊儒术”使得传统中国“法理”的几种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平衡,故而陷入停滞之中。
(二)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吴经熊传统中国“法理”观的再思考
初看之下,吴经熊的传统中国“法理”观与爱斯嘉拉及宝道颇为相近,即将儒家“法理”视作中国法律发展停滞之根源;但不同的是,吴经熊并未因此而像二人一样进一步主张缓废治外法权,直到中国全盘接受西方法治理念为止。与之相反,就在《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演说后不久,吴经熊即受邀以《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The Problem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为题在1930年4月召开的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吴经熊在演讲中指出,“治外法权制度确实建立在一块坚实的基石之上,一块名为顽固偏见的基石”,而治外法权制度的起源也并非像诸多西人所言,源自所谓“文明的冲突”,而是源自“不文明的冲突”(a clash of uncivilizations),因为“真正的文明之间从不会发生冲突,他们只会相互交融。当这两大文明交融之季到来时,那才是人类真正繁盛的春天”。对于华盛顿会议后所成立的调查治外法权委员会,吴经熊也同样认为,它的“很多建议要么是无用,要么就是没有道理”,特别是其中关于建立完备立法以消除“中国法中的不确定性”的建议,在他看来,“法律不是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Procrustean Bed),它必须不断生长,而立法并非它发展的唯一途径”。
将吴经熊不到半年时间里所发表的两次演说相结合可以看出,他虽然一方面批评传统中国法律中“道德的过度饱和与泛滥”,但另一方面却并未因此转而接受一种彻底的法律至上主义,也没有将治外法权制度与西方所谓的“文明”相等同。事实上,在吴经熊看来,法律与道德均服务于一种更高级的“文化事业”。而“人类的文化事业,是由无数的解放运动积聚而成”,其中既包括“精神上的解放”,亦包括“脱离法律的专制而得解放”,“我们须晓得不但人治有专制,即法治亦有专制的”。因此,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都是共同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手段而已,“中国春秋时代儒家和法家互相争论,几以为法律和道德是枘凿不相入的。不知法律自有法律的作用,道德自有道德的作用。离之双美,合之两伤”。从中可见,吴经熊不仅反对汉代以降儒家以道德“淹没”法律体系,亦同样反对法家以法律抹杀道德。所以张君劢才对此评论称:“吴君越脱成文法派之束缚,而为法界开一新生面之旨趣亦在是矣。”
吴经熊对于法律与道德的上述理解,实则深受霍姆斯法律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根据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解读,霍姆斯的法律实用主义包含两大特点:一是法律的语境性,二是法律的工具性。所谓“语境性”,是指法律“嵌入过去的面向”,它“包含着一个民族在漫长岁月里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因此必然牵涉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而所谓“工具性”,则是指法律“展望未来的面向”,“是对共同体不断变化的要求和需求的回应”,是借法律以实现解放。用霍姆斯的格言概括来说,“与过去的历史连续性是一个必然,却非一个义务”。
如果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来理解传统中国“法理”,那么儒家思想所主导的传统道德观念便构成中国法律的基本语境,或者用吴经熊的话来说,一种“正义之源泉”。但与此同时,吴经熊又移用霍姆斯的格言作出批评,中国文明不能“错把与过去的连续当作了神圣的义务”。这也就解释了吴经熊为什么会像部分论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对于传统中国“法理”似乎存在一种矛盾的态度:既同爱斯嘉拉、宝道等人一样对于“法律化的儒家”提出犀利的批评,又如梁启超一样积极肯认中国文明的伦理价值。这种表面“矛盾”的背后,对应的是法律实用主义哲学的两个面向:在关注作为一种文化语境的传统法律观念的同时,又警惕法律因过度道德化而无法成为与时俱进的工具。其间的微妙平衡,既不能依靠立法上的简单移植,亦绝难仰仗治外法权制度下不谙中国传统“法理”的外籍法官,而只能由会通东西的中国法律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借用实用主义的方法予以灵活把握。正如吴经熊本人甫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法官时所言,“我可以试着将中国法律霍姆斯化了”。
葛兆光先生曾经指出,思想史的演进可以被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而传统中国“法理”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20世纪20年代治外法权论争这一历史语境的刺激之下,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被重新唤起与再度诠释的过程,由此也呈现出多重面相:在爱斯嘉拉与宝道笔下,对于自然法的推崇构成传统中国“法理”的主要特点,并因此桎梏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进程,也导致治外法权制度难以在短期内废除;而梁启超早年虽曾一度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批评儒家的“礼治主义”属于落后的“旧学派”,但晚年却转而认为“礼治主义”构成了对西方“法治主义”的一种超越;吴经熊的传统中国“法理”观则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在关注法律传统语境的同时,又警惕法律的过度道德化。这三种传统中国“法理”观实则映射了几人作为在华西人顾问、法政思想家与司法实践者的不同诉求。
梳理百年前传统中国“法理”论说兴起背后的深层动因,也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当代讨论。就国内法学界而言,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重新发现与认识,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法律文化”研究热潮。这一时期对于传统中国“法理”的检讨,在相当程度上是在探索、反思中国法律现代化受阻的文化根源,实则与宝道、爱斯嘉拉等人在思路上有相近之处。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反思的焦虑开始让位于文化主体性的追求,传统中国“法理”的总结由此转而成为诠释“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这其实又与梁启超当年在欧游之后对于儒家“法理”的着意赞扬遥相呼应。也正是在前述文化批评反思与文化主体性建构这两种进路之间,吴经熊的法律实用主义立场亦逐渐凸显出其特有价值:如何在充分尊重传统“法理”的同时,从中梳理、鉴别和提炼出可以与时俱进的元素,业已成为当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迫切需求。而这或许才是传统中国“法理”真正的时代意义所在。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