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花香如旧 岁月温柔
花香如旧,岁月温柔。那一点善意,如星火,终成照亮归途的灯。——题记。
刘洁
篇章一:1998年·初遇
那年头,镇子的秋天像是被老天爷蒙上了一层洗不净的灰纱,整日里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远处的鹿鸣山隐在乳白的薄雾里,轮廓模糊得像宣纸上晕开的墨痕,又像少年人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堵在胸口发闷的惆怅。
我师专毕业,分配回老家,在镇子上二初中当数学老师,兼班主任。那年我刚满二十一岁,瘦高瘦高的,带着几分青涩,额前的郭富城括号样式的碎长发还带着学生气,手里的教案却已经要撑起几十个孩子的未来。
教书这活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是因为在这山坳坳里的偏僻乡镇,知识是铺在孩子们脚下唯一能通往山外的路,是他们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唯一指望;小,是因为我除了三尺讲台、一盒粉笔和满肚子半生不熟的诗文,能给他们的实在有限——连自己都还没摸清人生的模样,却要替他们指引方向。
教室里总弥漫着呛人的粉笔灰和旧书本特有的霉味,混合着窗外飘进来的泥土气息。我日日浸润其中,踩着上课铃进,踏着下课铃出,黑板上的公式写了又擦,作业本上的红勾画了又画,人也渐渐像一支用旧了的粉笔,磨去了棱角,连眼里的光都黯淡了些。
直到那个女孩出现。她叫林蔓。开学一周,我才记住这个名字。她太安静了,像墙角一株默然的蔓草,悄无声息地生长,从不引人注目。她总穿着洗得发白、边角都有些磨毛的旧衣裳,一身衣服能穿大半个月不换,像墙角一株默然的蔓草。她瘦得像根豆芽菜,风一吹就要倒。头发黄焦焦的,脸也灰扑扑的,就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像山里头的泉水,清澈,却总蒙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惊慌。
她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等她挪到窗口,大盆菜里往往只剩些汤水。她从不抱怨,只默默拿着那个掉了漆的旧饭盒,怯生生地看着打饭师傅。那眼神,不像索取,倒像乞求。
我心里头,就那么咯噔一下。说不上是可怜,还是别的什么。就是觉得,那么丁点儿大的孩子,不该是这个眼神。我快步走进食堂售饭窗口,拿起厨师的勺子,勺子往锅底沉了沉,带上来几块沉在底下的土豆块,还有几片肥肉的边角料。
我飞快地盖在她的饭上,上面再铺上一层稀汤寡水的白菜,做得不露痕跡。她愣住了,捧着碗,小小的身子僵在那儿。
她愣住了,捧着饭盒,小小的身子僵在原地。她回头看我,隔着食堂蒸腾的雾气,目光深深落在我脸上。那一眼,清澈见底,带着讶异,还有一丝微弱的光。我仓促点头,示意她快吃吧。
那一眼,我记了很多年。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篇章二:秘密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像是缔结了某种无声的约定,无需多言,却彼此了然。每天早上,我故意早来会趁教室还没人,把家里带来的苹果,或是点心,“顺手”放进她桌肚里最靠里的角落,用课本轻轻压住,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她总是来得不算早,却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那份隐秘的暖意,心领神会地收下,从不说破,也从不刻意道谢。只在低头整理书本时,用那双黑亮得能映出人影的眼睛,飞快地、偷偷地看我一眼。
那眼神里藏着太多情绪:有小心翼翼的感激,像捧着易碎的珍宝;有难以言说的不安,仿佛觉得自己不配这份馈赠;还有一丝让我心头骤然温热的信赖,像寒夜里燃起的一点星火,纯粹又真切。那温暖,不像烈火那样灼人,倒像冬日里揣在怀中的暖手炉,温温的、糯糯的,顺着血液蔓延到四肢百骸,足以驱散青春期所有莫名的寒意,也驱散了她周身那层孤寂的薄雾。
后来我才从同学们口中得知,她的人生远比我想象的沉重——父亲在她小学时就因意外离世,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家里的田地靠亲戚帮衬着种,微薄的收入大半都花在了医药费上。才十三四岁的她,早已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唯一的支柱,既要咬牙撑起学业,又要在周末回家洗衣做饭、照料母亲,小小年纪就扛起了不该有的重担。
变故发生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天空压着厚厚的乌云,连教室里的光线都透着一股压抑。我刚上完课准备回办公室,就看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瘦弱的妇人,穿着旧棉袄,头发枯黄凌乱,走到我面前,声音有点嘶哑。“刘老师,我实在撑不下去了……,让蔓蔓辍学吧,让她回家帮我一把,……”林蔓妈妈的嘶哑声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而林蔓,就躲在办公室虚掩的门后,单薄的肩膀剧烈地缩着,像一片被狂风裹挟的落叶,随时都会被撕碎。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脊背挺得笔直,可我分明看见她的身子在不住地颤抖。她死死捂住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眼眶红得吓人,泪水顺着脸颊无声滑落。我看着她死死捂住嘴,不让哭声溢出。
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篇章三:家访
那天放学,我特意留了下来,将林蔓唤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我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牛皮纸信封,指尖能触到里面纸币整齐的纹路——那是我刚发的一个月工资290块零八毛,是我能拿出的全部钱。我把信封轻轻递到她面前,声音尽量放得温和:“跟你妈妈说,这是学校给品学兼优的学生发的专项奖学金,必须用来交学费、供你读完书,这是规定,不能退。”我撒了个善意的谎,语气坚定得不容置疑。
她愣愣地看着我,又低头看向那个信封,迟疑了几秒才颤抖着双手接过。信封在她掌心显得有些沉重,她刚握稳,眼泪就“啪嗒”一声砸了下来,紧接着,更多的泪水汹涌而出,在牛皮纸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印记,像一朵朵骤然绽放的墨花。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化作一声哽咽,然后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极低,久久没有直起。起身时,她又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有愧疚,还有一丝破釜沉舟的坚定,随后转身,像一阵风似的跑出了办公室,单薄的背影在走廊尽头渐渐消失。
我望着她远去的方向,心中五味杂陈,像打翻了调味瓶。我知道这些钱,也终究是杯水车薪。我能给的,仅此而已。一点钱,几个苹果,或许能暂时帮她渡过难关,暖她一时,却终究抵不过生活的风霜,暖不了她往后漫长人生里的艰难坎坷。可我只能尽我所能,为她摇摇欲坠的青春,多撑一会儿伞。
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她母亲病重的消息。我借着“家访”的名义,按她之前提过的地址,找到了西关那间低的租屋。推开门,一股浓重的药气扑面而来,混杂着潮湿的霉味,呛得人鼻子发酸。屋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得可怜,唯一的一张木板床上,她母亲蜷缩着,脸色蜡黄如纸,呼吸微弱。而林蔓,就蜷在屋角的灶台前,守着一个冒着热气的药罐,小小的身子裹在旧衣裳里,小脸瘦得只剩下一双大眼睛,黑亮却带着掩不住的疲惫,眼底布满了红血丝。
我没多说什么。等药煎好,她倒在碗里,晾到温热,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扶起母亲,一勺一勺地喂下去,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易碎的珍宝。母亲咳嗽时,她会轻轻拍着后背,眼里满是担忧。离开时,我悄悄将身上带的所有现金都压在了空药碗底下,不多,却希望能帮她们买点营养品。
自那以后,我“顺路”去她家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是周末,拎着一兜新鲜的鸡蛋和半块猪肉;有时是下班路上,带些小孩子爱吃的奶糖、饼干和橘子味的硬糖——我记得她上次吃零食时,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每次去,她都会默默地接过东西,帮我倒一杯温水,然后坐在一旁,小口小口地吃着零食,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一点浅浅的弧度。吃完后,她就用那双比从前沉静了许多的眼睛望着我,眼神里没有了最初的惊慌,只有满满的依赖和感激,像望着家人一样。千言万语,都藏在那一眼里,一切尽在不言中。
好在老天眷顾,她母亲的病情渐渐有了起色。有一次我去,她母亲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看到我进门,颤巍巍下床,嘴唇哆嗦,想要说什么感激话。竟然就要往床下挪。我慌忙上前一步扶住她,手心触到她枯瘦冰凉的胳膊,心里一阵发酸。
“大姐,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我紧紧按住她的肩膀,“孩子这么争气,成绩越来越好,将来一定有出息,这比什么都强。”她母亲泪流满面,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动容,拉着我的手反复念叨:“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是蔓蔓的福气,这辈子都忘不了你……”
我们之间,自此多了一层难以言喻的牵绊,超越了师生,更似亲人。那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仍在继续,有时是书桌里悄悄出现的一个红苹果,有时是抽屉里一罐香甜的麦乳精,有时是一张我写着“坚持住,你超棒”的小纸条。东西虽小,却是她灰暗青春里珍贵的光。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篇章四:温暖
从那以后,我总想着法子给她带些吃的。中午回家,我让妈妈多煮些饺子,用保温桶装着带到学校,趁课间没人时塞给她,看着她红着脸小声说谢谢,指尖捏着温热的饭盒,眼里满是局促又感激的光。知道她很少能吃到荤腥,为了让她解解馋,我到街上的卤肉铺买些卤肉用干净的油纸包好,假装“吃不完”分给她,看她小口小口地啃着,嘴角不自觉扬起浅浅的笑意,像雨后初晴的月牙。
有天中午,亲戚家办喜宴。我突然想起林蔓,回到学校,骑上摩托车硬拉着她往喜宴的地方去。面对朋友们好奇的目光,我随口说“这是我表妹,一起吃个饭。”说着就往她碗里夹鱼夹肉,一个劲让她不用客气。她起初还有些拘谨,筷子捏在手里半天不敢动,脸颊涨得通红,直到我不断给她布菜,轻声劝她“多吃点”,她才慢慢放开,眼眶红红的,一口一口吃得格外香,像是要把这久违的美味都记在心里。
端午节那天,家里包了不少蜜枣粽,还煮了一大锅热乎乎的鸡蛋。我特意挑了几个个头最大、糯米最饱满的粽子,又揣了五个带着余温的鸡蛋,一早就在教室门口等她。她来的时候,依旧穿着那件旧衣裳,看到我手里的东西,脚步顿了顿。我把粽子和鸡蛋塞到她手里,她捧着还带着温度的食物,指尖有些颤抖,抬头看我的时候,眼里的惊慌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暖意,轻声说:“谢谢。”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已是深秋,风变得凛冽起来,吹在身上带着刺骨的凉。可林蔓依旧光脚穿着妈妈做的布鞋,鞋面早已磨得发亮,单薄的旧衣裳裹在身上,根本抵挡不住寒意。她本就精瘦,十四五岁的年纪,个头倒有一米六五,细高的身子缩着,冻得微微发抖,却依旧挺直了脊背,精神头倒是挺好。我看在眼里,心里揪得慌,实在不忍心让她就这么挨冻。
中午下班,我特意绕到老街的服装店,跟老板细细描述了林蔓的身高和身形,老板挑了一双加绒的运动鞋,鞋面是柔和的米白色,还有一身带连体帽的加绒外套,藏蓝色的,既耐脏又暖和。老板又额外送了两双厚实的棉袜。
下午上班时,我把林蔓叫到办公室,把衣服和鞋子递到她面前,她却连连摆手,死活不要,脸颊涨得通红,小声说:“老师,我不能要,太贵重了。”我拉着她的手,认真地说:“我家都是男孩,一直缺个妹妹,今后你就当我的妹妹好了,这是我给妹妹的礼物,必须收下。”她愣了愣,看着我真诚的眼神,终于不再推辞,红着脸接过东西,小声说了句“谢谢”,转身跑了出去。
可第二天见到她,她却没穿那件新外套,只换上了那双新运动鞋。我拉住她,问她为什么不穿新衣服,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小声说:“想留到过年再穿,太好看了,舍不得。”我心里一软,没再多说什么,只摸了摸她的头,让她注意保暖。
那些细碎的帮助和陪伴,像一缕缕暖阳,慢慢驱散了她眼底的惊慌。她渐渐敢抬头看我,偶尔还会主动跟我说上几句话,身上的旧衣裳虽然依旧朴素,却总洗得干干净净,整个人也比从前舒展了些,不再像从前那样缩着身子,仿佛终于在这陌生的校园里,找到了一丝可以停靠的暖意。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篇章四:消失
日子在粉笔灰簌簌飘落的声响和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中悄悄流淌,不疾不徐,却带着倒计时的紧迫感。黑板旁的中招考试倒计时牌,数字被一天天擦去、改写,日渐变小,像在提醒着每个人,青春里最关键的战役即将打响。
林蔓也渐渐长高了些,不再是从前那个缩着肩膀、带着怯懦的小姑娘,脊背挺得愈发笔直,清瘦的身形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她愈发用功,像是要把所有失去的时光都补回来,夜深了,宿舍早已熄灯,整栋楼都陷入沉寂,唯有走廊尽头的声控灯还会为她亮起,她就倚在冰冷的墙壁上,就着那点昏黄的光背书,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书页翻动的沙沙声,是深夜里最执着的回响。
她话依旧不多,性子还是安静内敛,可手却巧得很。有一天,我下班走出办公楼,夕阳正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红色,她忽然从旁边的树后走了出来,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纸盒,低着头,脚尖轻轻蹭着地面,显得有些局促。
“老师,这个……给您。”她的声音细若蚊蚋,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把纸盒轻轻递到我面前。我接过打开,里面躺着一串用五颜六色的彩纸叠成的千纸鹤风铃,每一只千纸鹤都折得棱角分明,翅膀舒展,用细棉线串起来,下面还坠着小小的铃铛;旁边还有一条亲手织的白围巾,毛线是最朴素的纯白羊毛,针脚细密而整齐,能看出是花了不少心思织成的,摸上去软软糯糯的,带着淡淡的阳光气息。我心里一暖,连忙说谢谢,她却红了脸,飞快地说了句“老师再见”,就转身跑开了,背影轻快得像只小鸟。回到家,我把风铃挂在卧室的窗台上,风一吹,千纸鹤轻轻晃动,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像她藏在心里的悄悄话,听着就让人心里暖融融的,连带着整个房间都多了几分温柔。
第二天早读课,我特意戴上了那条白围巾去上课。晨光透过教室的玻璃窗斜斜扫进来,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带着初春特有的暖意。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我眼角的余光就瞥见了林蔓,她原本正低头看着课本,察觉到我的身影,猛地抬起头,目光落在我脖颈间的白围巾上,脸颊瞬间就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像浸了蜜的桃花,娇嫩又明艳,连垂下的眼睫都沾着细碎的羞赧,轻轻颤动着。她攥着笔的手明显顿了顿,笔尖在纸上无意识地蹭了蹭,留下浅浅的一道痕,却始终没敢再抬头看我,只让耳尖的绯红一点点漫到鬓角,比我窗台上那些五彩的千纸鹤还要鲜亮几分。我心里暗自发笑,故意抬手拢了拢围巾,白围巾软软地贴着脖颈,暖意顺着皮肤蔓延开来,仿佛还带着她指尖的温度,带着毛线在阳光下晾晒过的清香。
课堂上,我偶尔会不经意地看向她的方向,她总能敏锐地察觉到,然后更快地低下头,肩膀微微绷紧,连呼吸都像是放轻了许多。那泛红的脸颊、慌乱的指尖,还有藏在眼睫后的羞涩,比任何华丽的告白都要动人。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最深情的心意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而是藏在她亲手折的千纸鹤里,藏在她一针一线织就的围巾里,藏在这份见我珍视她的礼物便羞赧不已的温柔里。这份纯粹又真挚的情感,悄悄暖透了往后的每一个晨昏,也成了我记忆里最珍贵的一抹亮色,无论过了多少年,想起那个带着晨光的早读课,想起她鬓角的绯红,心里依旧会泛起满满的暖意。
我以为岁月会如此静淌。我教书,她读书,守着秘密,彼此照亮。直到中考结束,她消失了。
毕业了,不见她来领毕业证。赶去她家,已人去屋空。房东说,她们连夜搬走,投奔远方亲戚。走得无声无息。
空荡屋里,我只在墙角找到她那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我送她的笔记本。扉页上,一行娟秀小字:“刘老师,我会再见的。”
我拿起笔记本,心仿佛也被掏空一块。
那丫头,她叫林蔓。这名字,我从未刻意去记,却早已刻在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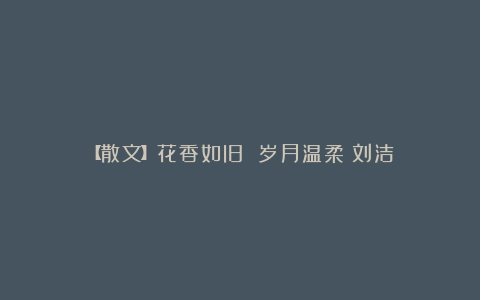
生活照旧。我仍站在讲台,手持粉笔。只是目光掠过她曾坐的靠窗位子,总会微微一顿。仿佛那里,还有个沉默身影,眺望山外。
时光能抚平伤痕,也能模糊记忆。几年后,听说她母亲去世。又几年,听闻她去广东打工了。
只是,她再未回来。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篇章五:归来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云阳镇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记忆里坑坑洼洼的泥路,如今铺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路,两旁栽满了葱郁的冬青;曾经低矮破旧的瓦房,被鳞次栉比的楼房取代,烟火气愈发浓厚。2016年,我调回镇子上另外一个中学教书时,发间已悄悄染霜,眼角也刻上了岁月的细纹,不知不觉间,竟已在讲台前站了大半辈子。
那天,校长突然找我,语气带着几分郑重:“有位爱心企业家专程来咱们学校,要长期资助贫困学生,今天搞个启动仪式,想请你主持会议。”我点点头应下,只当是一场寻常的公益活动,并未多想。
仪式定在上午十点,学校的报告厅里人头攒动,镇里的领导、学校的师生坐满了会场。台上,一位女子正站在发言席前讲话,三十出头的年纪,身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装,长发利落地挽成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整个人显得干练从容,气场十足。她气质卓然,眉宇间透着商界人士的果决,却又藏着淡淡的书卷气,眼神明亮而坚定,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
我坐在主席台一侧,斜斜望着她,总觉得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像在哪里见过,可搜遍记忆的角落,却始终想不起具体的出处,只当是错觉——十八年的时光,见过的人太多,记不清也正常。
她的声音清悦动听,透过话筒传遍整个报告厅。发言中,她聊起自己的成长经历,说起年少时的困境,当谈及当年教过她的一位老师时,语气忽然软了下来,眼角泛起不易察觉的红,声音也带上了一丝难以掩饰的动容:“如果不是那位老师,我可能早就辍学,被生活的重担压垮,走不到今天。她给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黑暗里的一束光,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也有盼头。”
台下响起轻轻的掌声,我也跟着鼓掌,心里莫名泛起一阵酸涩——教书育人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困境中的孩子,不知她口中的老师,是哪位同行。
发言结束,仪式圆满落幕,我收拾好桌上的稿件,起身准备离席。就在这时,她却穿过散去的人群,径直朝我走来,脚步急切而坚定,目光紧紧锁在我身上。
我心里猛地一紧,莫名生出几分慌乱,下意识地想避开,可她已经走到了面前,距离不过几步之遥,再也躲不开了。
“刘老师,”她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目光里满是试探与期盼,“我是林蔓。您……还认得我吗?”
林蔓。
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竟是她!那个十八年前突然消失、让我牵挂了无数个日夜的丫头!
我猛地抬头,撞进她的目光里。那双眼,早已不是当年蒙着惊慌的清泉,而是变得明亮沉静,像深不见底的潭水,从容而有力量。可在那潭水深处,分明还映着十八年前的影子——那个瘦得像豆芽、眼神里藏着怯懦与感激的少女,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
一瞬间,脑中轰然作响,过往的岁月如潮水般涌来,食堂里的匆匆一瞥、走廊灯下的背书身影、千纸鹤风铃的脆响、空屋里那本写着承诺的笔记本……所有的牵挂、遗憾、期盼,都在这一刻汇聚心头。我的手抖得厉害,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酸涩得发疼。
她看着我这副模样,忽然笑了,眼圈却瞬间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没有落下。“老师,我回来了。”这五个字,说得轻而坚定,像是跨越了十八年的时光,带着无尽的思念与终于得偿所愿的释然。
“林……林蔓……”我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却语无伦次,只剩下满心的震惊与激动,泪水也不受控制地模糊了视线。
“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您。”她眼中的泪终于滑落,顺着脸颊轻轻流淌,却依旧笑着,“我从广东打工,到后来创业,一路走过来,最想做的就是找到您,好好回报您。当年若非您,我早就在辍学后,被生活的苦压得喘不过气,哪有今天。”
周围渐渐静了下来,几位好奇的同事凑近了些,其中一位轻声问道:“林总,您和刘老师……原来是旧识啊?”
她没有理会,目光始终紧紧凝视着我,带着深深的眷恋与感恩:“我妈走的时候,意识已经不太清醒了,却还一直念着您的名字,说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您的恩情。”
“她说,您当年给的哪里是几块肉、一点学费啊,您给的是一个孩子的尊严,是活下去的希望。”
“她说,世上还有您这样的老师,孩子的心就永远亮着,就不会走歪路。”
她的话一字一句,像温暖的溪流,淌过我的心田。一辈子教书育人,不求回报,却从未想过,自己当年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食堂里拨给她的几块肉,谎称是奖学金的工资,悄悄压在药碗下的零钱,竟被她们母女记了一辈子,感念了一辈子。我再也忍不住,用手背抹了一把脸,声音哽咽:“别这么说,都过去了,都是我该做的。”
“过不去。”她轻轻摇头,目光坚定得不容置疑,“于我而言,永远过不去。您当年那句’这是学校发的奖学金’,我记了一辈子,它支撑着我熬过了最苦的日子,让我知道,我值得被善待,值得为更好的生活去拼。”
中午的宴席上,她特意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双手捧着酒杯,微微躬身:“老师,我敬您一杯。”
我接过那杯酒,只觉得重若千钧。杯中的酒液清澈,映着她含笑带泪的眼眸,也映着我自己泛红的眼眶。
“老师,我先喝。”她话音未落,便仰头一饮而尽,毫不犹豫,动作干脆利落,早已没了当年的怯懦。我端着酒杯,凝视着她——从当年那个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丫头,到如今亭亭玉立、独当一面的企业家,她真的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能为自己遮风挡雨,还能为别人撑起一片天。而我,不过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为她挡过一缕微不足道的风,递过一把微不足道的伞。
我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烈酒入喉,辛辣的滋味瞬间蔓延开来,却化作滚烫的热泪,顺着脸颊汹涌而出。十八年的牵挂、十八年的期盼、十八年的欣慰,所有积压在心底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奔涌而出,再也无法抑制。
她轻轻牵着我的手。“老师,慢点喝。”她的声音依旧清悦,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像极了当年她递我围巾时,那藏在羞涩里的暖意。
十八年光阴流转,云阳镇变了,我们也变了,可那份藏在岁月深处的牵挂与感恩,却从未改变,反而在时光的酝酿下,愈发醇厚,愈发动人。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篇章六:念念
那天下午,我们长谈。
她说起别后经历。当年,她们投奔远方姨妈,日子过很清苦。母亲病弱,她进南方一家外企,后创业。凭韧劲与才智,公司风生水起。人前是女强人,可每当夜深人静,她总会想起那间简陋办公室,想起总“不经意”帮她的班主任。
“老师,您知道吗?”她眼中闪光,“撑我走过所有坎坷的,非宏大理想,也非坚强神经。”
“是您当年,偷偷放我抽屉的那个煮鸡蛋。”
“它让我相信,世界终究温暖。”
次日,她给我留下一张鞋店的购物卡,悄然离去。
我生活依旧。她常寄保健品,年节电话最先响起。我回信:“林蔓,勿念,师安。你一切安好,便是为师最大欣慰。”
去年秋,她带女儿回来看我。小女孩眼睛像她,黑亮亮的。她让孩子唤我“爷爷”。
小姑娘甜甜叫了声。我掏出备好的巧克力,递给她。如同多年前,从抽屉里掏出那个煮鸡蛋。
我说可不能叫爷爷,一下子把我叫老了,林蔓,以后叫我洁哥,我好像大你七八岁,叫哥最适合,孩子叫我伯伯吧!
哥,洁哥。
林蔓看着我叫声哥,笑了。笑容干净纯粹,一如当年。
她说:“洁哥,您知道吗?我给这孩子取的小名,叫’念念’。”
“念念不忘的念。”
我心猛地一颤,眼一酸。我转过身,假意去看院里那棵树。
花香如旧,岁月温柔。那一点善意,如星火,终成照亮归途的灯。
作者简介: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刘洁,男,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北戴河创作基地文学院签约作家, 河南省散文作家协会会员,南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南阳民俗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州风情》文学顾问,《百姓文化视点》签约作家。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中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更多作品请点击底部“ #刘洁散文作品集 (部分)▪目录”阅读。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