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别人都是什么情况下读的《伤逝》,我是在中学语文课堂读到的。老师说,这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结合鲁迅关于“娜拉”的一个演讲,老师细细剖析了这篇小说里失败的爱情。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生,我自然对老师的话照单全收,都信了。
恰好我也学过陆游那篇“钗头凤”,红素手黄藤酒什么的,讲的是那个叫作封建礼教的东西,如何毁掉宋朝诗人的恩恩爱爱。鲁迅够狠啊,他明明也一直抨击礼教,但写下唯一一篇爱情小说,偏偏不提礼教这事,他让封建家长的阻拦失效,让年轻人私奔成功,而后演绎一出婚姻仍旧失败的好戏……他比陆游更狠些。
我想这就是老师讲的作文要出奇制胜,也是鲁迅讲的“不吃别人嚼过的馍”吧,根本没想过,鲁迅写这么一场爱情,深藏骗人的成分……
文本细读,的确在爱情以外读不到别的
我同意余华那个说法,当年读鲁迅文章“味同嚼蜡”,口感很不佳。当然我们后来都承认鲁迅的所有文字都属于良药苦口。要找原因的话,一方面他那时候刚兴白话文,语言还没通过充分的写作实践进化到纯熟境界;另一方面,要表达独有的恨意和狠意,也得用独有的语言,鲁迅不可能有染启超胡适当年的语感,也不可能用后来张资平张恨水的语言。还有一点,似也不应否认作者濡染了乃乡师爷文风,笔墨刁钻,不易测度。
万千原因,那一代人中,仍是鲁迅用文字挖得最深,写得最牛。如果没他,二十世纪(至少前五分之四时段)中国文学真的让人很抬不起头。
《伤逝》写于1925年10月。说来我跟这篇小说还是蛮有缘分,课堂学过,后来参加工作到一个杂志求职,笔试给的题目前头是基本语法,后面是分析《伤逝》。我以笔试成绩第一被录用,改过我卷子的副总编,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前辈跟我说:你把《伤逝》分析得不错,不过我顺便告诉你,鲁迅这个小说不光是写爱情,还写进了兄弟感情。
我当时有点吃惊,考虑到周氏兄弟和北大的渊源,我记住了他这话。稍后我又把《伤逝》小心翼翼读了一遍,涓生和子君,一男和一女……娜拉出走了,娜拉又死了。真的无法完全相信副总编的话,但又顾及他北大身份——他应该是周氏兄弟嫡传弟子的弟子的弟子……最后,只能说半信半疑吧。
慢慢发现,要想不被骗,工夫在文本外
我九十年代开始学习写小说时,基本不读鲁迅,我想我肯定不会沿用鲁迅的语言去写文章,从中学到大学读到的鲁迅文章,已经够多,蜡也嚼够了。另外,考上军校靠着全额供给制才开始吃饱肚子,我觉得我成长阶段积累下对于这世界的苦感,差可与鲁迅相比。对什么有兴趣读什么,借学外语机会多读外国书,占用了我大部分时间。不读或尽量少读本国书,现在想想其实也失之偏颇。
这几年闲得没事干,终于搬出早年开书店购入的鲁迅全套作品,还有研究他的人写的那些书。
旅居日本东京后我也发现了自已另一浅陋:以前太轻看日本小说了。其实,从鲁迅那一代算起到现在,日本出了夏目、芥川、谷崎、川端、森鸥外、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津岛佑子、多和田叶子……岛国的现当代文学牛人没断过线,像一川珠子串在一个多世纪时间线上。而我们那边呢,只鲁迅一个拿得出手,勉勉强强张爱玲也算可以,沈从文钱锺书居然大半辈子坚决不再写小说(我去……这都什么事儿)。既然只有一个鲁迅可供琢磨,闲来只能多琢磨琢磨他了。
就说这《伤逝》吧,里面除了爱情重伤,居然还藏着兄弟失和这块伤疤。
感谢王晓明王锡荣杨智深吴俊这等承前启后的学者,也感谢竹内好伊藤虎丸和丸尾常喜这些独辟蹊径的域外研究者,他们的文章,已经说得很明白。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依据的那些材料。
比如当事人之一周作人早年给曹聚仁信里这样写过:“《彷徨》中《弟兄》前面有一篇《伤逝》,作意不易明了,说是借了失恋说人生固然也可以,我因了所说背景是会馆这一’孤证’,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丧失……但对先生私下不妨一说……”。
知堂不是说了这么一次,在晚年回忆录里,他又明确说了一遍:
“《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周作人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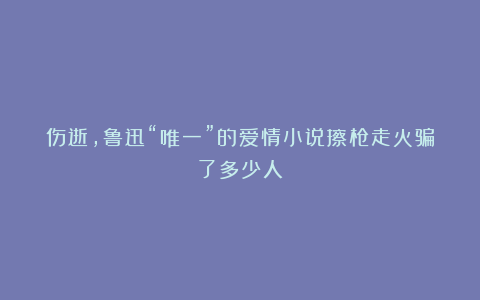
周作人这些话和他先后如一的用意,在我上学时是被老师屏蔽掉的。或者,老师也不知道有这样隐曲的材料,照本宣科,讲了明面能讲的东西。
我在读到这些材料时,像是从知堂手里接到一把钥匙,以前的疑问种种,基本都可以解释通了。
读书之余,我也作了如下分析:
一,鲁迅为啥要写这篇“爱情小说”。据鲁迅日记,《伤逝》完稿于1925年10月21日,在那之前,他曾于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为主题的演讲,后收进了杂文集《坟》。就鲁迅当时的阅读所及外国文学作品有易卜生《玩偶之家》,以及那一时期女性独立成为中国社会热门话题,鲁迅为此构思一篇爱情小说是完全说得通的。因为文本里能够读到的只是男女之情,读者不作他想实属正常。
但也应意识到,鲁迅恋爱经验并不丰富,甚至说少得可怜,他的一生除去为数不多的绯闻,有据可查的爱情仅有和许广平这一例。他写“爱情题材”,不管现实经历还是心理感受层面,可供挖掘的东西都很有限。即使不考虑周作人的“解读”,也极易导致一个有趣的猜测:它不宜完全当作一篇爱情小说来读。
在时间上,1923年兄弟失和,做演讲和写此文都在之后。
二,鲁迅对涓生的刻画有违男女之情的常理。如吴俊先生在《暗夜里的过客》中分析的那样,兄弟失和后,鲁迅写了一批以“牺牲者的被弃和愤怒”为主题的作品,《伤逝》是其中“最扑朔迷离却又耐人寻味的”一篇。通过涓生之口,把一位女性(子君)放到了被动不利和应该受指责的地位,爱情破裂,主要是由子君造成的;她后来死去,涓生不过只具有情感上的责任和道义上的自责,丝毫没有事实上的负担。就涓生(实际是鲁迅借这一角色代入了自已情感)这一方,自始至终都在自我开脱,显示出推脱责任的心理。他对子君的爱,在子君做出离家出走这么大牺牲之后,却很快由热烈变为平淡,继而是失望、不满、苛责。作为一个男人,这一系列表现显得非常自私和冷酷无情。仅就文本呈现的子君所作所为来说,完全没必要受到一个爱过她的男人如此毫不留情的谴责。这样有悖常情,写到这个程度,完全可以看成作者是把自已久积的怨愤(由兄弟失和引出的)捎带进了一篇“爱情小说”里。
三,鲁迅处理“兄弟失和”话题时无路可走,只好借“爱情”影射兄弟情。事实已经证明,他无法专门就兄弟失和写文章。二人当年失和,留给时人及后人种种猜测,其中一些说法极为不堪。简单来说,哪怕仅仅出于“家丑不可外扬”这一传统“规矩”,兄弟之间也无不三缄其口。就鲁迅的性情,不大可能将之压抑于胸,要想纾解表达,只有曲笔一途。
因此说,这是一篇擦枪走火的爱情小说。他最初“立意”也可能只是要写写爱情,给模仿“娜拉出走”的女性另一个警告或提醒。但到了下笔之后,稍有小说写作经验者都会知道,故事常要挣脱作者“设计”,自顾自开步走。“我(涓生)”这个人物,把作者完全代入了《伤逝》的文字洪流,借主人公爱情婚姻的失意以及由此生出的不满和怨怼,自觉不自觉地“夹带私货”,把兄弟失和引出的不满和怨怼带了出来,发泄了出来。悼爱情时顺带也“悼”了失去的兄弟情,而且让后一种哀怨不小心占了重头。总之,这完全可视作鲁迅写作中的一次“擦枪走火”。
鲁迅素有面对敌手和假想敌时得理不饶人的个性,这篇“擦枪走火”并非孤例。前有《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后有“答徐懋庸”那封信,虽“走火”原因、方式不同,但都显示了他不愿压抑自已,要借文字释放胸中怨气的习惯做法。
《伤逝》的独特还表现为文本风格
最后,我想试着分析一下鲁迅《伤逝》的文本风格与日本私小说之间的某种关系。
鲁迅早年在留学日本期间,即开始着手翻译日本小说,阅读和购买了日本当时出版的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森鸥外、菊池宽、国木田独步、佐藤春夫、志贺直哉等人的不少名作。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他去世前,通过跨洋邮购和日常逛上海内山书店等,基本购齐了同期日本主要作家的作品全集。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据王锡荣先生考证,菊池宽《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之于《阿Q正传》,国木田独步《巡查》之于《在酒楼上》,佐藤春夫《形影问答》之于《影的告别》……每组前者对后者都有一定的影响(见王锡荣《鲁迅学发微》)。
我想这也很自然,我来日本五年多,就接触到的在日华人小说家而言,从陈永和、哈南、亦夫、元山里子、黑孩、弓也直到更年轻的琪官等人,其作品都可以看出受过日本小说的影响,文本对比阅读中极易发现。正如郁达夫当年受佐藤春夫《忧郁的乡村》直接影响,写出《沉沦》,被日本评论家称作“中国私小说”一样,可以合理地推定,鲁迅《伤逝》以内心独白方式剖白男女私情,发泄内心怨愤,应该也是深受日本私小说写作方式的影响。
私小说作为日本近现代以及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存在,最早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作家有田山花袋(代表作《棉被》)、葛西善藏(代表作《湖畔手记》)、志贺直哉(代表作《在城崎》)、尾崎一雄(代表作《虫子的二三事》)等人,稍后,太宰治(代表作《人间失格》)、谷崎润一郎(代表作《痴人的爱》《疯癫老人日记》)成为写作私小说的一代大家。资料显示,出于对谷奇润一郎的兴趣,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即购买并收藏了日文版《痴人的爱》(该书首版于1924年)。仔细对比阅读,《伤逝》的叙事语感,男主人公对男女私情层层剥皮,以及对所爱之人彻底失望后的谴责情绪,都与私小说《痴人的爱》有颇高的相似度。
《伤逝》既借日本私小说形式达成了鲁迅作品中独一无二的“爱情”表达,同时也借“爱情失败”这杯酒,浇了“兄弟失和”的块垒。或许可以说,这篇小说当年“骗”过我做学生时的眼光,随着时间推移,而今渐渐“水落石出”。真难为鲁迅先生了。对于专门的研究者来说,这“发现”或许没啥大惊小怪。但对于一般读者,如果错过这一层理解,无疑是个遗憾啊。
202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