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 ,作者王东杰
社会科学研究杂志
《社会科学研究》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1979年3月创刊,致力于研究问题、锻铸新知、繁荣学术、昌明文化。
王东杰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雅各宾党人宣布:“一个自由民族的语言应是唯一的,且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The language of a free people must be one and the same for all)。”[1]一语道出了语言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两百年后,法国政治学家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指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必然伴随着语言状况的改变:“在帝国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之间以有文学传统为依托的通用语言进行沟通,而每个地区都有方言”。进入民族国家时期,方言“先被当地社会精英所抛弃,又被大众教育冷遇”,无可挽回地趋向“灭亡”。相应地,“民族语言”则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反对帝国语言的多样性象征”,又是众多地区性方言的掘墓人。作为一个国家“剩下”的唯一一种语言,它同时是“语言标准和政治规范”。[2]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亦是与方言文化相关的地域性共同体的瓦解过程。[3]因此,语言民族主义不但意味着一种新语言(民族统一语)的诞生,也意味着许多旧语言(方言)的湮灭。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无疑是语言民族主义浪潮的众多追随者之一,不过,这并不等于它在任何方面都对其原型亦步亦趋。李方桂在1947年的一段评论中注意到:接受政府所颁行的国语标准,并没有妨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用方音去诵读文学文本,也没有使得方言的“声望”受到什么明显损伤。[4]确实,中国国语运动的领袖们大多对方言抱有一种积极而友善的态度,即使不将其看作家属,至少也当作可以共处的邻人,而不是一定要打倒的对手。国语和方言之间虽然也有紧张,但无论如何还没有发展到敌对地步,在多数情形下,反而是并辔骈行,形成了一种“双语”体制,并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可。同时,“国语”也常被看作一组可以在某种范围内适当移动的语言光谱:只要人们能够大体无障碍地沟通,国语的能事已毕;国语运动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把标准语说得字正腔圆。
在这些方面,国语运动和欧洲原版的语言民族主义主张显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此一特色似乎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尽管也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诸子对国语和方言的互补有过不少论述,并且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文化人,对方言文学和方言文艺的倡导和实践也一直没有停止,但对于这些现象,论者往往是点到为止,多数研究者仍然倾向于把国语运动看作国家(中央)政治和文化权力对(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文化实施的“文化宰制”。[5]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既存研究对中国国语运动的思考,基本是通过西欧、日本经验的透镜进行的,故而多见其同,而鲜见其异。
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有关论述篇幅虽短,却深值注意。他把中国“语言改革运动中文字统一化和多样化之间的论争”,与“中央集权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围绕着中国国家形态问题的政治竞争”,视为两个同构而平行的现象。费氏同意,无论是“语言联邦主义”者,还是“中央集权者”,都处在“民族统一”的话语框架中,但前者所说的“统一”乃是“各个分裂的地方社会的集合”,后者更重视“抽象地重新组织起来的民族”。费约翰对两派平等对待,并注意到方言和国语之间的复杂性:对方言的认同未必即是对统一的背叛,相反,甚至可能是国家认同的另一种形态。[6]
与大多数研究取向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国语运动中那些“不统一”的面相:乍看起来,它们和国语运动的旨趣背道而驰,但它们的确就存在于国语运动内部。这些面相主要表现为两个主张,而恰与那位雅各宾党人的理想南辕北辙:“国语运动”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只剩下“唯一”一种语言,也不要求所有人的“国语”都能说得一模一样。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都不曾完全变为现实,但这里边的关键显然不是其在客观上是否可能,而是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此一原则。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中国国语运动明确揭出了“不统一主义”的旗帜,且将其列为宗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特立独行之举;若考虑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浓郁民族主义思想氛围,此一主张就更显得不合时宜,值得细加检视。
一 “国语不统一主义”
1906年,陆费逵在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人之所以“知有乡谊而不知有国家观念,知有省界而不知有国家种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言不一”。因此,要凝聚“全国人心”,就要从“统一语言”做起。[7]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基本思路的高度概括。显然,自一开始,方言就和“分省界、判同乡之成见”联系起来,[8]成为国语运动主要的针对对象。20年代中期之后,在有些“革命家”眼里,方言更是成为“封建”势力的表征。[9]与此同时,作为铸造“国家观念”的利器,国语则被提升为确立“国民资格”的要件。1923年,黎锦晖宣布:“不懂中华国语的人,当然没有中国公民的资格。”[10]不久之后,沈恩孚也提出:“不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懂得国语,假使不懂国语,就是没有国民的资格。”[11]
不过,对方言纷歧的批判,是否即意味着国语运动应把打倒方言作为一个努力目标?按照“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原则,答案自然是肯定的。1902年,《外交报》刊发的一位英国传教士的演说便预测:“中国苟能永远自主,则各地土音,必尽易为官话。将来铁路大通,往来便易,复多设学校,教化齐同,土风之不操,有断然者。”[12]那么,语言的统一即是“土风”的绝灭。1910年,由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发表了一篇倡导国语统一的文章,提及西方“宗主国”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土语”,“以消杀其故国之思”。[13]这些例子隐含了两个假定:语言塑造了人的认同,而方言所代表的认同和国语的认同是对立的。
中国国语运动同样是从第一个假定出发的,但对于第二个假定,则有不同的看法。它的不少领袖人物都明确宣称:国语和方言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统一国语的同时,也应容许甚至鼓励方言的存在与发展。比如,早在1911年,陆费逵就批评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不能囊括各地方音,担心“将来各省之音,势必归于消灭”。[14]作为国语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这段话清楚表明了他的态度:国语统一不能以方音湮灭为代价。
这方面更为自觉的思考是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推广而展开的,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胡适所说的“活文字”的概念,它被拿来论证方言写作的合理性。朱执信提出:对于“一般”中国人来说,“文话是中风麻痹的,国语是还没有活的,真正活的还是土语”。因此,大部分写给本地人看的文章都可以“用土话做”。[15]二是歌谣运动,其初衷本是搜集民间文艺,为国语和国语文学提供“最需要的参考材料”,但如同周作人所说:“歌谣原是方言的诗”,[16]二者具有一种天然的亲缘性。在歌谣运动中,如何记录方音和方言日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7]这不但推动了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开展,也刺激了学界对方言文学的关注。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属1926年初顾颉刚搜集整理的《吴歌甲集》出版,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都给此书写了序言,纷纷为“方言文学”背书。
胡适
新文化人对方言和方言文学鼎力相助,出于多方面考虑:既有实用性质的(即“与普通人发生交涉”的需要),又有美学性质的(方言的表现更为活泼),或从价值论立场出发,或来自学理的考量。就方言与国语的关系而言,他们多强调二者互为依赖,密不可分:方言是国语的形成条件,也为后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源。钱玄同提出:“方言是国语底基础”,它“是帮国语的忙的,不是拦国语的路的”。周作人建议,方言中有许多可以补充国语不足的表述方式,应“正式的录为国语”。胡适更指出:“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这个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国语虽然“优胜”,也还是“方言”,与其他方言相比,性质并无根本不同。语言如此,文学亦然。胡适强调:“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方言文学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渐渐为大家接受,才成为“公认的国语文学的基础”。因此,“国语的文学”是“”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的”,而其最终“仍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18]
其实,胡适根本就怀疑“国语统一”的可能:“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语言总会变化,“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使其整齐划一。更重要的,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也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胡适认为,在国语文学之外,中国还“有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即是吴语文学和粤语文学。它们各自表现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和“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应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19]直到晚年,他还重申:“当初我们提出国语文学时,我们不注重统一。”针对台湾的国语推广运动,他也在各种场合呼吁,对方言“不要严格的限制”,应听其“自然”。[20]
俞平伯和钱玄同的态度也不遑多让。俞氏宣布:“我赞成统一国语,但我却不因此赞成以国语统一文学。”从事实上说,“方言文学的存在——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我们决不能闭眼否认的,即使有人真厌恶它”。从价值上说,“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因为它才是“现在真的活人们口中所说的”,最能反映“真我”:“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热稔熟;惟有它,于我无纤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诸君之前。”[21]这里的理由和朱执信相似,但更侧重从“个性”角度立论;“牙牙学语”一句,尤其刻画出一幅天真纯洁、不被社会“污染”的图像。这些都意味着,方言自有独立价值,不须依附于国语。钱玄同说得更直接:方言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它们作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22]
值得玩味的是,俞平伯特别在文中声明:自己的见解“自然和国语热的先生们有点背道而驰的样子”。[23]钱玄同便专把此话拈出,“一本正经”地反驳道:“平伯先生提倡方言文学,我完全同意;但他认为提倡方言文学跟提倡国语文学有点背道而驰,这话我却不同意。”其实,俞平伯不过是在讽刺那些“国语热的先生们”,钱氏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他故作庄语,乃是自觉配合俞氏演一出双簧。俞平伯挖苦的是什么人,钱玄同清楚得很——即是一些“所谓教育家也者”:
他们最爱咬文嚼字,他们最爱凿四方眼儿。他们开口便要分别怎样是文,怎样是语;什么是官话,什么是方言;哪个字是文体绝对不用的,哪个字是语体绝对不用的;国语文法应该怎样规定,国语词类应该怎样限制;文雅了又不好,俚俗了又不好(如只许用“的”,用了“之”就说太文了;只许用“头”,用了“脑袋”又说太俗了);欧化了又要反对,民众化了又要反对……
钱玄同主张,国语应“活泼、自由、丰富”,而要致此效果,就得兼容并蓄:“采自活语,方能活泼;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然后丰富。”方言、外语乃至文言,不拘一格,皆在采获之列。似“教育家”们这般“违反自然、缚手缚脚”,当然令他生气。[24]
钱玄同多次批评,“现在那种顶着国语统一的大帽子来反对土音方言的议论,高谈平民教育而完全不顾——甚而至于要排斥民众的活音活语的见解”,比“守旧”言论“更要不得”。[25]此时新旧对决胜负已定,旧派已不足为虑,新派中的教条言论,反有成为一种新专制的危险。钱氏对“所谓教育家”的反感,其故在此。刘半农更指出,不要“把统一国语的’统一’,看做了统一天下的统一”。后者的目的是“削平群雄,定于一尊”,但语言有其“自然的生命”,不能用人力“残杀”。“我们必不能使无数种的方言,归合而成一种的国语;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在无数种方言之上,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来。”[26]直到30年代中期,林语堂用吴语撰文,大张“方言文学”的旗帜,理由也还一样:“为啥要提倡方言文学?……为只方言自身本来与啥个国语呒不分别,像煞楚霸王与汉高祖,成则为帝,败则为贼。但是因为汉高祖一旦为帝便要尊孔,不敢勒浪儒家帽子头上撒泡尿,失脱不少沛郡无赖本色,实在可惜,……还是方言俗语来得灵活。”[27]这些理由都超出了实用考虑,而与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反对专制的价值取向有关。
尽管多数新文化领袖都支持方言和方言文学,但还没有激进到主张以方言代国语的地步;有之,则是孙伏园。孙氏预言,随着国语统一和中国字拼音化的发展,将来“必有革新派起来,主张以各地方言代替国语,又必有今日被人认为洪水猛兽的国语运动中的末代子孙出来拼死地反对,但到底还是反对不了”。那时“京语一定自成一种文字,取得国语的七八分遗产,相对于今日之意大利文字;豫、鲁分得的遗产较少,只相当于今日之法、比;长江流域更少,仿佛今日之英、美了”。这全靠中国字拼音化之力。因为一旦拼音文字成功,“用拼音文字代替拼音文字”就很容易了。届时“无论你怎样主张一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语,一世界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语,理论上怎样充足,事实上怎样便利,但于方言文字的发展仍然是无碍的”。由此看来,“现在”提倡方言文学还“太早了”,因为方块字还没有废,“方言文学与非方言文学其间的差别到底有得了多少,还不是就是那么一回事吗?”[28]
孙伏园的思路是:西方人是先有统一的拉丁文字,再有写方言的白话文。因此,把文言比作拉丁文实非其伦:“拉丁文在欧洲所以渐渐失去势力,缘故是各地的语言都自己成功文字,渐渐的取拉丁文的地位而代之了。但是这件取而代之的事,里面含着一个重要分子,便是以多代一。”而在中国,“文言文的地域是十八省等等,白话文的地域何尝不犹是十八行省等等。所以,以白话文代文言文,止是以一代一”,还不是“各地中国人自己所有的语言文字”。若“用语言学上循序渐进的步子来衡量”,文言和白话其实“同站在一个阶段上”,尚不能与“英、法、德、意各语代替拉丁文”相比。因此,“现在我们的路只有一条,就是赶紧把我们的文字改成与欧洲的拉丁一样”;及至“以拼音文字统一全华”之后,再“用北京语、齐鲁语、江浙语、闽粤语代替”之,那才是真正的进步。
孙伏园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英、法、德、意各语代替拉丁文”的过程,也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和欧洲诸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与中国民族主义重在国内统一的立场截然相反。事实上,按照他的看法,国语运动的终极目标倒成了语文的分裂而非“统一”。好在大多数论者并不这般食洋不化,跟从西人亦步亦趋,而是希望同时维持“多”和“一”的平衡,既不是“以多代一”,也不要“以一代多”。
1920年,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提出:统一国语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把各处的方言都改变一些,使他们趋于折衷,成为统一”;第二种则“不求改变方言,只求个个人除了方言之外,还能说第二种同一的语言”。在张士一看来,第一种办法只能造成一种“混合语”,不能真正实现语言统一;可行的是第二种办法。他的理由是,方言根植于社会,“寿命很长,难死得很;要强制去消灭他,或是改变他,是做不到的”;但一个人“学习第二种语言”却是可能的。[29]其时张氏正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就国语的语言标准问题进行大辩论,后几位都是所谓“混合语”的支持者(后来有所改变,那是另一回事),[30]但对于方言的态度则并无分歧。张士一所提出的,实际是国语与方言并行的“双语”制。而这也是周作人的想法:在“统一的国语之下必然仍有各地的方言”,要解决它,“只须国民于方言以外必习得国语”即可,好在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难事”。[31]
1926年初,由一批国语运动积极分子倡议,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展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在黎锦熙起草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中,“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被确定为国语运动的“两大宗旨”,它们各自又包含两个层次:“国语统一”兼有“统一”和“不统一”两面,“国语普及”也兼具“普及”和“不普及”两面。《宣言》强调:“国语统一,并不是要灭绝各地的方言”。方言不但于“事实上不能灭绝”,在“文学上”亦有其独特“价值”。从国语统一的主要途径看:在教育方面,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应学会国语;“僻陋的农村、不交通的乡镇”可以不说国语,但须“能够写得出表示国语的拼音文字,能够读得懂一切国语的书”,此即“统一”。一般平民则“不必一定要学习标准的国语”,可以用注音字母书写其方言,此是“不统一”。在文学方面,“国语的文学”是“统一”的,民间文学则可使用方言,以保持其“真相大明精神活现”,又是“不统一”的。“总而言之,统一的国语,就是一种标准的方言;不统一的方言,就是许多游离的国语。各有用途,互相帮助,这就叫’不统一’的国语统一。”[32]
文章虽出自黎锦熙之手,但既题为《大会宣言》,自应代表会员共识。从国语文学运动初期的“不注重统一”,到将“不统一”明定为“宗旨”,国语运动保护方言的意识愈益自觉,历历可见。
黎锦熙
“双语”构想获得了多数语言学家认可。40年代,罗常培曾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一次常委会上提出:“国语务求统一,应该全国一致推行国音国语,不必再顾方言。”吴稚晖当即反驳:“方言是自然存在的,即使将来国语通行全国,而各地方言仍会在各地老百姓嘴里应用,决不会归于消灭。”[33]1946年,吕叔湘声明:“咱们提倡国语,可不是要消灭方言。”[34]王力则提出“提倡国语,拥护方言”的口号。[35]不但不“消灭”,还要“拥护”之,态度更为积极。1959年,赵元任在台北讲演,也还是坚持国语运动的初衷:
推行国语最后目标是否应达到一国一语之程度?一国一语看怎么讲,全国人人都能用国语,这是一个标准。还有一种就是全国人人都不用乡语,这又是不同的问题。第一种是我们应该努力求达到的,并且我相信能够达到。第二种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36]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界兴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下简称“拉丁化”)。它以国语运动为假想敌,指责后者“强迫”各地民众放弃自己的语言,去学习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所谓国语”,实际就是文化“侵略”和“独裁”,戕害了“各地民众语文以至文化的发展”。为此,他们明确揭出“反对国语统一”的旗号,主张将汉语划分为几个方言区,以方言区为单位,制定拼写方言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当然不是不要语言统一,但他们主张,共通语应由方言自然发展、融合形成,各地方言都应有“均等的机会”去“参与”其创造。这是语言上的“民主”原则,和“官僚的国语”的精神截然相反。[37]
问题是,国语运动本无打压方言之意,其与拉丁化的诸多主张只有技术差异,并无实质不同,对于这种政治先行的批判当然不服。1932年9月,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语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左翼人士“把国语统一的意义,看得太死”,唯恐其“妨害了,或阻止了,各地方音的发展”。其实,“’国语统一’并不是’中央集权’,多少倒有点像’分治合作’或者’均权主义’”。国语运动不但不会消灭方言,而且提倡各地方言“尽量发展”,亦努力“吸收”某些方言成分。[38]
不久,黎锦熙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语“不”统一主义》,先在北平《文化与教育》旬刊连载三期,之后又由《国语周刊》分两期转载,极受国语运动方面的重视。其实,此文不过是对《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宗旨的重申,其中有一大段根本就是原文照录。但这次它更具针对性:在《宣言》中,“不统一”只是国语运动两大宗旨中第一个宗旨里的一个层次,此处则正式升华为一种“主义”,且以文题方式表示,重要性明显上升;其次,文章举出教育部颁布有关法令中的不少条目,指出它们都是根据“不统一”原则确立的,表明这主张已见诸行事,绝非空言;第三,文章在结尾处强调:“’国语统一主义’,为的是全民族精神之团结;’国语不统一主义’,为的是各地方特性之利导。”[39]将“统一”和“不统一”的关系揭示得更清晰。对比两篇文献可知,这层意思乃《宣言》所未言,十有八九是在与拉丁化交锋过程中发挥出来的。
拉丁化醉翁之意本不在酒,黎锦熙等人的辩白自然无用。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大家其实都反对废止方言。
二 “双语”制的实践
早在西周时期,华夏诸国就有一种共同语言,时称“雅言”,[40]但并未成为遍及社会的要求。后世尽管也有少数人如顾炎武提出,“友天下之士”不应“操一乡之音”,[41]可是也不具任何强制效力。在日常生活中,共通语并未享受更多青睐。除了特殊情况,很少有人把官话当作首选语言。[42]即便小儿念书,大多也都采用乡音授读。这种情形不但普遍,也被认为理所当然。只是到了清末,情况才开始变化。严复在1898年的一篇文章中,讥讽中国“当轴贵人”:“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甚为可“鄙”[43]按“楚囚”一词,典出《左传》:“乐操土风,不忘旧也”,被称为“君子”之行,自来世无异词,到了严复这里却成为鄙陋之征,时代风气将变,于此可觇。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顺利改变积习。1914年,胡适在日记中感慨:“吾辈少时各从乡土之音。及壮,读书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读遂不复注意。今虽知其弊,而先入为主,不易改变。”[44]这是力不能,不是心不愿。然也有人恰好相反,虽然会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却很少说,甚至根本就不想学。这里举三个文化学术界人士的例子。
一是傅振伦。他的家乡河北新河,离北京不远。傅氏1929年自北大毕业,一直在学术界工作;而且是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参与组织中日世界语学会,编有《英汉双解基本世界语字典》、《汉语世界语辞典》等。但他一辈子只说方言,不讲国语。他自己的解释是:“北京笑’南宫冀州人,说不清星辰日月肉和人’,我怕脱离父老乡亲,不敢向乡里撇’京腔’,故说话不改乡音,且仍沿土语。”[45]
第二个例子是傅斯年。据赵元任讲,傅进北大不久就学会了北京话,但回家一张口便被嘲笑:“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这么一笑就把他的北京话给笑了回去,把他本来的’闪董料秤’的话又笑回来了”。1924年,赵元任与傅斯年在柏林相遇,“那时候好几个中国同学虽然多数都不是从北京来的,但是说话差不多全是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就只有孟真老是他的’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声调”。[46]其实,傅斯年对国语运动一向积极关注,[47]不过他也的确认为,“中国的国语完全统一”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了。[48]过渡期既如此漫长,自己就一口“闪董料秤”话当然也无所谓。
第三位是吴稚晖。陈存仁曾在回忆录里说,吴平日说话,都是“一口无锡土话带一些常州的尾音”。有次陈终于忍不住,请教这位读音统一会会长、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语统一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以自己从不说国语?吴稚晖遂大谈一番国语统一的意义,紧接着便称自己的国语其实“相当好”。吴一向滑稽搞怪,陈存仁以为他这也是开玩笑,“不禁哈哈大笑”。吴知其不信,遂约他翌日再来:
到了次日下午六时,我准时而去,稚老却换了一套中山装,见了我一开口说的就是爽朗而清脆的国语,讲得非常流利,这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接着就用演讲的姿势说:“中国一定要语言统一,注音字母是我和黎锦熙等创行的,希望能像英文的’字母’、日本的’片假名’、韩国的’谚语字’,用拼音来统一全国的言语和广泛地推行识字。”他讲这些话全是用国语说出来的,一些不带无锡土音,我佩服得不得了。[49]
刻画生动鲜活,虽有几处错误(比如说吴稚晖选定“北京话”作国语,又说注音字母由吴氏与黎锦熙创制等),却无妨其史料价值。这当然证实吴稚晖并非纸上谈兵,不愧国语运动的领袖,然而并未解人迷惑:既然如此,他为何偏偏多操方言?[50]
吴稚晖
论年龄,这三位一位比一位老:傅振伦生于1906年,傅斯年生于1896年,吴稚晖则是1865年生人;但说国语的积极性似乎每况愈下:吴稚晖是能说而不常说,傅斯年是曾说而终未说,傅振伦则根本就不愿说。我们不能据此推断他们保守:吴稚晖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宣传家之一,傅振伦对世界语的热爱直到晚年犹未减,保守分子岂宜如是?
这当然都是个例,但国语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一般人士更可想见。192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儿童在学校学了国语,偶尔在家庭说着,家属便生厌恶。”[51]这是东南一带的情形,而那还是推行国语运动最热心的地区,其他地方只会更甚。显然,普通人对国语的实际感知和轰轰烈烈的宣传之间,存在不小距离,有时甚至可能恰好相反。不过,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此归为理论和实践的差异,而应从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所说的“语域”(register)角度去理解。这个概念关注到社会“情境类型”的变化对语言选择的影响。一个人说何种“方言”往往与其“出身”有关,但他在特定情形下选择说哪种语言,则通常由“社会活动性质”也就是“场景”决定。[52]换言之,这里涉及的不是语言能力的问题,而是对社会场景的主观判断问题:对于一个具备“双语”能力的人来说,何种情形使用国语,何种情形使用方言,是有规则可寻的。具体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这种“语域”可以分作几种类型,每一类型又与不同的意义脉络相关。要细致地勾勒其地形,就要求我们必须突破单纯的思想史路径,兼采阐释人类学视角,不仅注意那些带有宣言和理论性质的文献以及官方发布的政策、条令等文件,更要从时人的具体日常实践中勘察其背后的意义走向。
第一种语域是城乡(或“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别。当时流行的一个看法认为,国语适合于大都会,农村和偏远的内陆则是方言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可以用话剧为例。作为一种“舶来品”,话剧的影响长期限于少数几个大城市,基本采用国语或普通话演出。[53]3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其演出范围进一步扩散。初期主要沿“各大水陆交通线”展开,推行得较为“顺利”,但随着交通线逐渐沦陷,“除了少数城市和部队以外”,话剧的生存范围迅速压缩,据说其主因就是语言上的障碍。[54]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剧团在城区演出时使用国语,到了乡村就用方言。[55]有人还专门提醒热衷于戏剧救亡的人士:“在大都市里利用国语是应该的,但是偏僻地方,用起国语来,便会使观众发生’洋戏’之感!”[56]其实,乡下人当然有可能真的不懂国语,但也可能是因国语与其日常生活环境相去太远,而产生格格不入之感,此其所以“洋”也。若果真如此,则障碍就不仅是语言上的,亦有文化和心理上的(更可能是几方合力的结果)。不过无论如何,“国语”而让人感到“洋”,未免显得讽刺。
这又带来第二重反讽:30年代,国难日亟,鼓动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成为当务之急,以服务民族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国语却显得软弱无力,甚是尴尬。有人为此提出:“战时演剧最主要的任务,并不在推行语言的统一,而是要宣传并教育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日战争,及抗战中民众应有的任务”,只有方言才能完成这一使命。[57]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乡村或“偏僻地方”之时,真正使人兴起家国之感的,不是“洋气”的国语及其背后抽象的“国家”、“民族”,而是“土气”的方言和活生生的“地方”。这样,在民族主义主题下,国语和方言形成了一种不无紧张而又相互支撑的关系,提示出“双语”实践对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尽管它并不总是被人们意识到。
第二种语域是内外之别。所谓“内”,主要指家庭和家乡。黎锦熙说:国语统一当然要“各地方的人都要牺牲他的土音方言”,但“牺牲”并非“消灭”,一个人“身在家乡,和家乡人说话,谁来禁止他用土语方言?谁来强迫他一定要来打官腔,说官话!”[58]《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讲得更清楚:国语要“人人能够说,却不是人人必须说,因为常言说得好,’官腔莫对同乡打。’”当然,另一面也很重要:“虽然不是人人必须说,却要人人能够说,为的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却不应该见面时不会说中国话。”[59]末一语微有语病(方言其实也是“中国话”也),不过不影响其语义效果。黎锦熙以一句“常言”为据,也提示我们,文化和社会习俗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中国传统讲究内外之别,同样一套举止,对外是谦恭有礼,对内可能就是生分疏离,不同情境的转换非常关键,语言就是其中最直观的标志之一。唐人贺知章的名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回乡偶书》),在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切身经验。30年代一位左翼文化人观察到:“少数的智识分子或是生活有着流动性的人们,到处跑码头,于是他们便会说国语或类似的国语了;但一回到家乡,不讲土话好像是一种耻辱,于是便哇啦哇啦地打起乡谈来了。可见对于一般人,方言较之国语是亲切的。”[60]家庭之内当然更是如此。吴稚晖说,中国人即使能讲官话者,于“家人父子之聚语,仍各操其亲切之纯一方言。家人而说官话,即小孩亦笑不休也”。[61]这是实况,前揭傅斯年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同时这也解释了吴稚晖自己在不同“语域”间转换的原则。
一个人选用何种语言,反映出他对自我及所处社会空间性质的判断,同时也暗含了一整套与之相应的社会互动方式。[62]用社会学家席尔斯(Edward Shils)的话来说,家乡、家庭都属于“原生性的纽带”(primordial tie)。[63]在这类情境中,“母亲语”才是最得体的语言。[64]作为一种认同的表现,这直接影响到一个人是否能被用“自己人”的方式来对待。在清代四川这样一些移民地区,同籍相遇,“必述其原籍之土语”,谓之“打乡谈”。据云此举有两意:“一以验真伪,一以必亲切也。”[65]“验真伪”重在人我区隔,“必亲切”重在情意交洽,身份的内外两面,都经此界定出来。尤值注意的是,上文所引几条文献,时间和来源不一,却在描述方言时,不约而同使用了“亲切”一词,可见它的确代表了中国人对方言的普遍感受;反过来,在乡人面前讲国语,则被视为“耻辱”,招人鄙笑。这些都提示出语言在建构社会身份的同时,也塑造了人们的情感体验。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化才刚刚开始,大多数人的心理结构还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也为方言的广泛使用提供了极大空间。
第三种语域是“公私”场合(或“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之分。陈存仁笔下吴稚晖讲国语的那段轶事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吴稚晖的举动——从预约时间、穿中山装,到用“演讲的姿势”说话等,都表现出浓郁的仪式意味。虽然从其一贯作风看,仍可理解为“作怪”,但无论如何,其意图都是要经营一种“郑重其事”的氛围。因此,即使它纯属虚构,至少也形象地传递了陈存仁本人的感受:方言是非正式的,可以用于日常和私人的场合;国语是“正式”的、官方的、面向公众的,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国家色彩。
这种认识当然也体现在事实中。据吴稚晖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时,要请一位“熟于北平音”的人士“专任”报告之事。[66]有些地方政府也做了一些相关规定。1938年2月,福建省主席陈仪明令“全省公务人员及教职员”,“以后无论公共讲演以及私人谈话,均应避免本地土话,尽力应用国语,以为一般民众表率”。1940年6月,省府再次号召公务人员“力避方言,倡用国语”。1944年,福建省会暨永安县国语运动周筹备委员会呈文省党部、省政府,建议“规定在办公时间绝对禁用方言接谈”。[67]广东省教育厅则要求各级机关、学校职员、教员自1944年12月1日之后、学生自1945年6月1日之后,“一律以说国语为原则。”其具体推行步骤是:
(一)行政机关由主官作起,次及于下层;由公事来往交接作起,再及于私人谈话;(二)学校由教职员作起,次及于学生;由教学演讲作起,再及于私人谈话;(三)社会教育机关由本身作起,次及于民众;由公事往来作起,再及于私人谈话。[68]
三、四十年代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语运动,每以福建、广东为重点。这不仅因为两省语言状况异常复杂,内部方言林立,与国语标准的差距也最大;而且也因其在政治上频繁反侧,令国民党中央头痛不已。因此,无论在象征还是实用意义上,闽粤二省的国语运动都是中央权力扩张的一部分。但也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文件都是针对公务人员和教师、学生制定的,并不包含普通老百姓;对方言也不是一律严禁,福建省政府的几份文件大都采用了“号召”的口吻,而福建省会暨永安县国语运动周筹备委员会的呈文也特别说明是“办公时间”。广东的要求更严格,但也没有消灭方言的意思;同时更将“公事来往”和“私人谈话”分为两个层次,对使用国语的要求也表示了区别对待(至少是“步骤”的区分)的意思。
这些文件提到的“公事”,主要跟党政机关、官办机构和学校等场所有关。而在1913年,胡以鲁就提出“强制公人使用”国语的建议。其所谓“公人”,包括“官吏、公吏、议员、军人、教学师生”等。[69]无论“公事”,还是“公人”,都指向国家权力及公共事务领域。它们大都是晚清以来“现代化”改革的产物,在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承担着主力任务:政府、官员、议员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操控者、分享者;学校和军队则分从文武两面服务于权力结构、社会分层、意识形态的生产(再生产)和维持。这一共同使命把它们彼此,也把它们和国语绾合起来。而在这些机构和场所之外的更广大区域,则被认为是更私人、更“传统”,也更适合方言的场合。
上面粗略辨认了与国语和方言使用的“语域”有关的几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只是帮助我们梳理某些社会现象的权辞,不可过于拘泥。实际情形要比这复杂得多,而不同类型又多少具有一些连续性:家庭内外的区别也常被看作公私区别的一部分,而城乡差异既反映出政府控制力强弱的不同,也同现代与传统的社会文化区分有关(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社会流动程度的差异)。[70]实际上,很多时候,不同因素同时作用于一种场合,很难将之限定于某一层次。[71]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分类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一种认知取向:国语和城市、外乡、“正式场合”的关联,方言和农村、本土、“非正式场合”的关联,更多地建立在心态认知层面上,受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系统影响,未必存在任何逻辑的必然性。但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场景的分类系统一经形成,就为国语和方言的“双语”实践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行为参考框架,而生产出相应的社会事实。(未完)
注释
[1]Bertrand Barère’ s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1794, 转引自 David A. Bell, “Lingua Populi, Lingua Dei: Language, Religion, 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oo, No. 5, Dec. 1995, P. 1405.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消灭方言的主张,参看【法】克洛德·海然热(Claude hagège):《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祖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9—210页。
[2]【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95页。
[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4]Fang- Kuei Li, “Review on Yuen Ren Chao ‘Cantonese Prim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No. 1, Jun., p. 60.
[5]比如,汪晖就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左翼文化人对“地方形式”的肯定,“不是为了形成地方认同,而是’民族认同’”。而从整体来看,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不但“是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还伴随着“现代国家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的形成”(见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505、1526页)。对国语运动方言观的大体勾勒,见崔明海:《“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江淮论坛》2009年第1期,第173—179页。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5—266页)较全面地讨论了中国现代“方言文学”的发展及其最终命运。此外,如赵黎明:《五四歌谣方言研究与“国语文学”的民族性诉求——以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的活动为例》(《学术论坛》2005年第12期,第167—171页)、王丹、王确:《论20世纪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第140—145页)都涉及其中的某些层面。关于国民政府对方言电影(主要是粤语电影)打击,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如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刘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110页;李培德:《禁与反禁——1930年代处于沪港夹缝中的粤语电影》,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70—187页;范雪:《电影“国语”与三十年代有声片》,《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第90—104页;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8页;吴国坤:《语言、地域、地缘政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泰∕电懋的都市喜剧》,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5—322页。喻忠恩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独立性最强的“两广”地区为例,讨论了国语运动与中央—地方斗争的直接相关性(《“两广事变”后的广东国语运动》,《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第66—73页)。又,“文化宰制”一词,来自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dialect一词演变过程的描述,详见《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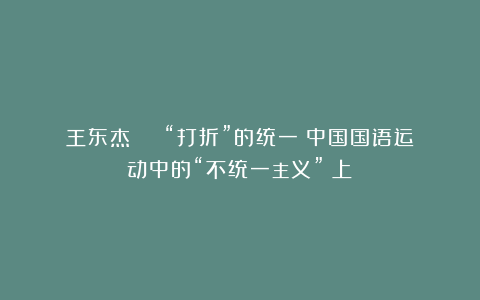
[6]【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31—238页。我这里想特别点出的是: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载体,方言认同并不意味着“地方认同”的消失,反而展现了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协调一面。汪晖的论述虽然关注到了同样现象,但他所突出的是两者的对立关系。
[7]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8]沈敦和:《统一方言说略》,《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期,1906年6月,第26—27页。
[9]比如,马俊超在分析陈炯明的“封建思想”时,就有意无意提及,陈氏“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见刘凤翰等整理:《马俊超、傅秉常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10]黎锦晖:《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发展》,《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第32页。
[11]沈信卿(沈恩孚):《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开会辞(二)》,《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第19页。
[12]《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902年3月4日),第16页。
[13]《论语言之必宜统一》,《盛京时报》1910年5月22日,第2页。文章作者身份不详,但应代表了主办者的态度。不过,也应指出的是,类似的表述也常出现在中国人的笔端。
[14]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第74页。
[15]朱执信:《广东土话文》,1920年4月《建设》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第3、4页(篇页)。
[16]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周刊》第31号,1923年11月4日,第1版。
[17]沈兼士:《吴歌甲集·序二》,收在顾颉刚:《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页;《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续)》,《晨报副刊》1924年3月8日,第4版。当然,北大的方言调查计划早在歌谣运动之前就已有所设想,惟其正式开展仍需到歌谣运动之后。
[18]本段引文分别见杨芬、(钱)玄同:《通信·方言文学》,《国语周刊》第10期(此为《京报》副刊,后文所引《国语周刊》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办,应区分开来),1925年,第8页;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四》,收入《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1,第17页;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第11—12页;胡适:《吴歌甲集·序一》,收入《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1,第3页。
[19]胡适讲述、郭后觉记录:《国语运动与文学》,《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第3版。
[20]胡适:《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52年12月8日);《提倡拼音字》(1953年1月6日),均在《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60、61页。小说家张大春曾引用胡适《吴歌甲集序》里的话,证明胡“只是把’方言的文学’当作’国语的文学’的一个准备”,而非真的“提倡方言文学”(《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有此看法者还不少,但至少从胡适本人的论述来看,这个评论是不准确的。
[21]俞平伯:《吴歌甲集·序三》,收入《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1,第9—10页。按:引文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及此句之前的段落,在收入俞氏散文集《杂拌儿》(初版于1928年)时全部刊落,经此改动,原文的强硬意味有所减弱,但意思仍保留下来。
[22]钱玄同:《吴歌甲集·序四》,第18页。
[23]俞平伯:《吴歌甲集·序三》,第9页。
[24]钱玄同:《吴歌甲集·序四》,第16页。原文自注从略。
[25]钱玄同:《记数人会(1)》,《国语周刊》第21期,1925年11月1日,第7页。
[26]刘复(刘半农):《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国语月刊》第1卷第6期,1922年,第1页(篇页)。
[27](林)语堂:《提倡方言文学》,《宇宙风》1935年第4期,第172页。
[28]本段和下段,均见孙伏园:《国语统一以后》,《国语周刊》第27期,1925年12月13日,第1—2页。
[29]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0年,第432—433页。
[30]这场争论,史称“京国之争”,详见王东杰:《“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77—100页。
[31]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第15页。
[32]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第2—5页。
[33]《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会议记录》,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按此件是手稿,未注明具体时间。
[34]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汉字改革一夕谈》,《国文杂志》第3卷第5—6期,1946年,第17页。
[35]王力:《漫谈方言文学》,《岭南大学校报》第38期,1948年10月10日,第1页。
[36]赵元任:《国语的语法和词汇问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40页。
[37]引文分别出自聂绀弩:《给一本厦门话写文章小册子作的序》,《语言·文字·思想》,上海:大风书店,1937年,第126页;林士一:《国语罗马字呢,还是拉丁化新文字呢?——答黎锦熙先生的〈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青年文化》第3卷第5期,1936年,第24页;叶籁士:《拉丁化概论》,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第35页。进一步的详论见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第155—170页)与《“代表全国”: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第94—98页。
[38]老谈:《国语统一和方言》,《国语周刊》第52期,1932年9月17日,第2页。
[39]黎锦熙:《国语“不”统一主义》,分见《文化与教育》第5期,1933年12月31日,第2—3页;第6期,1934年1月10日,第5—6页;第7期,1934年1月12日,第2—4页。以及《国语周刊》第127期,1934年3月3日,第2页;第128期,1934年3月10日,第2页。引文出自《文化与教育》第7期第4页,《国语周刊》第128期,第2页。
[40]缪钺:《周代之“雅言”》,《缪钺全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页。许倬云先生更认为雅言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参考《西周史》(增补本),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1页。
[41]顾炎武著、黄汝成注:《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35页。
[42]参考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
[43]严复:《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90页。
[44]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7月4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45]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文中自注从略。
[46]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43页。
[47]傅斯年曾对国语的“制定”提出若干建议,见其《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918年2月15日,第188—189页。
[48]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第400页。
[49]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50]由于吴稚晖平日很少讲国语,以致被有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务的黄通误会为“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参见黄通口述:《黄通口述自传》,陆宝千采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51]孙浚源:《我对于国语运动的四个绝大希望》,《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第24页。
[52]【英】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苗兴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4页。
[53]不过据赵元任说,在上海,话剧是以双语演出的,“主角说北方普通话,配角说上海话”(赵元任:《中国音韵里的规范问题》,《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519页)。这一现象至少部分地受到中国传统戏剧习惯的影响。清初李渔《闲情偶寄》已云:“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李渔全集》第3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54]季纯:《谈方言演剧》,原载1942年11月10日《解放日报》,收入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第4册,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0—441页。
[55]史亮:《戏剧下乡之方言问题》,《抗敌戏剧》第2卷第3、4合期,1939年,第29页。
[56]齐同:《大众文谈》,《现实》(上海)第4期,1939年,第307页。
[57]史亮:《戏剧下乡之方言问题》,第29页。
[58]黎锦熙:《黎锦熙的国语讲坛》,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初版于1921年),第7页。
[59]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第2—5页。
[60]齐同:《大众文谈》,第307页。
[61]吴稚晖:《西北为文明之摇篮》,《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75页。
[62]在此意义上,语言乃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说的社会“表演”中“个人前台”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尤其是第20—21页),而戈夫曼的著作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语言与认同关系的理解。
[63]Edward Shils,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in Selected Essays by Edward Shils, Chicago,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0, pp. 39- 40.
[64]周有光曾说:方言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母亲语”,共同语是从教师那里学来的“教师语”(《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新语文的建设》,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年,第12页)。从社会角度看,这个区分是很有启发性的,提示出“国语”背后的建制性因素及其作用途径。
[65]汪承烈修、邓方达纂:(民国)《宣汉县志》,卷16“礼俗”,1931年石印本,第28页。
[66]吴稚晖:《注音符号歌》,《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第359页。
[67]《福建省政府主席手令》,1938年2月22日;福建省政府:《公务员及教职员应负普及国语责任,以后讲演及谈话,应均用国语以为民众表率》,1938年2月24日,均在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1—1—426。《福建省政府训令》(府秘甲报永字第02033号),1940年6月2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24—2—192。福建省会暨永安县国语运动周筹备委员会:《呈请准予通令所属推行国语运动禁用方言由》,1944年4月26日,福建省档案馆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档案,档案号:2—11—12885。
[68]《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云教社字第48312号),1944年6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不过,这份貌似严格的训令,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佳。1947年1月,教育厅再次命令各中等学校“自本学年度下学期起,逐渐采用国语教学,并应设立研究会或讲习班,俾便教职员学生自动学习”。见《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雨社卅六字第四〇〇四八号),1947年1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
[69]胡以鲁:《国语学草创》,铅印本,出版日期不详,第55页下—56页上。
[70]在有些情形下,上述某些区分亦可能连类生产出新意义。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陆的影视作品中,领袖人物说方言或带方言口音,几乎成为一种身份标志,以致当他们在屏幕上改说普通话后,反使不少观众产生形似神非之感。这主要是为了使得领袖人物的塑造更“真实”,但也隐含了人们对方言的某种认知:作为更适于“私人场合”的语言,它比普通话更能表现个性,因而更容易突出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至于其他“次要”人物,则不妨使用千人一面的普通话。
[71]比如,在1963年拍摄的方言电影《抓壮丁》里,所有角色都说四川话,而最主要的两个反面人物卢队长和王保长则时不时冒出一两句川味“官话”。这种安排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意在和他们那似官非官的“奴才”身份相吻合。事实上,卢队长明确宣布:在“官场”就要说“官话”。王保长的“官话”是向卢队长学的,卢队长则是到“成都省”受训时学到的,也提示了城乡和社会等级之间的语言差异与流动情形。
△ 滑动查看更多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