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上有一些作曲家
似乎更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有意将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
更确切地说,
是宁愿在自我创造的后花园中长梦不醒。
“老实人”布鲁克纳的背后
是一张虔诚、神秘且孤独的教士之脸,
舒伯特用天真烂漫的旋律
勾勒出一位在精神世界中酣梦许久的孤寂旅人,
萨蒂或斯克里亚宾则更像音乐术士,
孤独地在实验室内研制色香味各异的灵丹妙药。
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
这篇文章的主角——
更是在孤独中做梦的高手。
在现实生活中,拉威尔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或许是受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的影响,他终其一生用实际行动在给“孤独”二字释义:一位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老百姓,性格内向又有着有限的幽默与些许的古怪,终身未婚,总是独来独往,时而自相矛盾,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共机构任过职,只收留了几个私人学生,一生犹如沧海孤舟在或平静或汹涌的大海上航行,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不带走一片云彩。音乐会上,每逢人们要演奏他的作品,他总是会溜出去抽一支烟。人们在拉威尔的家乡西布勒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条街道,本应出席授名仪式的拉威尔却躲在广场另一侧的咖啡厅里默默注视这一切,活像一个当下在夹缝中生存的极度内向的人。
在音乐世界中,拉威尔似乎要比现实生活中从容得多,用音乐与人们交流似乎是最令他感到舒适的方式。他的作品时而质朴真挚,时而充满异域风情,间或回归传统,也会倏忽顺应潮流……不过,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指向孤独——拉威尔最为纯粹的底色。孤独是拉威尔的缪斯女神,她没带领拉威尔攀登世俗之巅,却给予了他无穷尽的创作灵感。
为了满足远离社交、孤自创作的“刚需”,拉威尔于1921年买下一栋位于巴黎西南约50公里的蒙特佛·拉莫里小镇的小屋,名为“Le Belvédère”,在法语里的意思为“屋顶或花园小山上供观赏风景用的亭台楼阁”。小屋可谓名副其实:这套房子不如理查·施特劳斯的乡间别墅那般阔绰,看起来更像是维京人的长屋,但胜在雅致,从阳台可轻易观赏到拉威尔亲自设计的小树林。拉威尔在生命最后的16年独居于此,只有一个管家和一窝暹罗猫和他共享“望亭”。
异国的酣梦
“望亭”的书房位于主厅的侧面,推开门就可见得那些精装的藏书。在那个没有网络资讯的年代,书籍是了解异国文化最为直接的途径。书房里的《一千零一夜》十分显眼,写作声乐套曲《天方夜谭》时的拉威尔一定对这部民间故事集手不释卷。《亚细亚》无疑是拉威尔异国梦的“总纲”,借助音符与诗歌,拉威尔将游历神秘东方的梦想倾注其中,“我想去看……”在歌词中不厌其烦地出现,似乎与前辈柏辽兹《夏夜》中《无人岛》一章中屡次出现的歌词“您想去哪里”形成跨越时空的美妙问答,这大概也是两部相距六十余年的作品总是出现在一张唱片里的缘故吧。
异国情调是拉威尔音乐旨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希腊人、吉普赛人到俄罗斯人,从南半球的马达加斯加岛到与非洲对望的伊比利亚半岛,听众乐意在此等神游中进行精神淘金。不过,拉威尔从未像殖民者那样对别国音乐文化进行强取豪夺,而是基于自己的想象力与无人能及的直觉,以最为自然的方式玩角色扮演游戏,他似乎拥有一种“不是本地人,胜似本地魂”的特异功能。正如同法国诗人、作家扬科列维奇在《拉威尔画传》一书中写的那样:“拉威尔在异国情调中彰显出无可比拟的可塑性。”写西班牙风格的作品时——如《西班牙狂想曲》,他比作曲家曼努埃尔·德·法雅更像西班牙人;当他在声乐作品中使用希伯来语时——如《两首希伯来旋律》,他比作曲家达律斯·米约写得更像犹太人……
彰显古希腊神话色彩的《达芙妮与克罗埃》以无可比拟的瑰丽和华美著称,考古出来的古希腊音乐与该剧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却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不正宗”或“不协调”对作曲家进行指责和非难。究其原因,正是拉威尔对编舞米歇尔·福金所说的那样——“我只是忠实于我梦境中的希腊是什么样子。”此等才能,我认为只有同为配器大师的普契尼能够与之媲美。晚年的拉威尔曾到访北非的摩洛哥,在聆听当地阿拉伯音乐演奏后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我还有精力创作阿拉伯音乐的话,那一定比他们演奏得更具伯风格阿拉。”不知道当时参与接待的马拉喀什市长听了这句话后会怎么想,不过拉威尔绝非口无遮拦的狂妄之徒——他似乎真办得到。
在“望亭”创作室的墙壁上,有一张拉威尔童年时期装扮成俄罗斯王子的画像。也许出于对异国文化的向往,或是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舞台带来了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穆索尔斯基与鲍罗丁的音乐,这些来自北方的新鲜音乐深刻影响了拉威尔、德·法雅、弗洛朗·施米特等这些狂放不羁的文艺青年。颇有才气却谱曲困难的“业余”作曲家鲍罗丁在音乐史中始终是个被边缘化的小角色,却被拉威尔当作可与海顿并列的致敬对象。拉威尔改编的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或许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改编范例,经过拉威尔妙笔的上色,侏儒、古堡、牛车与女巫都从黑白变为了彩色、从二维变为三维;地下墓穴的通灵对话,或许在此刻并不是发生在穆索尔斯基与哈特曼之间,而是发生在拉威尔与穆索尔斯基之间。拉威尔并没有去过俄罗斯,自然也没有听过正宗的俄罗斯钟声,不过当《基辅大门》中“漫步”主题再度出现时,画中钟楼里的大钟似乎真的被敲响,比《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加冕仪式要更为辉煌和宏大。
在拉威尔的“精神衣柜”里,西班牙无疑是最为绚丽多彩的一件。拉威尔的母亲是巴斯克人,响板与巴斯克铃鼓交融而成的律动自然在拉威尔的血液中流淌:从色彩纷呈的四联画《西班牙狂想曲》到喜忧参半的《丑角的晨歌》,再到螺蛳壳里做道场的酒馆音乐《波莱罗》,最后到人生尽头前的《堂吉诃德致杜尔西内娅》之《饮酒歌》,西班牙文化风情在丰富多彩的音响游戏中被一次又一次彰显。
“爵士乐”这件衣服是拉威尔“精神衣柜”里最为摩登的一件。20世纪的巴黎作为世界新艺术中心不断繁荣,来自大洋彼岸的爵士乐让艺术家们大开眼界。德彪西以《木偶的步态舞》接纳了这一舶来品,到了拉威尔这里,《G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中小提琴拨弦对斑卓琴的模仿、《G大调钢琴协奏曲》中巴松慵懒的哈欠和如汽车鸣笛的铜管以及《D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长达三百多小节的爵士主题快板,都是作曲家对爵士乐创造性吸收的证明。一战后的拉威尔与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相见恨晚,格什温曾以作曲技术不够为由拜拉威尔为师,拉威尔婉拒了格什温的请求,于是就有了“与其做一个二流的拉威尔,不如做一个一流的格什温”这样的金句。巧合的是,格什温也曾渴望向勋伯格学习,得到了上述类似的回答。
传统的旧梦
在“望亭”的客厅里有个隐蔽的侧门,通向比书房更为狭小的储藏室。不同于带着花边令人浮想联翩的精装书,储藏室里摆放的大多是印刷简约的平装书,我们既能看到与瓦格纳、李斯特、舒曼等诸多音乐大师有关的书籍,也能看到关于当代法国音乐以及拉威尔作品相关的评论。不难看出,这间屋子不仅更为低调,也更为现实,串联着严肃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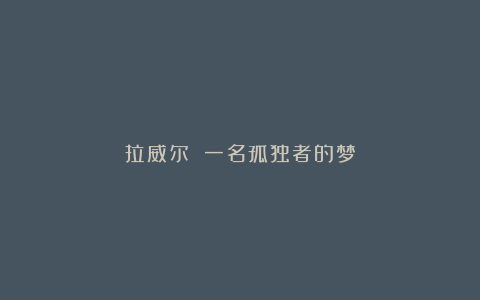
“如何看待传统?”这是摆在作曲家面前的灵魂拷问。面对这一命题,拉威尔的回答可谓相当得体:不同于“安静的革命者”德彪西,拉威尔本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一种进化,即创造一种带有奇妙语法的语言,用现在进行时把一般过去时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水之嬉戏》可以看作是李斯特《埃斯特别墅的喷泉》的完全体形态;《西班牙狂想曲》是超越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和夏布里埃创作的更胜一筹的产物;《大圆舞曲》中,施特劳斯家族的舞步明晰可辨;《G大调钢琴协奏曲》对莫扎特与圣-桑的怀念之情力透纸背;拉威尔对舒曼《狂欢节》与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配器,也算得上是为传统招魂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还能借助加九和弦、教会调式、调性并置等理论工具,更为理性地去看待拉威尔的音乐创作。
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指挥家水蓝、钢琴家孙颖迪与中国交响乐团一起奏响纪念拉威尔诞辰150周年音乐会 摄/牛小北
拉威尔对如何看待传统这一问题给出了富有创造性的回答,不过其口吻中透着凝重。这份凝重,既饱含对历史的尊重与温情,也夹杂着个人的孤独和感伤。他身处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巴黎开展音乐创作,内心却沉浸在逝去的旧时光里。《库普兰之墓》不单单是战争死难者的墓志铭,更满含对巴洛克时期法国音乐的深切追忆,这与《古风小步舞曲》有着相似情怀;《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不只是对老师福雷的深情缅怀,更体现出对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的遥想;从《三首尚松》中的《回旋曲》里,我们甚至能捕捉到拉絮斯或雅内坎音乐风格的回响。艺术家面对消逝事物的情感通常极为复杂,难以用寻常情感标准衡量。以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为例,作曲家借被捉弄的公爵、马裤角色、意大利歌手等元素,表明这是莫扎特时期盛行的题材,可也无奈地展现出那个戴假发、撒香粉的时代,已随玛莎琳夫人的马车远去,一去不返。
童真的幻梦
我们或许见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有穿越时空的能力,你最希望委约哪位作曲家进行创作,或者想拜访哪个作曲家并与之交谈?对我而言,拉威尔似乎是首选,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拜访他的“望亭”,看看他的“赝品王国”,并委托他先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再给他养的暹罗猫家族写一部作品,体裁不设限,稿酬无上限。
拉威尔的童心与天真总是美妙得令人感到为难,不论是《鹅妈妈》里的瓷偶女皇、《西班牙时刻》里拟人的时钟,还是《孩子与魔法》中跳狐步舞的中国茶杯与英国茶壶,都将成年人最深处的童年乡愁深深隐藏。
穿过如同轮船过道一般狭窄的走廊后,我们来到拉威尔的工作室。除了音乐家必需的钢琴与写字台,还有如水晶球一样的台灯、精致的烛台、海顿与舒伯特的剪影画以及各式各样的摆件,有些甚至一文不值。
拉威尔的父亲从事蒸汽发动机行业,他也对机械充满热爱。拉威尔曾对着钟表中的布谷鸟自言自语,说他仿佛能够听到鸟的心跳,也曾经对着机械夜莺听了一个小时,完全不顾其他音乐家还在等着他排练。不仅仅是会动会响的东西让拉威尔欲罢不能,那些如同“古玩五元店”里的小物件也能持久地吸引拉威尔的目光:仿制的花瓶在行家眼里就是垃圾,却被拉威尔大大方方地摆在厅堂里,就好像它们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拉威尔并不是有着糟糕的品位,而是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以至于他能够从任何事物中提炼出能够说服自己的美,就好比事物带来的趣味远超过这些事物本身的实质,真与假的边界不复存在,这与他能够写出比本地人更地道的音乐如出一辙。
莫里斯·拉威尔曾经居住的房子
对于母亲的依赖是孩子的本能,这种本能却在拉威尔这里被无限放大——母亲的形象就像顶天的柱子。“望亭”离钢琴不远的墙上挂着拉威尔母亲的画像,这意味着创作时稍稍抬头,他便能看到这张亲切的国字脸。在工作室创作的拉威尔犹如子宫里的胎儿,而母亲照片的守护就是滋养胎儿的羊水。《孩子与魔法》这部歌剧就是在这间工作室里完成的。故事里,小男孩因写作业拖沓被母亲训斥,一怒之下大闹房间。屋里的物件、窗外的动植物都能说话,它们纷纷躲开失控的小男孩。孤立无援的小男孩呼救,却招来更多反感。混乱中,小松鼠受伤,小男孩为其包扎后累倒。此时,物品与动植物原谅了他,助力他唤回母亲。最后,一道光出现,小男孩重回母亲怀抱,全剧以“Maman”(法语中对母亲的昵称)画上句号。这看起来这只是一个逗小孩的睡前故事,但弦外之音恐怕如脚本作者柯莱特说的那样——眼泪流到脖子上也没有察觉。拉威尔的母亲于1917年去世,他一度一蹶不振,创作也大不如前,而《孩子与魔法》就是舔舐伤口期间的产物。终曲合唱里不断重复的“他是个好孩子,是个乖孩子”是小孩最希望听到的,拉威尔也希望自己是剧中那个不想写作业、喜欢吃蛋糕的好孩子,但母亲的怀抱却只能定格在回忆之中。
战争的噩梦
拉威尔的卧室位于地下室——这是个几乎没有采光的地方。卧室既是最为私人的空间,也是最适合做梦的地方。噩梦作为美梦的反面,其出现与否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所思所想、潜意识甚至个人性格都有一定关联。拉威尔本人及其音乐,就如同被潮汐锁定的月亮,明亮皎洁的那一面清晰可见,可月球常年背对地球、阴暗未知的那一面,我们却知之甚少。西班牙钢琴家瑞卡多·维涅斯曾这样评价拉威尔——“中世纪天主教般虔诚与魔鬼撒旦般不敬的结合体。”
拉威尔作品里的阴暗面并不难寻觅:在《夜之幽灵》中,夕阳下的绞刑架上来回摇摆的尸体和夜幕下神出鬼没的侏儒幻影,将噩梦具象化;我们沉醉于《钟之谷》的幽深回音,却不能忽略此地渺无人烟且并非存在于现实地球,还有夜蛾抖落的鳞粉、悲鸟凄厉的哀歌、丑角沉重的叹息以及随时可能被海浪吞没的孤舟;《亚细亚》里,既有寺清真的宣礼塔以及满腹经纶的文人墨客,也有鲜血、仇恨、商人鄙夷的目光和举着弯刀砍下头颅的刽子手;《孩子与魔法》中,精致的家具与可爱的猫咪确实让人眼前一亮,然而淌血的大树也在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
拉威尔的卧室里有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不仅是那个西装革履的波特莱尔式公子哥,也是身披军装的后勤战士。一战开始后,有的人想方设法逃避,手无缚鸡之力的拉威尔非但没有流亡大洋彼岸,还要效力沙场。或许对于机械的喜爱过于根深蒂固,拉威尔原本打算在战场开飞机,可是虚弱的身体使他连空军的大门都进不了,于是只能当起了卡车司机。阿黛莱德(Adélaide)既是《高贵感伤的圆舞曲》的别称,也是他对于卡车的爱称。虽然后勤工作比直面枪林弹雨的冲锋陷阵要安全得多,拉威尔侥幸成为一战和西班牙流感的幸存者,但战争还是给拉威尔留下了一生的阴影,更何况他还遭受到母亲去世的打击。到了就寝的时刻,人间地狱般的场景就像硬盘里的文件自动开始播放,失眠总是在阴暗的地下室折磨着他。
艺术家对于战争的思考总是超乎常人。拉威尔在递交入伍申请书的同时,还将《三只美丽的天堂鸟》作为音乐版请愿书题献给保罗·潘勒韦,他既是与莱特兄弟共同研发飞机的数学家,也是一名可能帮助拉威尔应征成功的政治家。这部矛盾且复古的合唱作品,诗意而含蓄地表达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投身战争的决心。
如果在拉威尔作品中选出一部最阴暗的作品,非《D大调左手钢琴协奏曲》莫属。虽采用D大调——这本应是辉煌的调性,却像极了爱伦·坡的小说,黑暗如驱不散的夜。“被禁止的右手”是这部作品最为直观的阴暗之处。奥地利钢琴家保罗·维特根斯坦在一战中失去右臂,他委托拉威尔创作一部钢琴协奏曲,右手自然无从施展。“被压垮的左手”是这部作品最为核心的阴暗所在。大段独奏犹如孤独者的独白,使作品协调性欠佳,而且压倒性的乐团与单手钢琴演奏极不相称。爵士乐风格的主题推向高潮时,钢琴声完全被歇斯底里的铜管乐团掩盖,弦乐高音区下行的固定乐思也在侵蚀钢琴仅存的余响,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
难醒的孤梦
或许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过于严重,拉威尔1927年就出现间歇性失语的症状。1932年,一场严重的车祸对本就不健康的拉威尔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他几乎无法继续创作,甚至连记事、认字、开门这种日常基本生活都出现了障碍。虽然生活能力堪忧,但拉威尔的创作欲望丝毫不减:他想创作一部和奥涅格《火刑堆上的贞德》相媲美的舞台作品《圣女贞德》,根据阿里巴巴的故事写一部歌剧《莫尔吉亚妮》以继续构筑他的亚洲宇宙,德·法雅也知道拉威尔渴望以“圣方济各向雀鸟布道”为主题进行创作(这个愿望由后辈梅西安实现了)。没有人知道晚年无法继续创作的拉威尔是怎么生活在“望亭”里的,也没有人知道他需要克服多少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
1937年12月19日,拉威尔在布瓦洛街诊所接受了探查性质的脑外科手术,由当时著名的脑科专家克洛维斯·樊尚主刀。医生并没有发现明确的症结,术后的拉威尔因为手术并发症而昏迷,而这一昏过去,就再也没醒来过。拉威尔生前的最后时刻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体面,死后也是。苍白的遗容上有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不得不裹上一层又一层的纱布,看起来像是戴着头冠的法老。
德彪西和拉威尔的墓志铭都极为简短,都以作曲家冠名。令人欣慰的是,在那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墓碑上,我们能看到他的弟弟爱德华、他的父亲约瑟夫以及他最依赖的母亲——玛丽·德劳特的名字,一家人终于在天上团聚了。
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的墓碑
《龙萨致其灵魂》是我最后能想到的作品,我们不妨听着这部作品结束在“望亭”的神游。这首只有两分钟的尚松作于1925年,本是为钢琴和男中音独唱而作,拉威尔于1935年将其配器,可以说是作曲家最后的作品。苍凉而朴素的旋律线配合五度,就像墓志铭上的刻字,冰冷而单调,就像歌词中说的那样,肉体苍白无力地掉入死人的国度。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龙萨应该不会想到,他的这首诗是那么的适合这位三百多年后的作曲家。
拉威尔是个一生都在用音符点燃人造烟火的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远离世俗的烟火,与歌词中“没有因谋杀、毒药和怨恨而愧疚,也藐视被众人羡慕的恩惠与财宝”不谋而合。尚松的最后一句如同微笑着的拉威尔,和蔼但不刻意讨好他人。就像格什温坚持走自己的路一样,我们这些神游的过路人不妨听听作曲家最后的话:“过路之人,如我所说,追随你的命运,不要打扰我,我正在安睡。”伴随着颤音琴的五度叠置和弦,这句话的余音渐渐消失在绿树成荫的花园中。
文:庚天
编辑:文珊
美编:张琳琳
排版: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