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曾经当过皇帝的可怜虫
作者︱万伟恒
他不再是李煜,他是“违命侯”。
这三个字像一记冰冷的耳光,抽在他曾经作为帝王的尊严上。开封城里的这座府邸,不是家,是一座精致的囚笼;那些依旧供应的锦衣玉食,不是恩赐,是喂养宠物的饵料。宋太祖赵匡胤,这个用一条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的雄主,以他特有的、混合着市井精明与政治智慧的残忍,完成了对一个失败者最彻底的剥夺。他不杀他,他只需要他活着,像一件活着的战利品,像一只被拔去了爪牙、圈养起来以供观瞻的珍禽异兽,用以证明新朝的武功与德政。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长廊中,这一个极其怪异又极其典型的形象:一条曾经当过皇帝的可怜虫。
此刻,他蜷缩在开封府邸的阴影里。窗外是北地的风沙,与他魂牵梦萦的“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的江南,隔着千山万水,也隔着天堂与地狱的距离。他或许会时常恍惚,那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那醉生梦死的繁华,究竟是一场真实存在过的旧梦,还是他此刻囚徒生涯里,因极度痛苦而滋生出的幻觉?历史的吊诡与残酷,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先将他捧上九重天阙,享尽人世极致的尊荣与奢靡,然后,又毫无征兆地,将他狠狠掼入尘埃,让他品尝尽世间最尖刻的屈辱与最无望的煎熬。
这条可怜虫,难道生来便是可怜虫么?
不,曾几何时,他是南唐国主,是坐拥江南锦绣河山的君王。可他的悲剧,恰恰在于他错位的命运——一个本该在文苑词坛挥洒才情的风流才子,却被历史的阴差阳错,推上了他根本无法驾驭的帝王宝座。他的骨血里,流淌着艺术的敏感与天真,却唯独缺少了政治家应有的铁腕与冷酷。在赵匡胤磨刀霍霍、志在天下的时局里,他依然沉溺于“春殿嫔娥鱼贯列”的歌舞升平,寄望于卑微的纳贡称臣,以求偏安一隅。他像一只精心装饰着金丝银线的纸鸢,在江南温软的暖风里飘摇,以为这便是全部的苍穹,却不知北地早已狂风大作,那攥着线头的,已换成了开封城里那双粗粝而有力的手。
所以,当战争的铁蹄踏碎金陵的春梦,他的人生,便完成了一次从“人主”到“人囚”,乃至到“人宠”的断崖式跌落。这身份的转换,其间的痛苦,远非“亡国”二字可以概括。它意味着你不再是你,你的身体,你的情感,你最后的、仅存的一点尊严,都成了胜利者可以随意处置、甚至肆意践踏的资产。史书那句语焉不详的“小周后入宫,辄数日不出,必大泣骂后主”,像一根淬了毒的针,轻轻一刺,便让我们窥见了那华美囚笼之下,何等不堪的凌辱。当曾经的皇后,他心中圣洁的“嫦娥”,被新的主宰者召去,如同征用一件美丽的器物,他除了“徨徨殚惧,唯唯承命”,还能做什么?他连保护自己女人的能力都已丧失。这种痛苦,比之山河破碎,或许更为具体,更为锥心,它日夜啃噬着一个男人最后的底线。此刻的他,岂止是可怜虫,简直是被剥光了所有鳞甲,在盐碱地里痛苦蠕动的虫。
那么,他该如何面对这无法面对的人生?
他选择了酒,选择了在酒精的迷幻中,暂别这清醒的耻辱。“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这是他无奈的告白。酒,成了他通往短暂自由的唯一舟楫。在醉乡里,或许能重见故国的明月,能再拥旧人的温存。然而,酒醒之后,现实只会加倍的冰冷与狰狞。他也选择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欢作乐”,这与其说是放纵,不如说是一种麻醉,一种对生命意义的主动放弃,是“混一晚算一晚”的绝望。他像一条被驯养的犬,在主人划定的圈子里,用主人施舍的肉骨头,麻痹着自己野性的记忆。
然而,他终究不是一条纯粹的犬。如果他真是,或许还能在饱食终日中,获得一点懵懂的快乐。可悲就在于,他灵魂里属于诗人的那一部分,始终未曾泯灭。那是一种无法根除的痼疾,是长在他骨头上的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让他无法真正麻木,让他对痛苦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感知。于是,当外部的羞辱与内心的创痛累积到无法承受之时,他找到了另一个出口——词。
正是这个出口,最终拯救了他作为文化生命的存在,也最终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点。
那三年囚徒生涯中,他用血泪拌和着墨水写下的篇章,尤其是那几首千古绝唱《虞美人》、《浪淘沙》、《相见欢》,完成了他从一个庸碌的亡国之君,到一个伟大词人的最终蜕变。在这之前,他的词是“绣床斜凭娇无那”的宫廷艳曲;在这之后,他的词是“以血书者”的生命绝响。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哪里是写花,这分明是他命运的白描。曾经的“春红”何等绚烂,而时代的“寒雨晚风”又是何等的无情。“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那“胭脂泪”,是小周后的,也是所有故国宫娥的,是他整个逝去的美好世界的缩影。他把这巨大的、个人的悲哀,升华成了对人类共有之“长恨”的咏叹。
最致命的,当然是那首《虞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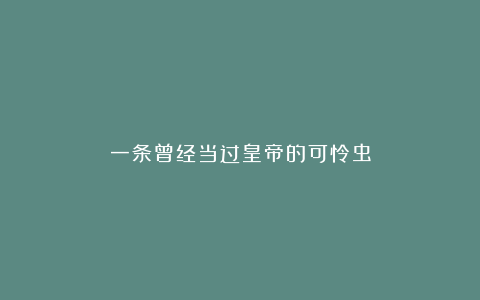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开篇便是对永恒自然与短暂人生的巨大与叩问,是一种厌极了的美丽。“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那“又”字,写尽了岁月流逝中痛苦的循环往复。囚禁他的小楼,连春风都成了提醒他失去自由的嘲讽。而最后那“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将一己之私愁,倾注入了亘古奔流的长江大河,使之具备了与天地同其久远的磅礴气势。他个人的愁,是亡国之愁,是辱妻之愁,是苟活之愁;但他用艺术之手,将这愁绪提炼、放大,让它成为了人类所能体验到的关于失落、伤逝与无奈的一种永恒象征。
他在这声声泣血的吟唱中,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不是作为帝王的尊严,那是永远失去了的;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能以其极致的情感体验与超凡的艺术表达,触动后世无数心灵的“人”的尊严。
然而,政治是容不下这等真挚的。宋太宗赵光义,不像其兄赵匡胤那般带有几分枭雄的豁达,他更阴鸷,更敏感。他无法容忍这个“高级宠物”在文艺的领域里,发出如此凄厉而动人的哀鸣。这哀鸣,在太宗听来,不是艺术,是“贼心不死”的宣言,是可能唤起旧国遗民感伤的煽动。于是,那壶牵机药酒,便成了必然的结局。历史,终于用它最惯常的方式,掐灭了这一缕不合时宜的、过于耀眼的艺术之光。
李煜死了。死得极其痛苦,据说身体蜷缩如弓。他作为“违命侯”的物理生命,被彻底抹去。
但,他活了下来。活在他的词里,活在中国文学浩渺的星空中,而且光芒愈久愈炽。后世人们读他的词,会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而蹙眉,会为“别时容易见时难”而叹息,会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而怅惘。有多少人在被这艺术魅力深深打动之时,还会去苛责他作为帝王的昏聩与无能呢?艺术,完成了他对自身悲剧的救赎。
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尖锐的问题:他,究竟值得同情吗?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他毫无值得同情之处。他是一位亡国之君,他的颟顸怠政,直接导致了家国的覆灭,他应对那场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治下的臣民,所遭受的战乱之苦,恐怕比他个人的屈辱要深重得多。他的可怜,有其咎由自取的成分。
但从文学史,从人类情感史的角度看,我们又无法不同情他。他是一位被命运抛错了位置的天才,一个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被撕得粉碎,却在艺术的祭坛上将自己献祭的羔羊。他以其个人的、巨大的不幸,为我们酿造了文学的甘醴。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那三年的囚徒生涯,没有那刻骨铭心的屈辱与痛苦,就没有词人李煜的登峰造极。是开封的囚笼,囚禁了一个君王,却释放了一个词魂。
这条“可怜虫”,因此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符号。他集昏君与词帝于一身,融极致的荣华与极致的屈辱于一命。他让我们看到,历史在碾压个体时的无情,也让我们看到,文化艺术在超越时代苦难时的伟力。他像一尊被打碎的精美瓷器,帝王的身躯已然零落成泥,但那些碎片,却映照着月光,每一片都闪烁着凄美的、永恒的光泽。
今夜,当我们再次吟诵起“问君能有几多愁”,那千年前从开封一座小楼里流出的哀音,依旧能漫过时空,流入我们心田,泛起微微的涟漪。这时,那条在历史尘埃中痛苦蠕动的“可怜虫”,仿佛也获得了他的宁静与永恒。
作者简介
万伟恒,网名玄机子,自由职业者,往来于城乡之间,无所谓宠辱沉浮。热爱读书,喜欢写作,偶有佳作,自娱自乐,偶然获奖,纯属巧合。个人微信号:wanweiheng
原创作品
未经授权禁止盗用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