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门前的紫薇花又开了,只是栽花的人——我的父亲却永远地走了。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文艺风云”特别推出“我与书的故事”征文活动,那段时间,好巧不巧,我在外地出差,便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将记忆里的碎片逐字敲成了这些文字。
我的家在清水江畔,蓝蓝的天,青青的山,绿绿的水,那里风景如画,只是我家的小木屋,像一朵褪色后歪倒在绿草地上的蘑菇,低矮,泛黑。家里穷,穷得仿佛被时光的尘埃层层覆盖,毫无亮色。刚秋收后的几个月,家里还能经常吃到白米饭,待春寒漫过老屋的瓦檐,白米饭就与土豆、玉米、红苕等各种油茶交换着吃。到了蝉鸣聒噪的夏日,白粥已成奢侈,红薯、玉米与野菜已成主食,它们在我肠胃里咕嘟作响,一打嗝,满嘴的红薯腥味。无数个深夜里,我肠胃的咕噜声与窗外的虫鸣应和着,清晨,我总是被巨大的饥饿感给唤醒。
每到开学季,这对于我家来说是巨大的折磨,尽管只是几十元的报名费,却像块沉重的磐石,压得老木屋都透着股喘不过气的压抑。父亲说,我是家里的长女,读书理所当然要优先考虑我,其实只是读个书而已,父亲搞得像重大财产继承般。也正因为读书机会的万般不易,我读书特别卖力,乃至后来读到《骆驼祥子》里拉车的段落时,总恍惚看见自己弯着腰在文字里跋涉的影子。墙上一张张奖状,我以为那是对父母最好的慰藉,却不想成了妹妹们读书的枷锁。
那个煤油灯摇曳的夜晚,父亲的脸在旱烟的雾霭里忽明忽暗,他剧烈咳嗽着,烟袋磕在桌沿发出钝响:“老二还是不送去读书吧,免得像她姐一样读得好,一旦辍学会更难受。”我夺门而出,蹲在屋后柴堆旁,默默流泪,直到午夜的月光把自己纤弱的影子揉碎在泥地上。如果可以,我宁愿辍学回家让二妹也踩踩学校的大门。可贫瘠的时光里,从来没有“如果”这个选项。
为了补贴家用,初一那个寒假,我去了集镇街上一个同学家的制糖作坊打工,当时主要是制作花生糖、饼干和棒棒糖之类。将铁锅支在土灶上烧得发烫,粉红的花生米倒进去翻炒,“噼里啪啦”蹦得满灶都是。然后,把花生米放进簸箕里,我的师傅快速地左右拨动簸箕,我则用铁瓢舀起熬化的金黄糖浆,让糖浆一点一点地滴入簸箕,花生米在簸箕里快速翻滚,随着糖浆的滴入,裹着糖浆的花生米越来越大,直到花生米有大拇指粗时,花生糖基本成了,接下来,等上半把天,糖浆完全冷却变硬,一颗颗雪白的、甜蜜蜜的、嘎嘣脆的花生糖就算是完全制作成功了。
远口中学旧貌。
那个寒假,我和工友们起早贪黑,不停地制糖、包糖,纤细的双手长茧,开裂,渗血,双手粗糙得像栗木树蔸蔸。但一份付出,就有一份收获。那个寒假,我挣了十五块钱,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可解决了春季一半的报名费啊。
隔壁三嫂见我家实在困难,在我不读书的周末,就带着我去远口集镇倒运水果卖。曾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批发的是本地山葡萄,批发着一块五一斤,卖两块钱一斤。她不会算账,我不会看秤,我俩分工又合作,她负责吆喝,称重,报数,我负责算账,收钱,退零。日暮时分,一挑葡萄终于卖完了,一算账,我俩共赚十四块钱,三嫂分我一半,算是相当不错。
就这样,每个寒暑假和周末,只要有机会,我就跟着三嫂和寨上的人,去挣钱。我们去辣子坪淘捞金,去山上打蕨菜和竹笋、挖折耳根和中药材、砍芦苇草和竹子等来卖,还干过挑砖挑瓦的苦力活。
从我们鸬鹚村到广溪冲约四公里,那会没有公路,全靠翻山越岭步行,大山那边的百姓要想建砖房或者盖瓦,必须得用人工挑运。
初一那年暑假,七月的太阳晒得黄泥巴路面撕开一道道裂痕,三嫂告诉我说挑砖去广溪村有工钱赚,我操起家里的扁担,挑起两个比我身子还宽大的撮箕,毫不犹豫地加入村民的挑砖队伍。我一头撮箕放进五个砖块,一挑约五十斤,紧紧跟着大部队奔走在羊肠小道,时而上山、时而下山、时而顺着山腰一道一道地拐弯。队伍里有人笑我:“读书的,干这个活路可能不行哟。”只有三嫂,一边抹汗一边怜惜地看着我说:“日头太毒,山路远,不好走,少挑点。”我点点头,紧紧跟在三嫂后面。
烈日似火,熏得山路两旁的小草像蒸熟了一般,蝉鸣似一张细密的网,织满整个山野,追着人影,一路缠缠绕绕地铺陈开来,躲都躲不开的夏日喧嚣。刚爬上凉亭坳,我已气喘吁吁,汗水浸透了我的前胸后背,沉重的扁担隔着薄薄的衬衣硌得我肩膀生疼,脚也似灌铅般沉重。三嫂见我这般吃力,赶紧扯下自己的毛巾,告诉我先垫垫肩膀。果然,垫了毛巾的肩膀,疼痛感减半,我咬紧牙关,跟着三嫂继续前行。三嫂说:“挑担不走,压猪压狗。” (酸汤话,意思是挑重担的时候,要小跑,越慢越累。)
每次回老家,都要带上孩子们到家门口的清水江划船游玩。
山那边的半山腰老枫树下,扁担“吱呀”弯成月牙,终于忍受不住,我踉跄靠树,蹲下歇气,脱鞋一看,左脚脚后跟已被解放鞋磨得又红又肿,难怪,火辣辣地痛。三嫂说距离广溪冲还有一个山头两道弯,忽然想起书本里的“蜀道难”,只觉山路更难。
片刻歇脚后,我拼命跟着大部队继续前行。大伙后背的汗渍,一半湿润如洗,一半风干成一朵朵灰白的盐花。咬紧牙关,继续坚持,终于到达大山深处的户主家,那一刻,我再也顾不上什么,一屁股瘫坐在地,掀开肩膀一看,肩膀已压出紫红印子。主人见我年龄最小,还是女娃,忙招呼我喝口凉水,还不断感叹:“这姑娘不错!”
挑砖的活路,我连续干了五天,挑了二十多个来回,挣了三十来块钱。
这样的生活,不努力读书跳出农门,怎么行?
夜晚,舍不得多费煤油点灯,很多时候,我就趴在火铺边,借柴火微弱的灯光复习功课。那跳动的火光忽明忽暗,却始终照亮着我心中的梦想。夜已深,火铺上的柴火熄了,可我仍舍不得去睡,便点起煤油灯继续看书,可书页刚掀开几页,父亲总会低声催我熄灯——家里的煤油钱,实在紧巴巴。
家里看书条件受限,我便万般珍惜在学校的读书时光,把每一分钟都抓得紧紧的。早操前的清晨,我攥着英语课本沿清水江公路跑上四五里路,再喘着气往回走,一边抹汗一边背单词。同学笑我“晨跑背书两不误”,我却把这苦差事当作“双赢”的秘密武器。
下晚自习教室熄灯后,我舍不得跟着室友去寝室睡觉,经常点盏煤油灯继续在教室看书。班主任周老师知晓后,与吴校长商量,特许我去教师办公室开灯学习。那十五瓦的灯泡把整个办公室的角角落落照得透亮,办公室桌下还有微弱的炭火,温暖极了。老师总叮嘱我“别熬太晚”。
那盏灯,照亮了我眼前的书本。那炉火,温暖了我酸楚的心,至今想起,仍有股热流漫过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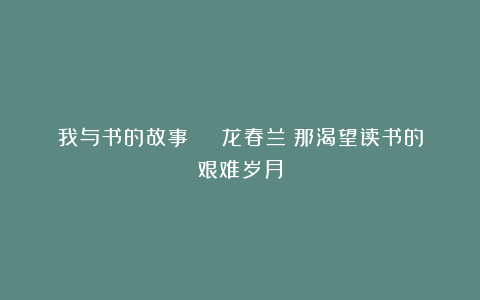
那会读书,学生需从家里带大米到食堂换饭票,但菜却要另外花钱买。我总是用罐头瓶从家里装一瓶黑黢黢的盐酸菜去当下饭菜,咸酸味儿能撑一周。那时能吃饱已是幸事,哪敢想营养二字?早餐,买不起三毛钱一个的包子,上课时,肚子“咕咕”抗议,我只好左手按住发空的胃袋,右手握紧笔在纸上疾走,试图把饥饿感驱散在全神贯注的听课中。
这点儿饥肠辘辘,总在领奖时被抛到九霄云外。每次站在学校的领奖台上,我都把头高高昂起,看着台下头投来的一双双羡慕的目光,听着那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我内心被浓烈的欢喜感充盈着。
人世间,有一种修行叫阅读。图为作者带着二宝在图书馆阅读。
远口的老街很长,伴着清水江,弯弯的,似月牙,街两边全是住户和店铺,从北端的街头到南端街尾的学校,大约要步行二十来分钟,每次路过老街,总有人从店铺里探出头:“那个姑娘就是远口中学的第一名!”“妹,进屋坐坐,讲讲你是怎么读书的?”“我家丫头要有你一半省心就好了……”乡音裹着笑纹,让灰蒙蒙的水泥路都亮堂起来。那会的自己是老师眼里的“读书苗子”,是这条长街上被念叨的名字。那些日子虽苦,可我浑身上下胀满了劲儿——考上师范,端上铁饭碗,供弟妹读书、让父母歇肩,便是我攥紧拳头要奔赴的光。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初二暑假,一向身强体健的父亲突然重病不起,床榻间“哎哟哎哟”的呻吟,似一张黑色的蜘蛛网,紧紧勒住我每一根神经。母亲刚在这个暑假生下五弟,家中却无半分添丁的喜悦,只有令人窒息的压抑——父亲的医疗费、弟弟的超生罚款,还有我和三妹、四妹的学费,笔笔开支如大山压顶。深夜辗转难眠,泪水一次次浸透枕巾:难道我真的要被辍学了吗?
夜,漫长得没有边际。我坠入无尽的黑色漩涡,拼尽全力挣扎,却始终触不到希望的彼岸,在黑暗中彻底迷失了方向。
转机来自三嫂的提议:“广溪村偏僻,家家没冰箱,你背冰棒去卖,肯定好卖。”这话如溺水者触到浮木,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第三天,天刚破晓,我步行四公里到远口集镇,在冰棒厂租了冰棒箱,批发了满满一箱冰棒,朝着十多里外的广溪冲出发。冰棒箱很大,超出我身子好几公分,虽只三十多斤,但烈日当空,脚下全是碎石公路,背上的箱子慢慢沉重起来。冰棒箱的铁扣抵着胸骨,每喘一口气都像顶着石块,湿透的衬衣黏在肩头,我知道我的双肩又被勒出了血丝。
行至鸬鹚村便转入崎岖山路,慢慢爬上高高的凉亭坳,再沿着山腰一弯又一弯地拐,背上的箱子愈发沉重,我双腿颤抖得厉害,我打算歇息一会再走。刚靠着一棵古树坐下,几个从大山走出来的村民见我,便在我对面坐下,一位老汉竟说:“姑娘,别卖冰棒了,来我家做儿媳,我家有砖房呢。”我呛声回绝:“呸!谁稀罕你的砖房!”我立即起身,不停地安慰自己:“世上好人多,好人多。”但内心还是比刚才胆怯了许多,脚步比先前快了几分。
当日头爬上广溪村晒谷场草垛时,我终于晃进广溪村口。“卖冰棒!卖冰棒……”我怯怯吆喝道。很快,村里的孩子们捏着硬币,从四面八方涌来,“我要一根冰棒!”“我要一根雪糕!”很快,冰棒卖出去了一大半。
远口中学新貌。
时光飞逝,转眼,燃烧了一天的火球也累了,它慵懒地耷在西山,将大地镀上了一层橘黄。还剩有一些冰棒怎么办?挨家挨户去卖?对,只有这个办法了,不卖完这一箱冰棒,那我这一天不是白折腾了么?于是,我鼓足勇气,背上冰棒箱,铆足劲,奔走在山弯弯的一户户散居人家。我一边走,一边大声吆喝:“卖冰棒!又甜又冰的冰棒!”
暮色漫过山头时,冰棒终于卖完,我长长舒一口气,背着轻飘飘的冰棒箱,脚步轻快地往家里奔去。
回到家,算账时惊喜不已:这一天竟挣了六块六毛钱,比挑砖轻松多了!
整个暑假,我卖冰棒挣得两百多块钱,既给父亲续了药,又缴了学费。更可喜的是,我在卖冰棒往返的路上,不停地背诵手抄的英语单词,让我那个学期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好几次测验,还考了满分。那段背着冰棒箱走山路的日子,终成“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注脚,在记忆里闪着光。
“皇天不负苦心人。”初三毕业,我顺利考取天柱民族师范,一家人欣喜不已。比起那些“八年抗战”(初三复读多年)的同学,我无疑是幸运的。
十九岁那年,我如愿站上了梦寐以求的三尺讲台。尽管月薪仅两百元,却足够给父母买点好吃的。更重要的是,我用这份微薄的工资供四妹、五弟读书,五弟大学毕业后还顺利走上了工作岗位。唯一的遗憾是二妹三妹没等到我上班领工资,便已错过了读书的年纪。
就这样,读书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家人的命运。
现在,给二宝讲睡前故事时,我会说起《凿壁偷光》《程门立雪》《闻鸡起舞》《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典故,也会聊起自己的读书岁月。天真的二宝总是听得入神,还会奶声奶气地说:“妈妈,这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吧!”我笑着告诉孩子:“妈妈不算人上人,也不能给你大富大贵的生活,但至少没有让你成为留守儿童,我们一家人天天在一起,多好啊。”
“妈妈,我念哥哥一定很想他爸爸妈妈,他们出去打工好久没回来了。”二宝望着寄养在我家读书的表哥说道。
如今,每当看到家境贫困的孩子,我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总会尽一点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每当遇到辍学的孩子,总会千方百计劝他们重返校园;每当碰到厌学的孩子,总想和他们聊聊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故事——想告诉他们,不论时代怎么变,读书都是提升自我价值的最低门槛。我知道时代不同了,他们或许很难理解那份对知识的热忱。
也许多年以后,二宝也会嫌妈妈的“老掉牙”往事太过陈旧,但那些在困境中坚持着捧起书本的时光,永远是我记忆里最璀璨的珍珠。
就像那句话说的:“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没有脚踏实地的付出,哪来收获时的喜悦?没尝过生活的苦,又怎会懂得珍惜当下的甜?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