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画语录讲录(五)
变化章 第三
引言
绘事,是寄笔墨以应真,
是画的寓言。
因形取象,
无关俗目之美丑。
人不知而不愠者,
可以习绘。
——连山先生
为禹老道兄作 石涛清
我们怎么样面对圣人的言语,然后把它转注为自己能受用的东西。
比如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注这一条时,你下意识的想法是不是要把这句话给分解开,然后变成一个你能把控的一个道理,大体知道要说的啥?是不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对吧?还有另外的可能吗?如果我们学习的方向是这样的,看到任何圣人的语句,我们都以凌空的方式试图击破它,然后总结它,若都是这样学习,是很困难的,你从外边是攻不进去的。
文字是可左可右的,任何一个文字,比如“志”是什么,一看,哦,是志向;志向是什么呢?哦,志向是修道;修道怎么修?哦,志向是画画。这就像打台球,一竿子打到台球,它运行会撞着边,会反弹突然变向,你逮不住这个字的意思,你发现你拼命想思考这个字的时候,你如果不给它搭配一个字,这个字你击不破它,但你只要给它个搭配,它就把你引到外面了,志于道,道在外面,志于德,德在外面,志于画,画在外面。它一下子就给你转移出去了,思维就打滑,你意识不到的时候,它已经给你悄悄转移了,你接下来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臆想,它把你带出去了。
这世间有的人辩才无碍,所以有个词叫诡辩,我们叫偷换概念,实际上就是他把概念偷换掉了,就像刻舟求剑,尽管在船上做了记号,确实是从这里掉下去,但你不知船慢慢移动,你做的记号虽然没变,但记号引的东西已经不是它了。文字就是这样,我们在书院训练的就是如何让文字与我们发生滋养的关系,而不是努力地如何去解决文字。
怎么叫发生滋养呢?什么时候我们看书,打开书本看到一句话,一个字,一个词,你能够不打包的去思考这个字,我讲的打包是,你一看到志就想志是啥意思,你一看到唯庸有光,就想庸是啥意思,然后再去想光是啥意思,见一画章就去思考啥是一,啥是画,啥是一画,“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大禹也搞不懂,不要说我们了,多一个文字,就多一个天幕,但人又没奈何,又不能不用文字,没文字没办法交流传达,它是在一种生死的矛盾中,生也是它,死也是它,你真正与文字之间有了良性的触发,那文字能救你,否则你识字越多,思维越丰富,越被埋得深。
那么我们通过不断地在书院学习,跟着善知识学习,就多了与文字一触即发的功夫,这就叫触发,不叫解释,看到这个字,你真正的生命气象能够从这个字的内部把这个字给它胀破,就像鸡孵蛋,鸡蛋从内部胀破,而不是老母鸡对着鸡蛋老是在那想,什么时候能变成小鸡呢?它理论上是能变成小鸡的,然后你就写论文去了,真正鸡的出生是小鸡从鸡蛋里面胀破出来的。这时候如果鸡蛋是个字,有一个活泼泼的东西一下把字胀破了,字没有了,但字所有的功能都完成了,它激活了一个生命。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让先天的东西从圣人的文字中从里面胀破。
是法非法,即成我法。
十二册寄上禹老道兄正。
苦瓜和尚濟
论语这几条,我们都很熟,但是我们胀不破,难点一堆,还以刚才的举例,“父在观其志”,为啥是父在,什么是个志,如何观,眼睛看吗?“父没观其行”父已经没了,如何观,谁来观,观谁的行?你看,一堆问题呀,如果是安抚自己,自己对自己谈不上是观,如果是别人,别人谁观你,邻居吗,还是你娘,还是你表姐?怎么是个志,怎么是个行?然后又来了一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啥是三年,怎么是父之道,是个什么道?这里面关键的字“志、行、道”,都在里面了,“可谓孝矣”又出来一个“孝”字,它几乎是论语中最难参的,哪一点都让你头大,如果你是泛泛的自欺式的想解,那容易得很,你就用白话转一下,父在时候看他的志向,父亲死后看他的行为,三年不要改父之道,这就叫孝了。
背书是没有用的,换个方式背书更没有意义,日常你们同门在一块儿,无论大学人小学人,只有所有的活干完了,坐那儿倒杯茶,翻开书来参一条,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活动,完全可以当游戏呀。每个人都很诚意地参与到这一游戏活动中,这个就叫参话头,古代精进的学人就是这样,寺庙中精进的和尚他也是这样的,他们对古今公案烂熟,任何一个和尚提起一个话头来,大家就可以有实感,它是真正的思维的一个洗礼,它会对人有重建的作用,我们继续这章。
“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没见过谁能真正的具古以化,“尝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多半都是泥古不化者,为什么没有见具古以化者,是因为什么呢?知见把我们拘滞了,“识拘于似则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我们要全神贯注于我们要看的东西,学习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这个时候思维就不能再多动了,这段比庖丁解牛到了“至于族”还机密的地方,就像刚才论语那一条,就像蚊子叮铁牛一样,根本下不了口。
“识拘于似则不广”,我们看这个句子不要当成石涛在说,他就是你的问题,我们每一个真诚活着的人,不仅画画会遇到问题,你干什么都会遭遇这样的问题,你学做生意,人家咋做你咋做,都叫识拘于似,学个皮似,学个皮相。比如说你致力于礼仪学习,你只是看看礼记里边的各种礼仪,包括丧祭你都会背,中国哪个地方有祭祀,你都跑去看,你都未必能入门。不会学的人,学得越多越学皮相,很多搞企业的人自己原来挑着担子去卖苦力的时候还能赚点钱,赶到做大的时候,上个商学院,就把生意做砸了,离开他对他自己做的事情的真诚的体贴,专心于套路的学习,很少有人能跳脱出来,并不是说商学院不能上,商学院是给什样的人上的,是给真正能身临其境的人上的,他听到的所有案例都当做自己曾经发生过,他不再是外在的观望。书院是给什么人上的,是给能与圣人同此心的人上的,而不是外在观察圣人所为的人,你要转到跟圣人同此心的内部去,就像刚才说的,那个生命契机一定是在鸡蛋里面的,所以让鸡蛋最后成为小鸡,绝对不是外在给的终极结果。外在只是提供一个因缘,它真正的发机一定内部就有。所以,你们不带着内部就有的发机去读,就没有用,你知道注啥?你以为是注文字吗?
我们基于这些真正能激活我们内在的发机,内在发机只要启动,文字就会被撞破,你就会发现圣人不我欺,贤人不我欺,人家说的话都是有的放矢的,你要不带着自我本有的东西看这个,你就会走神,带着你本有的东西,你绝对不会走神的,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正是他正在说的这个,难得啊,隔几百年还有人相应。你会发现你在学画画遇到的问题,他帮你解决,如渴者遇到水,怎么会走神呢?真的要对自我有感知,知己才能讲知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基于此来说的,这个知不是外知,不是泛泛的知。所以,历代画画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用功也画不好,这就是拘于似就不广。“故君子惟借古以开今也”,君子是主体,所以古和今才能为他所用,人是主体,每个人有君子之身,你们每个人都有主体,无论是诸圣诸神,还是历代画坛圣手,都会变成你的助缘,你不是要去学石涛,你也不是要去学颜真卿,你也不是要去学范宽,恰恰因为你在,石涛、范宽等画家都来成就你,会成为你的助缘,本末不能倒置,不要把主次颠倒,主次一颠倒,你就变成一个可怜的,每天伏案不起,腰都累弯的所谓学画画的人,除非是你疯了,想去皓首群经,想去邯郸学步。
为禹老道兄作 石涛清
“又曰: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石涛为啥能言出必杀,我们也学了不少,说个啥都是皮相,言语没有透彻,家人卦里面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有物”,说话一定要有触点,不是空说,我们也讲有法无法,画画的人大都是空说,他只是看着词好看,你要知道这个路径他是有根基的,“至人无法”然后俗人就以为是无,用无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前话后话之间是互相补救的,不是为了补救话,而是补救听这话听岔了的人,一听“无法”,我们就会下意识着眼在“无”上,“无法”不是“无法”,立即给你兜回来了,所以言语是救弊的,不是为了给你讲道理,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掉入坑里,言语再把你从坑里拽出来。你如果没掉入坑,根本不需要拽你,如果没掉入坑,根本不需要去学习,只要学习,说明你知道掉坑了,掉坑了就需要去捞你,文字就是捞你的。“至人无法”,至人他已经抵达了,但是也不是无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看似在做文字游戏,是就我们用心处来说,无所不用其极,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有法还是无法,是有路还是无路,正因为他无乎不在,这个“无”是万有的意思,哪是真的无呢?所以老子说“当其无,有室之用。”“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两者同出而异名”老子为什么这样说?先讲无,再讲有,再告诉你无就是有,不要以为无是无,这只是两个不同的表述。就其万有处讲是无,就其个别处讲是有,任何一物就是有,但是这一物与所有的物是一样的,所以它就不以有的方式存在了,因为它跟砖头瓦块没有不同,不是针对它的形状来讲,而是针对万类一体的大本处来讲,那这个个体就变无了。
一滴水滴到大海里,这滴水就无了,它不是没有了,它和大海在一起了,这一滴水单独时叫一滴水,这滴水掉入大海里就不再是一滴水了,它就是一个大海的水,这是讲有无的关系。譬如大海水,海水有海沤,沤是泡沫,浪一起就是一朵一朵的浪花,浪花是不是有,但一浪下去,一浪又起,后浪起前浪灭,前浪起后浪灭,浪花翻起来一炸又到水里去了,浪花没有了,但它真没有了吗?它还在海里,所以对大海来说它叫无,对浪花来说它叫有,但所有的有瞬间就消到无里去了,而大海的无不是没有啊,它叫大有。
人只要有三岁能听懂话,圣人的话就能听懂,我们之所以以为听不懂,是你下意识地以为他讲的是道理,他根本不给你讲道理,他讲的是常识,哪个人不懂常识呢?所以你们在这如果以“为了知道什么是常识”而学习,你就不会畏难,你马上就发现与圣人之间没有年龄的界线了,七八岁也完全可以与圣人同呼吸。人心不管年龄大小一样是完备的,只是发用的时间有早有晚,有人发用早,像项橐、颜回这样;有人发用晚,像孔子这样的。但大多人是不发的,虽然生来是种子,但毁了芽,一辈子没有机会发,所以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经是不变的,权是变的,不变的是无,变的就叫有,如果大海是无,那海浪是有,海浪不断发生变化,大海没有变,这是经和权。
画画无论什么样的派别,真正的好画都是在这一个点上会通的,不管画什么题材,人物、走兽、鬼魅,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画?人,才是画的主体,所以人品即是画品,同样是金属,这是金子,这是铁,同样打一个镯子,金子就金贵,为什么呢?这是材质决定的。所以,你若是金子,你画什么题材都是金光灿灿的,海德格尔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写了一篇文章“论艺术作品的本源”。
我在最初画画时,画了一年多就画不下去了,我若对一件事情如果自己搞不明白,不会稀里糊涂的马上跟着干,画了一年多,实在搞不懂画画的审美标准,怎么叫好呢?我问了能问的人,他们说的比我还胡扯,我根本不信,我在《目击道存》书里回忆过这段,痛苦来自于找不着人聊天,聊一聊关于困惑的事情,到底什么是好画,我以什么为向度去学,然后背着包去美院走走,那是高等学府啊,到那一看,他们连想都不想这个问题。
曼衍之藤自随其曲傅,有主有宗,督也,
人能具眼,必有见也。
乙巳三月 连山
今天我给你们讲不要随便瞎练什么皴法,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排斥这个,人家讲各种皴法要学几年,我说学几年干啥呢,为啥要学这个皴法呢?当你学熟练了,你连思考的想法也没有了,你不会的时候知道不会,一旦你误以为你会了,你问问题的能力也就丧失了,你学两年,画的谁都想要了,你就会自以为你画的好,你会自大我慢,就再也听不进去别人对你的质疑,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对自己的质疑,不能自己把自己给消灭掉了。
所以,有将近七八年我也不再画画,背包进山去晃悠,沿途进某个城市的旧书店买几本书背回来,在城市基本上不打工,在山里面也没啥事干,我记得在山里,八块钱在农民家租个床搭伙睡,烤两个饼子带上,如果吃饭一天十五,不吃饭一天八块。太阳还没出来,我已爬到山腰,坐那里看日出,那年出去是赶过年时一月份,第一站先去离我们那里很近的刘邦藏身的地方,皇藏峪,天天躺着看头顶白云,然后到了其他地方。我基本到哪里,都是住旅馆,白天在石头上看,看饿了找东西吃,吃饱后渴了困了,回旅馆睡觉,基本上不画画,突然有几个名句来找我,就写诗,写了好多诗,实际上躺着是不快乐的,是很痛苦的,很悲伤,觉得找不着门路,看着满目青山不知道怎么画,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的去描摹,又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就是属于那种上不能上,不能下,一事无成,还眼比天高的人。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与我父亲的对话,当我画不下去又没有路走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坐那儿看书,我父亲端水洗脚,我十几岁之前天天挨打,最后一次是十六岁,上了高中也挨揍,我与父亲的关系原来很紧张,基本上十六岁之前我都不敢看他,他在那屋,我一定在另屋,绝对不会没事找事跟他在一块,如果不得已一块儿出去住旅馆,我得装睡着,反正不能让他看到我醒了,我醒了他就问我作业,让你始终有恐惧感,那次以后好像他突然对我的态度变了,不再揍我了。但是,我们聊天也不多,洗着脚能看出来他心情很沉重的说“我就没见过一个人啥都不干了立志画画,却天天不画画的,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啥呢?”我正看着书,他问我,我把书合上说,“我当然没有忘这个事情,我不是不画画,我是还没找到门呀,我没找着门就以为找着门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找门了,我现在最起码得保护好我现在还没找着门的觉知,我知道我还没入门,所以我还在努力。我们这个家庭祖上有很多画家,我如果像一般的画画那样上来就画,也会画的自己也觉得很满意了,我是干记者出身的,我也找几个人宣传宣传,我也能办画展,成为这协会那协会会员,这不是我的理想,对我来说,如果我到死的时候,即便天下人没人知道我画画,但我觉得自己入门了,我也会死得其所,如果我按照一般的正常的想法,通过个人的勤奋努力,也让自己活的名声很大,但我自己会很清楚我是没入门的,我会死不瞑目。”我父亲听我讲完说,“哦,不说你了。”从此我们爷俩就不再聊这件事情了。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入也,是为不动。
乙巳三月 连山
对我来说回忆当年,就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特别清晰的地方,尽管一直糊涂的活着,但是那个特别清晰的地方我始终有觉知,所以从来没有盲从过,不管世间多么名声大的画家,看不起他终究看不起他,看不起他不是因为他名气大,而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会蔑视他。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有一“不惑”,如果不能保护好这个“不惑”,就会带着“不惑”迷失在这个世间,你从来没有迷失过,只是你用自以为是的成果遮蔽了你的“不惑”,这叫“道隐于小成”。你只要在某个领域有进步,你只要自己也认为有成就,你就迷惑了,你几乎没有救,庄子为什么说“道隐于小成”,人最终是以自己绝对不可能惑的东西带着自己走出迷失的人生,这叫以不惑解惑。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觉得自己迷惑了,是你没迷惑,只有不迷惑的人才会知道自己迷惑了,只有不迷惑的人才知道自己病了有问题,真迷惑了你就傻了,你会觉得你清楚,庄子说唯有愚者自以为觉,你要听清楚这句话,所以不要总是说我这听不懂怎么弄?画不好怎么弄呢?你要在这个点上打得住,从此你不会懈怠或疲惫,不会了,那个你与生俱来的“不惑”会持续给你真正的力量,让你一天天壮硕起来,成为一个雄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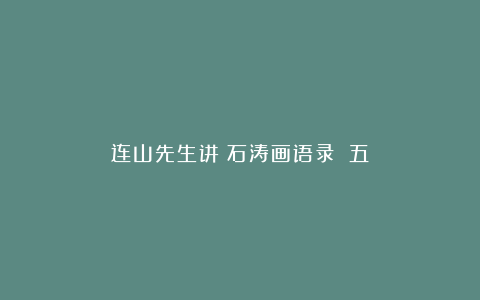
迷失是上天对每个人的保护,你想你不迷失怎么能行呢?哪个人不喝点迷魂汤能活下去?老百姓说,人一出生,喝碗迷魂汤,过了奈何桥,你的人生才能半清醒半糊涂的活着。你不能在人世间从里到外都清醒,从头到尾都清醒在人世间是不能活的,也就是说你靠洁净是没法活在这个污浊的世界的。真正的清醒是你知道这个污浊的世界污染不了你的洁净,你就可以天地任我行了,这不就是颠沛、造次必于是了吗?庄子称为入俗随俗,孔子称为入其乡随其俗,能顺人不失己,能随喜,能耳顺。如果水没有营养物,鱼咋整呢,如果大地干净,万物都不能长养,所以垢是净的养,迷惑是不迷惑的保养,正因为迷惑,难得糊涂地活着,这个不惑才不会被知识毁。
所以真人不说破,智者不辩,不辩不是他不明白,而是他不需要用辩论来表明自己明白,他只要活的明白,这世间风晴雨雪,污淤浊水伤不了他,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保养的功夫,这叫天保。否则的话,你以为你自己不惑,表里要如一,什么是表里如一?就是表迷惑,里不迷惑,而不是里外都呈现出不迷惑,你又不是透明的人,怎么可能呢,里外都不迷惑是你想象的,没有里外都一样的,里外一定不一样,里外不一样才叫偶,有左有右才是中,两面都是右,有这样的柜子吗?垢和净显相不同而已。
这与绘画是一样的,它不在似与不似上去讨论,如果我们不是真正带着不惑去画画去治学的,你就会被似与不似,这两个看似有道理的选项引诱,选画得像或选画得不像,以为画得不像是高境界,这都是自嗨。所以“一知其经,即变其权”,有本的时候就变了,绝不是本和变是两端,我们在讲不变的时候,变就在其中,我们在讲“无”的时候就有“有”,庄子说“虚则实,实则伦”,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不是说先要宗经再涉事,书院以宗经涉事来激励学人,讲宗经就是涉事,绝不是给你讨论说:我认为宗经固然重要,涉事也重要,你看多少人这样,说这样的话都不嫌丢人,他以为他表述的更加圆满,我认为不仅要宗经,还要涉事,说这话真是无聊。
为禹老道兄作 石涛清
宗经、涉事,二者同出而异名。所以石涛说“一知其经,即变其权”,是一个东西的两个表述,“一知其法,即功于化”,石涛为什么举这个例子,石涛画语录写在画论之中,古代画家都读圣人书,他们熟悉经与权,但不一定熟悉法和化,所以石涛用他们熟悉的四书五经来譬喻怎么画画,今天我们看这个就成了万仞宫墙了。今人不读书,看的都是皮相,所以石涛画语录变得更难,石涛举的例子反而更难。所以“一知其经,即变其权”是就当时读书人都知道来说,“一知其法,即功于化”,法不是技术,法即是化,我们一说法就变成法了,与化找不着任何的关系,法即是化,化就是化用,不能让我们受滋养的都不叫法,叫操作,变套路了。
“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画是天下变通的大法,从画扩充到天下万事万物,天下所有的事都和绘画一样,唐代张彦远说“画与六籍同功”,就是从这个地方说的,论语中“今汝画”,同样的字不同典,论语中是讲冉求描摹,你要想从外面撼动一个鸡蛋让它变成小鸡,那是不可能的,你会“力不足”的,这个鸡蛋之所以从外面给它个因缘,它能变成小鸡,是因为鸡蛋里面有变成小鸡的洪荒之力,如果里面没有生机,外面怎么搞都没有用,因缘只是缘,而不是主体。所以孔子讲冉求的“画”,不是这个画。
“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就是画,所以张璪说“外师造化,终得心源”,宇宙的一切发生视听言动的东西都是师造化的过程,我们如果没有空空如也虚静的心去转化它,只是徒摹其相,就像荆浩《笔法记》中老叟说的“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
“山川,形势之精英也”我们看山只是固体,画家看山是活体,动态的,是地气,大地蒸腾气息的鼓荡,它鼓荡出了一个个的山脉。今天人更容易理解,地球是地壳岩石,地壳运动挤压形成了山脉,当我们去远观一片山脉,从断崖式的山体我们会看到是气息的鼓荡,岩浆流淌起来遇冷冷却,有的大地像岩浆流淌出的气息,今天以物理来解释是气息鼓动的结果,古人没有能够以今天的科学观念看地球,但他依然正确,这就是气,虽然石头是坚固的东西,但它就是气,我们再看古人的画,画得就是气息,仿佛在滚动,这叫通天下一气耳。画画是布气的过程,我们经常会以这个表述画,怎么理解气到底是个啥?怎么是元气而不是空气,元气不显相,它借万物显相,画画取相,不是取物,取物只是描形。
“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一句话讲了当年璀璨的几位大人,许道宁是在长安街头卖药,开了药铺,没有生意他就画画,来买药的人夸他两句画的好,他有时会送人家,他并不以画画为职业,卖药是他的职业,就像元四家吴镇卖卜是他的职业。中国绘画史上以绘画为职业的几乎没有,绘画为职业是近一百年的事,原来世俗的美工,画家具的,装饰房子的,这些都不算画家,他们只算是工人,他们是作为手艺人呈现的。画家是以绘为事的,以绘事进道的人,你们经常听到画家的故事,郑板桥的故事,徐渭的故事,达官贵人拿钱财来他不卖,但是卖菜的,贩驴贩马的问他要就给,因此我们看到所谓的画家脾气怪,画家不是以画画来做买卖的,你想拿钱来羞辱他吗?他视为对自己的羞辱,我怎么沦落为卖画的了,他只与有感情的人打交道,他也知道卖菜的人未必能看懂他,卖菜的人虽然看不懂,但是给一筐菜想要你的画,这是感情,不是交易,他们注重的是感情,世间人以为他视金钱如粪土,也不是不要钱,钱得来的正当,孔子也不是不要钱,绝对不是凭空说讨厌什么,一个君子连瓦砾、砖头都不讨厌,他怎么会讨厌金钱呢?金钱如果是取之有道,该要的可以要;如果取之无道,无论怎么给都不要,跟你没有关系。
为禹老道兄作 石涛清
“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这是有形有势的,我们为什么讲取势,前面我们讲虞世南的《笔髓论》,笔一起就取势,它完成一个势的流转,起承转构成一个大势。以石涛、范宽为例,从一笔开始看,如何起动?树是向那儿走的,如何与下一物体呼应?无论是对面的树还是石头,这种呼应无非是顺势的走向,接下来,这边山石要么形成互倚的势,要么顺势走,或顺或逆,怎么都可以,关键是接下来你能把它收回来,凡是发都能收回来,画画无非是像海浪,起收起收,你不需要提前做好操控规划,只是你想画什么?要画牛马,就取与牛马有关的东西,马槽、草,再到牛马身上。你想画山,从一个土坡开始,从一棵树开始,从一个人开始,从一个骑驴进来的开始都可以。你如果想画个风景,这时候你大体上心中是有一个向度的,所谓行必有方,想表达冬天的寒林,还是想表达夏雨的盛貌,还是秋天的苍凉的感觉,这是你心中有数的,你不能乱糟糟的就上来,也就是说你出门不能不知道朝哪儿去啊。
古人讲的预想,不是预想技法,你得有个“预”,得知道在这张纸上你要干啥,你想画个雪景还是春景。然后与心境有关系,古人为什么不随便接受人定制的画。比如,他心情特别得劲,你却让他画一个苦寒的雪景,他找不着感觉,画这个他觉得难受;假如他正内心苍凉,你却要画一个春江桃花,他觉得画得吃力,跟他的心境完全不相应。所以画是画家的心映现的结果,如果赶上时事,山河破碎,就像八大的画,任何一张画打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你很难从八大的画看出喜庆来,但这些悲伤它又是君子式的悲伤,哀而不伤,有一种苍凉的气息,但是绝不会一下就塌下去了,他画的东西都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具象的东西在里面,那个东西不会被消灭的,这就是人性情兼具的画,石涛画语录中会谈到性情的,没有这个,你好像啥也都能来,你不就是蚊虻负山的蚊虻吗?现在的画家不就是追求啥也都能来吗?“你想要个啥?”就像点菜,你点啥他画啥,这样跟机器画有差别吗?
所以绘画它既是大公的,又是私的,它一定要有私人的气质气息,这画才动人,而不是公共地学一些技术,为什么今天工笔画不能看,你今天看画展,整个几十年的画展都是工笔画的画展,因为它好操作,谁都能操作,画个人是这样的,摆各种莫名其妙的动作,或者表演哀伤,表演快乐,大家都一样的操作,长一样的脸一样的手,今天美术界已经变成加工界了,画家一见面就谈钱,你在哪呢,谁给你操作呢?就干这个事。哪有一点意思呢?
“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石涛是个内行,阴阳不是两个,阴阳是气度流行的结果,就像白天黑夜不是两个,是地球运转的结果,是太阳和地球配合运行的结果,绝对不是有一个白天有一个黑夜,显白天黑夜的相,但绝不是两个,就相来说是两个,就理来说是一个。
“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我们画画也是笔、墨、纸,只是生命气度的流行,才能对人有陶冶,而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去操作,劳役式的画画。我以前讲过我老乡画画把手筋都累断,但到现在画得还是这样的,几十年都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俗,他自己认为他创造了几种图式,可以勤奋地去训练,然后他以为这是他的丰果,找记者吹他的风格,自己还创个画派,我看我老乡这样我真的是羞愧。
甲辰八月 自绍兴参大禹陵,
寻天池不遇归而写 。
此平渚之景以畅怀怀抱,连山
还有搞文字游戏的,写的既似这个字又不似这个字,把画面占满,留空的地方用颜色涂满,说你看现在东西方文化已经交流了,在画上也要交流,美其名曰底子是中国的,然后画面是西方的,好多评论家说如此是创新,因为他只要出钱就行,评论说美术史上一大进步,他就是这种搞,怎么低俗怎么干,以此为创新。这些你们得知道,你才不至于对这种不要膜拜,也不要多么鄙视,如雁过太空,看到这世间形形色色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你就当成一只麻雀从空中飞过去了。
但同样是做一件事情,有些人是换钱币以陶泳乎我,有些人是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不需要再换成第三者,但是大多数人一定要让第三者插足。本来画画是他的事,但画画一定得换成钱,他才有收获了,这就叫第三者插足。你们想想有没有这种见不得人的想法,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要换颜如玉、黄金屋,下意识有这个贼心,觉得我只要好好努力,以后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是吧?
你只要带这个想法,你就是盗跖,你知道盗跖是怎么骂孔子的吗?孔子你不是有道吗,不是圣人吗?“子自谓才士圣人邪?”你为啥“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你的道贵在哪里呢?“子之道岂足贵邪?”大多数的人所谓学道,都是为了换取,他下意识的就有学了道会如何如何?这种志乎期费的修道方式就是商人,甚至于商人都不耻。论语第一篇就讲“人不知而不愠”,不是你真正修了,真有了道,你就啥都行,与行不行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不因为你德行高,你就有饭吃,不因为你生命能居正,你就能活的长,根本就不挂钩,但是你一旦下意识把它挂钩了,你就会以为没有混好,你看我这有道也没用,没有混好,你看我这书院也白待了,你总是带着来这儿好像要干一把,能背一包什么走的一种收获感来书院,那不如现在就走,避免以后日久生怨,因为真的不会有啥东西的。
最是此草与人亲
甲辰八月九日 连山
“今人不明乎此”,一言以蔽之,这个今人,在石涛的时候是今,那时候的人已经不明乎此,庄子的时候的人也不明乎此,我们现在的人还是不明乎此。什么时候都是不明乎此的人多。所以庄子说天下有道的人少,无道的人多,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这就是天理,不要打妄念,不要以为我只要修好了,以后走哪里都顺,不会被人打劫,想多了,还没出门呢就被人打劫了。
“动则曰: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动不动就说,张嘴就来变成习惯,“我是学范宽的米点皴的,高级,北派的太粗矿了”,那些宗黄公望的就会反感范宽,然后又会出来一些人开始顶礼范宽反黄公望,绘画的江湖就是这样黑吃黑的,两方徒子徒孙都对不起祖宗。他们无非是狐假虎威,借黄公望的名义来打压范宽,范宽的弟子们借着范宽来打压黄公望,都是这样。没有谁是真正的尊师,相当于后世的儒道之争,儒佛之争,都是徒子徒孙争地盘争粮食,没有谁真正在维护他的学脉。所以他们在争皴点,“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然后他以这套理论说求法乎上,要知道“求法乎上”上不在外呀,不是你学倪赞你就高明了,不是你学佛就比学孔子高明了,但世俗总以为是这样,今人不明。
“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那些线条细的,但是工细不等于不达,与画得黑,画得明丽没关系,像黄宾虹这样画得一团团黑未必不工,今天的工笔画画得这么工,未必不low,不是你看到的表象。“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有哉!”这种想法都是被某家役使了,变成奴才了,你不但没有用它,所谓物者,用也。中庸者,中用也,物物而不物于物,才能物物。人不能被物役,人是役物的,万物可以被我们调遣,我们使用万物,我们是役物的人,不能役于物,这就是格物的功夫了。阳明格竹,实际上就是役于物了,阳明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格竹失败了昏倒过去,对着竹子坐了七天,说格不明白我就不吃饭,那活该不吃,这个时候他完全被竹子给控制了,他还要坚持,这个时候他内心不是心,他内心中长了一颗竹子,消解不掉它,直到上天出手把他一下推倒,不就是昏倒了吗?醒了以后才有所觉察,晚年才回忆当年用蛮力导致格竹这样一个过家家似的游戏。
但是不明的人依然念念说阳明格竹如何如何,把物作为对象,你怎么格它?注意!怎么叫用错功,为什么阳明七天用错功了,因为他把物作为对象了,阳明也是因为这次用错功,才知道朱子同样用错功,到晚年时候他俩消解了,因为他发现朱子跟他同样是年轻出的错,晚年的朱子也变了,他才有了晚年的朱子定论。谁没有年轻过呢?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美丽的东西在外面,我们需要出去走一走,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好像每年不背包出去都要病了,感觉到时光流逝,想想我们村有人到死还没有走出二十里路远,就觉得替他不值,现在想想人家那一个笃定啊,我们村一生没走出二十里路远的人,在我们那里名声很好,他是个和善的人,他的幸福感绝对碾压村里所有人。
乙巳四月 连山
直到有一天我到了九华山,想想那个没走出村二十里的人,一下子有愧疚感,原来我心中对这样的人有轻慢感。那年我同学是坐车上到九华街,我是半路下车走上去的,就走小路爬了半天山路到九华街,然后这一夜激动得睡不着觉,明天要看九华山了,我那时候对山有特别的激动感,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向天台走,走了一两个小时都没见着山,雾大到能见度只有不到两米,只能看到台阶。对一个好不容易上一趟山的人来讲,看不到山心情非常沮丧,一路上生闷气,啥也没看着,走到一个路标处,一个箭头指到天梯,一个到十王峰。大多数人都朝一个方向走,我走两步一看才知道人为啥不从这边走,因为能见度太低,一个牌子在路中间竖着“此路不通,游人止步”,我那时候因为心情不好,你说不通,我就非让你通通,所以就我一人朝那走,走着走着就到了悬崖栈道了,栈道塌了,沿着断了的栈道慢慢蹭上去,就到了最高顶,整个峰高出云彩了,就没有雾了,极目楚天阔,我在那里兴奋了十来分钟,“今天赚了”,兴奋的来回跑,再下来几步,又到雾里了,跑上去两步,就看着蓝天,远处像蓬莱岛一样,这样来回走了几下,就让我怵然为戒,坐在石头上就特别悲伤,悲伤自己的浅薄,人为啥会有占便宜的心呢?
想到前面几个小时的不愉快,是因为这次来没看着,刚才那么愉快为什么?因为我赚了,隐隐听到下边天台的声音,我觉得我比他们赚的多,他们谁也没有看到山,就我看到了,那一天九华山就我一人看着山了,我就觉得我一下子有这样的想法而有羞愧感,我坐在那儿时间很长,一边看远方,一边眼泪出来了,那时候我特别多愁善感,然后觉得这些年吃的亏都是因为这个,自己不赚不罢休。当时很多想法涌过来,特别的感受是那天忽然觉得头顶盖没有了,呼呼的和灌顶一样,一边难过一边有一种好像一下接着气打开了,对一个能见度只能看两米来说,你能看十米你觉得赚了,要是能看一百米呢,那你瞬间又失落了,坐在这儿能看一千米,那对于一万米,对无边浩瀚的宇宙来说,你都能看着吗,你肉眼能看多远呢?你终究没有赚的快乐感,如果靠赚来有快乐感的话,你后来发现越来越没有快乐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自我跟自我,像小狗一样咬尾巴的吗?你进入到一个无止境的追逐上去了,就是那天在九华我脑子一下子被撞击了,脑盖一下子被打掉了。自此,回来发现看书也不一样,学习也不一样了。
负阴以抱阳,此绣球花也,非摹其形耳。
乙巳连山
“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没有用的能力,你就是被奴役了,“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有哉!”即便画得和人家一样,只是吃人剩饭,与我有什么关系,你生来不是吃嗟来之食的呀,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你不是来吃人剩饭的,但是你也不是来显摆你自大的,我谁也不学,我不吃人剩饭,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譬喻,你不能不学,你不学你终生吃剩饭,吃你自己的剩饭,吃了吐出来自己再吃,如何才能真正的不吃剩饭,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我到底是谁,与我何有哉?
“或有谓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约我也。我将于何门户,于何阶级,于何比拟,于何效验,于何点染,于何鞟皴,于何形势,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这段,石涛在写的时候,也心神鼓荡,特别有用力感,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不仅仅是同行之间,同门之间,甚至于跟他学画的人学道的人都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粘着,不是粘着于我慢,就是粘着于外盛,一提就赞美这个如何好,那个如何好,所谓这个博我,那个约我,他以为都是技术,博和约都不是技术,博和约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每天诚意地对待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八大法写白岳 连山
文集:连山先生讲《石涛画语录》
听打:曦彰
校对:明此
编辑:明徹
乐物自取通道
风自庄门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