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读书》是山水澄明推出的学术公益项目,聚焦一流学者作品,以视频访谈的形式,紧扣时代关切,呈现深度思想。
横版视频请参见文末
本期《山水读书》专访李零老师。如探案一般,追寻子弹库帛书残片中破碎的故事,揭开四时、五行与阴阳并行的系统,图与书中的神话渊源,帛书本身的旅行史。
(以下文字内容整理自视频)
《子弹库帛书》的重要性,就是它是到目前为止出土最早,唯一的战国楚帛书,战国帛书只有这一件,如果所有的帛书加起来也只有另一批,就是《马王堆帛书》。我们现在研究经常说简帛研究,但是简很多,帛很少。在西北地区还出过一点书信,那些都无法和这个相比,这是独一无二的。
《子弹库帛书》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它少,重要,这是从发现讲。从发现讲,其实有一个可以与之比较的,就是西方出土的《死海文书》。《死海文书》比它的抄写年代要晚至少一百多年,发现也比它晚。但在西方,《死海文书》是关系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西方宗教研究的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大家可以想见,《死海文书》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非常重要。
《死海文书》
约前2世纪到1世纪
《子弹库帛书》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牵涉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中国的选择术。可能今天听起来就有点陌生,其实所有的农村老百姓都知道,就是黄历。比如说看黄历,今天是黄道吉日,可以不可以盖房子?可以不可以娶媳妇?可不可以剃头?关于这样一种方术的研究,叫做选择术。选择术在中国是很大的传统,在过去应该谁都知道,而且这种类似的其实在西方也有。我们这样一比较,至少我们就知道说《子弹库帛书》和《马王堆帛书》,其意义不亚于《死海文书》对于西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重要性。
子弹库楚墓发掘现场
湖南长沙
但是我一开始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说了我一开始就是为了字。但是认字应该说是一个起步,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认出字是为了读这个书的,而且要理解这些书里历史文化的意义。我觉得这更深层次的东西是逐步越读才越能体会的,我一下读了四十多年,我才慢慢地体会到它的一些重要性。
(问)这件文物它是一个帛书中的三块,还是说三件呢?大概是多大面积?
三件,但是现在完整的是一件,另外两件是残片。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现有的残片看就是有三种东西。一种就是通常大家说的楚帛书一,我们现在就叫作楚帛书一号帛书。现在你看楚帛书都用的是复数,是三件。第一件我把它叫《四时令》,第二件我叫《五行令》。虽然我们知道有日书这种书,日书它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就是每一天选择良辰吉日,它是一天一天的。但是时令书是要比这更宽泛的,它是一年分为四季,十二个月,问的是每个月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所以它是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这样一种时令系统。我把它叫《四时令》,就是春夏秋冬,正月到十二月,一共二十四个节气。这就是一号帛书的内容,是最完整的。
另外一些残片,实际上原来也是有图的,它是按照五行来分的,也就是按照金木水火土,或者说木火金水土,或者土金水也可以,这样一个安排。那就把一年分成五份了,没法按照春夏秋冬分了,就有一种奇怪的安排,时令书也就是所谓月令这类的,如果是五行时令,五分的话,七十二天就是三十个节气。它不是二十四个节气,是三十个节气。而且最麻烦的是,明明有四个季节,它不按照四个季节,按五个,那七十二天往哪儿放?因为当时的时间是按照这个空间来分配的,就是春夏秋冬配东南西北中,这样中间应该放七十二天,但是没法放。
楚帛书残片
我们过去去考察五顶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北京的五顶是东南西北中五个顶是吧?先比如北顶,鸟巢底下就是北顶,有南顶、西顶、中顶和东顶,就是东顶现在毁灭了,没有了,其他的还在。那时候我和唐(晓峰)老师他们去找中顶的时候,他们说中顶在哪?我说中顶在哪,紫禁城已经把中给占了,你到哪找中顶去?我说你们就到西南角去,现在的中顶可以去参观,就在西南角。我们当时跑到那的时候,那是一个菜市场,中顶的匾就在那菜市场地上扔着,大家都是全是卖菜的。果不其然,就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按照传统的这个时令书来说,它有一种非常别扭的安排。就是把这个中塞在季夏和孟秋之间,也就是西南角。这种时令书今天大家都已经陌生了,但是在中国的术数传统里始终都是存在的,是按照这个五个方向来分配所有的日子。所以它实际上和四时令是并行的一个系统,一直到汉代的时候,还都是同时有两种时令书。
《子弹库帛书·攻守占》残片
那么第三个帛书,是应该属于兵阴阳的,它是讲攻,我给它起名叫《攻守占》。应该说这些帛书的名字是我们拟加的,并不是它原来有的这个名字。所以它是由这三部分,《四时令》《五行令》《攻守占》这三部分三个帛书构成的《子弹库帛书》,所以它很重要。现在大家知道兵阴阳类的东西,也是古代占卜里面特别重要的,而且是属于兵书里面的一个专科,这很重要,所以子弹库里面包含了这三种文件,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马王堆没有发现以前,看到的这件帛书跟《马王堆帛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图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图书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书都是光是用字写成的,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包括外国的文本也一样,里面它都是有很多图的。特别是我们翻开《汉书·艺文志》,看到目录里面很多书都是有图的。有图的书实际上一直都流传,但是后来可能是有一个逐渐减少(的过程)。中国很重视文字,文字非常发达,相当多的书是没有图的,就只有字。而早期的帛书,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图书。其实中国一直说的图书馆就是图和书是并存的,而且它在书里面,本身就是一个书和图,有时候甚至无法分开。
《子弹库帛书·四时令》
蔡修涣摹本
子弹库一号帛书里面的文字是转圈排列的,中间两个,一正一反,像个阴阳鱼一样。然后周围十二个月是转着圈,而且还都画了十二个月的月神。李学勤先生是聪明绝顶的,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大家经常研究楚帛书的时候,这可以说也是一种习惯。中国搞神话学的都特别迷《山海经》。《山海经》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不是说不可以读,但是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人们研究楚帛书的时候,往往就是看见它周围的这一圈神像,有的长着三个脑袋,有的是一个蛇身子,有的是一个猴。大家就会翻《山海经》,说这个跟那个山海经的哪个神怪比较相像,这么来研究。其实这个研究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因为是一种没有系统的比较。
李学勤先生真是聪明绝顶,他从《尔雅》里一下看见十二个月的月名,而且他认识古文字,他一对,他说这十二个月的名字都已经早在上面写清楚了,那就是十二个月神就叫这些名字,你就不用再找什么神怪,就是十二个月,每个月有一个月神。它是这么一圈东西,然后在四角上还有四棵树,都是有颜色的树木。它本来如果要按照五行时令,还应该有一棵树在中间,因为中间我们说了,已经被两篇文字占领了,所以就没有。
《四时令》
李零摹本
1990年
所以这个是《子弹库帛书》是一个很典型的,你很难说它究竟是图还是书,因为它连它的文字都是按照一套布局设计出来的,其实我们现在叫版式,就是lay out这样的东西,古人也都懂的,要怎么来安排这个图和这个画,所以它很难区分。一号帛书和二号帛书都是有图的。三号虽然是文字,但文字也是转圈排列的。所以它本身也应该认为是有图案的意义,所以这是它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学者对于这个布局是应该怎么看,说先从哪儿开始读?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先从哪写,还有一个问题是先从哪读,但是它是一个转圈的。有的人说哪个应该是上,哪个是下。如果转圈的话,就不好说,就只能说哪是起点,哪是终点?但是你无法说图怎么放,其实那个图拿到手里是转着圈读的,画的时候也是要一定要转着圈画。所以关于布局问题有很多争论,我也只是一家之言,但需要有一种自圆其说的这个说法。
当然现在大家的兴趣主要还是字,但我觉得实际上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其实这一点像李学勤先生他们原来也都注意到,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这里既然有四种颜色的树木,而且它里面提到的是五种木头——它虽然是个四时令,但是他们当时的四时令,也是一种互相镜面的那种关系,这里头虽然也露出了一些讲五行的端倪。我后来写文章,重要的一个发现,虽然它也是一个需要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心得,就是热气、寒气,它里面讲了热气和寒气,就说明它是有阴阳的,一定是有阴阳的,而这两个字也都比较麻烦。热字其实是也是通过马王堆的线索知道那种热字的写法,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又有阴阳又有五行,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子弹库帛书·四时令》
商承祚摹本
当然过去大家更热衷研究的就是中间短的那一篇,因为讲到了一些传说人物,伏羲女娲,和后来有点类似于羲和四子那样的四神,就像打垒球跑垒一样的那种方式,实际上《尧典》里也是那样描述的。
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要从短的那篇开始读。我和他们不太一样的,我是从比较长的那一篇开始读。我认为长的那一篇是讲岁,短的那一篇是讲四时,然后边文是讲十二个月,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结构和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比较大,我觉得还在于,它已经露出了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时期所呈现的那种面貌。因为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然后把二者合在一起才有所谓阴阳五行学说。至少这个系统暗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阴阳五行学说,当然阴阳五行学说是一个可以不断延展的系统,不断地把各种东西都都整合进去。但是至少在这个时期,它是有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已经存在了,我觉得是它里面比较重要的。
《子弹库帛书·四时令》
战国中晚期
所以现在我们讲日书的传统,从《左传》里面虽然能够看到一些端倪,但是真正比较开始形成系统性的东西,可能在战国、秦汉这个阶段,才是它比较体系化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春秋就没有,我想春秋时候已经有一些简单的形式可能已经存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看《左传》里的描述,当时的人的占卜系统还是以龟卜筮占为主的,但是到了战国、秦汉以后,龟卜筮占就衰落了,很明显地是被选择术所取而代之。
第一次接触是我当学生的时候,就是我在考古所,应该1979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想解决认楚文字的问题,可是当时楚文字材料,青铜器上当然有,当时也有一些竹简,但是当时的竹简比现在少得多。这样我就想帛书是其中字数比较多,比较大的材料,特别是1949年以后,绝对就是《子弹库帛书》这一件东西。所以我就想从这个地方入手来学楚文字,无形之中后来带动了我的很多研究方向。
1980年就写这本书,这是当时学习楚文字的副产品,因为这不是我研究生的题目要做的。当时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像现在,也没有什么课题制,也没有各种考核,这纯粹是自己想去做。可是后来就造成了一种机缘,就是我1989,1990年在美国的时候,我跟张光直先生通信说想去拜访他,他特别热情给我回信,说1990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关于楚文化的讨论会,在这次会上会展出楚帛书。因为楚帛书实际上到美国以后从来没有露面过,1990年是第一次在华盛顿露面,这个会开是为了辛格医生开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博物馆工作,有人开玩笑说博物馆的工作,这些curator(策展人)的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给老太太打电话和请她吃饭。因为什么呢?一般的老太太都比老头子要活得长。更何况如果你娶一个特别年轻的太太,那一定就是老太太在,先生已经死了。然后他这个文物,你得给老太太做工作,才能把这个文物给抠出来。
赛克勒医生当然是赛克勒博物馆的一个大金主了,另外就是他的好朋友辛格医生。他们也知道辛格医生的年事已高,所以准备给他搞一个活动,其实目的是把辛格医生的东西都捐给赛克勒博物馆。
辛格医生
那次会议确实应该说是张先生的一个机缘,因为好多美国考古艺术史界的,我也不不怎么认识。那一次很多人都去了,比如像Bagley(贝格立),还有在博物馆工作的苏芳淑教授,他们当然都在场。然后在会上李学勤先生发言的时候,正好有人就向他提问,就是问楚帛书的图像一些含义是什么?李先生当然是一个特别客气的人,他在会上他就说这个问题,我们在场有这方面的专家,饶宗颐教授和李零教授,所以他们就让我发言,饶先生他是前辈,让他发言去了。后来博物馆编辑论文集的时候,要求我做一个书面的发言,后来就印在他们的论文集里。
我对张(光直)先生印象特别好,特别的谦和。现代人都很难理解那时候的气氛了,他一直是有一种抱愧的感觉,觉得他生活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就说他没能为中国做什么事。他就跟我说,你是不是能办一个能够经常往返于美国的签证能够来,其实他也不太知道,我并不是那么热衷要上美国去的,所以后来才见到他。
但这就是机缘,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1992年,John Cox(柯强)把他的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子弹库的残片匿名捐献。因为大的帛书是已经落入赛克勒医生的手里,借存在赛克勒美术馆。然后他又捐献了其他的子弹库的文物给了赛克勒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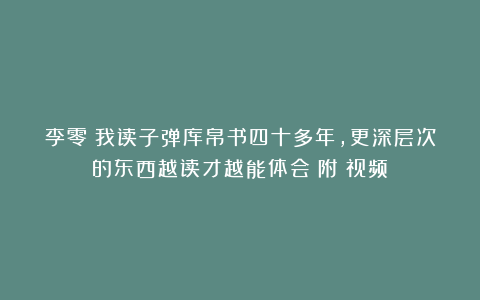
柯强
John Hadley Cox
当时他们交接仪式还很隆重,因为当时苏芳淑教授提议说,我们可以明年请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到美国来研究这个。他们说这个是不是很敏感,当时因为有所有权问题,那个谁说不让人家知道,就是变成一个秘密。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决定了,就是说在1993年请我去研究帛书,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外间的人都不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内关于这个帛书是怎么到美国的,在美国什么地方全都不知道,这里头年月日时、人物、有关的事件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去了,当然我就比较要投入这个研究。
其实当时我住得也很远,我记得苏芳淑教授他们在美国长期生活惯了,也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我说我住哪儿?他“啪”就给我寄了一堆,估计都是旅游部门提供的,华盛顿的豪华酒店什么的。我说我哪住得起?我说你给我提供那些我都住不了。最后找了一个地,就在Maryland(马里兰)。我差不多就有点像现在在北大,每天进城都很远,我得每天坐地铁去DC的赛克勒美术馆,所以路上也非常辛苦。他们有食堂饭,但我吃不太惯,我都每天带着饭到那儿去,我在那儿还是很用功的,就是天天搜集各种各样的材料。
其实最初,你可以看到像李学勤先生写《战国题铭概述》的时候,他并没有见过楚帛书,他是从日本的《书道全集》上面的一些材料,当时像林巳奈夫也写过这个东西。中国学者都是通过很间接的材料来看。
第一次看到这个照片,就是商承祚先生他搞到了一套弗利尔的照片。其实帛书一到美国,各个博物馆反复地研究,拍摄照片,所以有好几套照片,我都放在这书里面了。这套照片是稍微晚一点的,像这前面的照片就是比较早的。你看最晚的照片主要的就是有这一大块白。
李零在弗利尔美术实验室
这一大块白是怎么回事呢?John Cox把这些卖给大都会博物馆以后,他们有一位负责保管女士,辛格医生就说是一个“蠢女人”,因为这位女士,缺乏文物保护的知识,认为他们买了John Cox的那批漆器以后,她认为要保护这些漆器。然后帛书和漆器,反正就是John Cox的藏品都在这了,她要保护这些漆器,就要有湿度,她就拼命地在这放湿气,帛书就发霉了。发霉以后,又去请专家,专家就是说想办法把霉给去掉,结果一去,这块脱色,就是说它底色本来是咖啡色的,要比这个还深,所以字不是特别清楚。把霉去掉,就等于把它底色去掉了,原来它可能也是有一种类似于染黄工艺之类的,它上面是可能有一种东西给它去掉了,所以露出来的那个字是比那个原来要更加清晰。
当我们1990年看楚帛书的时候,那时候饶宗颐先生还拉着我说,咱们去看看帛书,我们俩就一块到那看帛书。然后饶先生,他就是关心那个字,能够多认得一点,既然这么看得更清楚了,是不是别的地方也不是给它弄发霉,给它弄喷点湿气让它发霉,然后再给它去掉。他还开玩笑说这叫“霉开二度”。
蔡季襄《晚周缯书释文》
最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书,它是叫《晚周缯书考证》,所以一开始叫缯书,反正中国丝绸的名字有好多,丝、帛、缯等等,后来我们一般都叫它帛书了,但是一般过去大家只说楚帛书,没有这个地点。我记得我调到北京大学来的时候,朱德熙校长就跟我说,说你这个书名也太长了,《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他说太长了,就叫《子弹库帛书研究》多好。所以后来我这个就变成《子弹库帛书》了,这是我因为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命名的习惯是这样,以出土地点来命名。但是过去命名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楚帛书只是经过蔡季襄装裱的那一件,它叫《子弹库帛书》。
后来,我去美国才调查,我才发现它有第二、第三帛书,包括李学勤先生原来写过第二帛书,研究那些,因为都不知道。而且他当时还看了巴纳的书以后,其实巴纳的书里面画了一个图,就是楚帛书的折叠示意图。结果李先生就根据插图,就开始写里头的释文。其实插图是巴纳自己画的,他根据长台关的一个模拟的。后来我因为在美国整理这个,我回来就告诉李先生,我说那个不是真的,那是巴纳他画的一个图。
子弹库竹笈(巴纳重绘)
后来我还跟裘(锡圭)先生说,然后裘先生说你应该告诉李先生,我就跟李先生说去了。李先生一开始很生气,说他怎么能这样骗我呢,后来他就把那个删掉了,他也说了是李零先生告诉我说是(巴纳画的),这个就作废了。所以可想而知,那时候大家对楚帛书很多事情都云里雾里的,真是搞不清楚。
当时我只是为了尽可能地知道各种各样的情况,也真的非常感谢这几位美国学者。比如Paul Jett先生。我翻他们档案的时候,就突然翻到了John Cox跟他们签订协约和登记手续。我看见以后,非常振奋,我就跟Paul Jett说,我说这个是不是你们的秘密?他说不是什么秘密,你去复印,很慷慨。所以很多材料也是到美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后来做调查越搞越细,有一些甚至是有很多后续的工作应该特别感谢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夏德安教授还跟我一起到长沙去调查,美国、中国都调查,而且他还写了很多信,帮助了解楚帛书进入美国以后的前后流转过程。所以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从进入美国海关以后,在各个博物馆里面之间的旅行过程,完全搞清楚了。
现在写考古学史,往往大家都认为考古学出现前面是一个比较混乱和比较糟糕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同样称为古物学或金石学。其实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往往是以这段比较混乱的历史作为前提的,往往是以它为先导的,这在中外都一样。
所以考古学史为什么要写古物学史,因为不可能不写。我们今天说的一些重大发现,应该说都是一些再发现。考古发现本身就是再发现,它本身是一个人把它埋下去,然后你又给挖出来了,这个它本身都是人把它造出来,然后又把它埋下去,然后你又把它挖出来。所以一开始都是被偶然地发现,或者是盗掘这样东西,才把它发现。因为你往往主动去找,往往不一定能找到,就很多偶然性。所以1949年以前的这些发现,就成为1949年以后很重要的线索。
而长沙的重要性是什么呢?1949年以前的盗墓有很多很有名的,像金村、浑源、寿县、新郑等等,这些每一个都应该作为考古学史来去研究。但南方大家就知道一个,就是长沙,基本上长沙盗墓就成了南方盗墓最集中的地方。
像湖北就不是,这是解放后才引起注意的,以前就是长沙。所以我记得我在美国去辛格医生家的时候,我看见他家里面有一个大铙。我说你这还有一个这样的大铙,长沙不是出了很多大铙吗,他就拿手这么敲大铙,“当”一敲,他说,它发出的声音是长沙货,这就跟中国悲惨的历史有关系。
那时候耶鲁大学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就选定长沙作为他们长江流域的传教点,所以在长沙建了湘雅医院,建立了雅礼中学。所以在美国的很多东西,从上海出去的,就很多都是长沙出土的。大家如果追溯起来,长沙出土那些东西,有一些今天看来是很有名的。比如说克利夫兰出的双蛇漆器,那个就是蔡季襄从上海给弄出去的双蛇双鹤漆器。有很多珍贵文物都是从长沙出土的。这些洋庄货,今天看起来那些都很普通,但是这里头真正出彩的,就是《子弹库帛书》和和陈家大山帛画,帛书、帛画还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
双蛇双鹤漆器
蔡季襄在以前他是搞古董贸易,就是到了1949年的时候,真正在上海出口那地方,有四家重要的古董店。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人他们有的知道共产党会不让他们再做旧的生意,他们就跑到海外去了。戴润斋(戴福保),还有金财记的老板金从怡都跑到国外去了,然后四大古董店都被取缔了。所以蔡季襄他也是一个旧人员,也要不断地向组织交代,他过去把什么东西弄出国外了。但是问题是在1949年那个时候,人心都还比较浮动的时候,那些已经出去的古董商跟蔡季襄说,你赶快给我们弄一批文物出来,而且最好你也出来跟我们一起在外国干。他就带着文物跑到广东去,准备跟他们接洽,然后在广东就被抓起来了,属于盗卖文物出境,这是很严重的。
没想到当时正在筹备成立湖南省博物馆,当时中南地区负责的中共首长王守道批示,说这个人对于新中国还是有用的,就把他放出来了。所以他感恩戴德,就把他的陈家大山帛画献给政府了,他手里的一些文物就都捐出来,而且也交代他都把什么样的文物都弄到国外去了,四个土夫子,原来都是盗墓的,都变成新社会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考古所的工作人员。
你们去湖南省博物馆看关于马王堆发掘的展览,那个照片上身先士卒在前面提文物的就是当时的那些盗墓贼,而且这几个人既参加了子弹库,也自始至终地参加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所以这是新中国对于旧社会的人员的改造利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子弹库帛书出境是,蔡季襄在战后,他回到湖南以后,从湖南的湘西,就到上海去准备兜售这些文物。他买卖主要是跟金财记,一个姓金的回族人。他的古董店是他主要的买卖合作人,店里的一个伙计叫傅佩鹤,傅佩鹤带着柯强到他这里,因为他(蔡季襄)正好写了《晚周缯书考证》,在上海能看到这样的书。
1930年代湖南盗墓场景
柯强其实他是在抗日战争湖南会战这些之前,就已经离开长沙了,他回美国去了。他是作为一个情报人员,又被派回中国。他听说有这个书,这个书各方面都看挺好,可惜都是没有照片,都是蔡季襄叫他儿子画的这些图。他说你这个东西最好是要照片,你借给我,我给你拍照片儿,他就借去了。借去以后,他就托我在书中写的舒尔泰斯这个人,直接就带到美国去了。然后蔡季襄问那照片拍的怎么样了,他说对不起,昨天我一看我的相机零件坏了,而且在国内也配不了,所以我就没经过你允许,已经托一个人带到美国,反正还是给你照相,拍比较好的照片。他听了大怒,傅佩鹤就说,你这惹不起,这是美国人,你可惹不起,就说算了,也不如顺水推舟,你不就是要卖吗,你就托他到美国去卖就行了。然后这个东西,就被舒尔泰斯带到美国,他的好朋友就是史克曼就带到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所以我们也到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去,夏德安教授也去看他们的档案。
其实他就是来回来去地就是在福格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和这几个博物馆之间转来转去,都是在研究怎么拍照,和怎么去找买家卖掉它的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他很长时间是卖不掉的,就是等于他们也在联手压价钱,就说,你这东西,破破烂烂的一个东西,一个画儿。而且他们一直疑惑的一个事儿,这东西到底是谁的,柯强是知道的,但是因为蔡季襄为了诈唬美国人,他怕他们觉得他没有可靠的金融能够系统给他汇钱。所以他说,我这个是跟银行大老板,还有傅佩鹤,我们三个人的东西,然后人家美国人就说这到底是谁的?因为他们是很严格的,他一定要把这个所有权讲清,所以他们也有一些疑惑,所以长期那个东西就没卖出去。
柯强在早期,他一直还是说他是在替别人卖这个东西。他在大都会博物馆把他的文物都交给大都会博物馆,说这是两个东西,这些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朋友的。咱们如实地讲还是这样的。但是等到人家不买,人家说到期了,按照合同到期了,你该把这东西提走了,他也没地儿存放,这时候他突然得病了,而且估计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辛格医生给我一个文件,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就把原原委委都讲了,说他那会儿脑袋出问题了,我是医生,他找我来问,他急需钱要治病,所以把他那些东西都给卖了。这样就使得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虽然是入藏赛克勒医生的东西了,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好像在在他来说,他已经就背叛了他的这个朋友了。
赛克勒医生和辛格医生是好朋友,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赛克勒医生是美国出生的,而辛格医生是德国出生的,他们是好朋友,都喜欢中国文物。但是赛克勒医生医生更钱大气粗腰杆壮,他是雇很多dealer给他买文物,而辛格医生是自己单枪匹马,自己到古董店去淘东西,因为赛克勒医生他自己不出面,所以他也不知道戴润斋在干什么。因为柯强卖的这个文物先是在戴润斋的手里,如果他自己根本不看的话,早就被戴润斋给蒙过去了。
辛格医生他自己收藏文物,而且他真是寝馈其中。我去辛格医生的家的时候觉得特别奇怪,远远的还没到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象,我想象辛格医生的收藏一定是一个博物馆,很大。后来到那儿看见一个楼,我就说这个楼一定就是他的博物馆了,不是,他们说这里头只有一套房子是他的。然后进了一套房子里就发觉,实际上他这个房子里完全就是被各种文物堆的,和字画什么的,只有狭长身体可以穿过去。而且所有的小抽屉一拉开,“哗”全都是带钩,“哗”一拉出全是玉器。而且他是单身,就一个人,就生活在这堆文物里,这都是他天天去淘文物淘回来的。所以有一天,他走到戴润斋的店的时候,他在看他这些文物的时候,他就听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机器的声音“轰轰轰”不停地响。他因为太熟了,所以他“啪”推门就进去了,一看就看见楚帛书就放在桌子上。后来他就一看,他反正也还是有点眼力的,他说这东西很珍贵的,说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回事,他知道他是给赛克勒买东西的,说这件东西你怎么给眯了,成了你自己要收藏起来了。戴润斋说我这都是我收藏起来的字画。他说你这很不道德,你干这行的,你不能这么干。
戴润斋就说反正你是买不起,我忘了多少,30万还是多少,就是你没有30万,你甭想把这东西拿下,反正你是买不起的。他就很生气,就出来到公共电话亭投个币,打了一个电话给赛克勒医生,说你赶紧打一个出租车到这儿来,我跟你说,你把你所有的藏品全都扔到哈德逊河里,也抵不上你买下这一件东西,这样他才把这件文物给买到手的。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现在的所有权就属于赛克勒基金会,但是赛克勒医生对这个帛书做过调查,他去调查了舒尔泰斯,他讲了帛书到美国这个过程,这个材料其实很难得。因为这是赛克勒医生他们内部的一个小文件,因为他送给罗泰教授,罗泰教授就给我了。这里头就很清楚,他是做过调查,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来的。
所以他一方面是捐钱让哥伦比亚大学开会研究它,出过几本书,一方面他就在考虑要把这个东西送回中国,他希望在中国要有一点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他有一个安排,他想在中国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出版他的医学杂志,要到科学院,最高领导就是郭沫若院长,所以他想见郭沫若院长来商量办这个杂志。他要制造一个噱头,就是把楚帛书作为跟郭沫若院长的见面礼,把它送回中国。但是跟中国联系的时候,正好郭沫若先生已经病入膏肓,不可能见他,所以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把楚帛书送回中国。然后他就想第二次要制造一个惊喜,给中国制造一个惊喜,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赛克勒博物馆落成的时候,他准备在这个揭幕的时候送给我们北京大学。可是这个房子盖得太晚了,当这个房子盖好的时候,赛克勒已经不在了。
英文版的第一卷是罗泰教授翻译的。在杭州我过生日那个会上,他还讲过,他认为这个故事本身就很重要。因为第一卷主要是楚帛书的传奇,Smithsonian(史密森尼学会)的这些负责人看了这个书后,都说这不是《夺宝奇兵》吗?
第二卷是夏德安教授翻译的,他现在半退休了,他后来跟很多学生都是说他这辈子最后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帮助李零把这本书做出来,而且把这些东西从美国送回中国。所以他是最热心这件事的,而且上次在青岛开会的时候,他特意把一个重要的见证物,就是楚帛书到美国的时候,那个大的帛书,以前蔡季襄已经把它裱好了,把它放在一个铁桶里头,其他碎片其实都是装在一个鞋盒子里,这个鞋盒子的盒盖,就是它每次从哪个博物馆到另一个博物馆都要进行交接仪式,所有的这些都写在这个盒盖子上,所以这个盒盖子就成为它在美国旅行的签证,就是每一个地方签到的地方都在这个盒子上。字迹很潦草,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字迹都都辨认出来。
盒盖上的文字
夏先生就把这件东西拿到中国来,先把它捐献给我们的国家文物局。因为这个盒子见证了这个楚帛书在美国旅行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希望楚帛书一号帛书能够由赛克勒基金会,按照他父亲的遗愿把它捐献给中国,不管他是回到哪里,当然他原来的遗愿就是要送到北京大学的。其他的帛书碎片,因为柯强匿名捐献的,其实他匿名捐献就说明他来路是不正当的,所以我们国家文物局希望按照现在国际上的对于不道德的文物流失应该进行追索,让它回到中国。这虽然是两件事儿,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有一天子弹库的所有文物能够在中国重新聚首,但实现起来很不容易,赛克勒美术馆过去也觉得是有很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曾经参加的那个帛书的揭剥工作,就在我走后不久就停下来了,直到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开会的时候,由罗泰教授和Martin Kern(柯马丁)教授发起。在那次会议参会的27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联名致信赛克勒美术馆,要求他重新开启这个帛书的揭剥工作,而且希望他们能够跟中国合作研究,所以也非常感谢二十多位国际学者对中国文物事业的支持。
子弹库竹笈
我其实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推动研究,特别是在普利斯顿的时候,我一再强调说这对于全世界的学术界来说,我们的共同利益是超出所有权问题的。当然我希望他回到中国,但实际上这个楚帛书是属于全世界的国际学术界,即使是楚帛书归还到中国来了,仍然可以成为中美、中国和西方学术界继续共同研究的一个课题。特别是这些残片里面,这个残片我们把它揭剥的时候,就像我们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它揭剥下来。但最后里面这个核还没有解开。所以其实如果回来,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
当然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是不是需要把它揭开?过去我们就讨论过,我们在华盛顿揭剥的时候,也非常有意思。我们中国的专家白荣金,我带着白荣金先生去,他是文物保护专家,他是用一个竹刀来揭剥,结果西方都是拿着手术刀在那揭剥。当时我就说,这些东西应该揭剥,但是那些文物保护专家说,你把它打开,它不就死了吗?你是给它动手术,但是动完手术了它死在手术台上了。后来我们当时还有争论,我说这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我说你应该想到这个帛书他的重要价值,不是这么一团丝绸,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里面的字,你看不见那字它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考古不是也都是这样的问题吗?任何考古都是破坏,问题就是在于你要考虑到你的这个工保护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继续放那,它继续碳化,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最后就一堆渣儿。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它揭剥开,我们怎么知道还有个《五行令》呢?所以我们的工作虽然没有做完,但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