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乐也。熙宁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
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于宇下。中央为沼,方深各三尺。疏水为五派注沼中,状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此,偕悬注庭下,状若象鼻。自是分为二渠,浇庭四隅,会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轩。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周三丈,状若玉玦,缆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沼北横屋
六楹,厚其墉茨,以御【禦】烈日。开【開】户东,出南北,置轩牖,以延凉飔。前后多植美竹,为清暑之所,命之曰种竹斋。沼东治地,为百有二十畦,杂莳草药,辨其名物而结之。畦北植竹,方径丈,状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爰,命之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欄】,芍药、牡丹杂花,各居其二。
种止植两本,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阑北为亭,命之曰浇花亭。洛城距山不远,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见。乃于园中筑台构屋其上,以望万安轘辕、至于太室,命之曰见山台。迂叟乎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羣】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赜。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勤体疲,则投
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徜徉,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足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迂叟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
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柜中,一卷纵 27 厘米、横逾六米的行书长卷静静铺展,墨色温润如玉,线条舒展从容。这便是文徵明八十九岁时所书的《独乐园记》,纸本之上,三千余字一气呵成,全无老态,反而透着洗尽铅华的平和力量,成为明代行书艺术的巅峰之作。
创作这幅长卷时,文徵明已近人生终点。这位横跨明成化至嘉靖五朝的艺术巨匠,出身江南文人世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 “吴门四家”,在诗文书画领域皆成宗师。他曾怀揣仕途抱负,却因宦官乱政、权臣当道的时代漩涡,年过半百才得授翰林院待诏,不久便辞官归乡。晚年的他深居江南,以茶会友、以书画自娱,在动荡时局中寻得一方精神净土,而《独乐园记》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绝佳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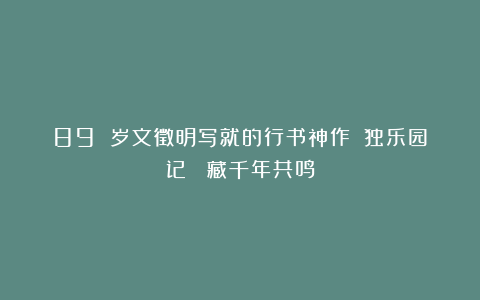
长卷所书的原文,出自北宋司马光的名篇。熙宁年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离京,在洛阳尊贤坊以北购地二十亩,构筑了一座朴素的园林。园中有藏书五千卷的读书堂,有 “状若虎爪”“形如象鼻” 的引水轩榭,有竹环绕的钓鱼庵,还有植满草药的圃地与可远眺群山的见山台。这位自号 “迂叟” 的学者,在此读书治学、耕园劳作,将 “各尽其分而安之” 的处世哲学融入园林,命名为 “独乐园”—— 这并非孤僻自守,而是在功名利禄之外,坚守本心的精神栖居。
文徵明书写此文,实则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他以新笔作书,彻底褪去了早年书法中的锋芒圭角,每一笔都秀妩温润,如春风拂柳却暗含筋骨。笔法上兼具王羲之的灵动与苏东坡的厚重,转折处圆融自然,收笔时含蓄蕴藉,恰如他晚年 “景与神会,象与心融” 的艺术境界。文中 “明月时至,清风自来” 的字句,与他常于庭中步月烹茶、与友品茗论道的生活相映,那些平和的笔墨里,藏着他对司马光 “独乐” 精神的深刻共鸣。
这幅长卷的价值,更在于它见证了一位大师的生命韧性。史载文徵明九十岁时仍伏案作书,最终悠然离世,而《独乐园记》正是他晚年精力不减的实证。卷末虽未题跋,却因笔墨中那份 “踽踽焉,洋洋焉” 的从容,成为后世解读其心境的密钥。后来他还为独乐园创作了《独乐园七咏》组诗,与书法长卷相得益彰,将园林中的读书、钓鱼、浇花等日常,化为文人安身立命的精神符号。
如今凝视这卷墨迹,既能读懂司马光造园时的坚守,更能看见文徵明晚年的通透。那些温润的线条里,藏着两位文人跨越千年的默契 —— 在世事纷扰中,守住一方天地,以读书、耕园、书画为乐,这份 “独乐”,早已超越时代,成为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最动人的底色。
附:文徵明《独乐园七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