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金燕,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374028);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培优项目(YLXKPY-ZYSB202211)。
摘要
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正日益受到重视,但有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本研究通过收集中国六个省市初高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及相关因素数据,并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技术对50多个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和识别。一个重要发现是:与人连接的“关系类”因素——父母的教养风格、学校的师生交流、同伴关系以及校园欺凌等,是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而在传统上被认为重要的“资源类”因素——学校资源、课外班学习以及父母养育时间的投入等,却与非认知能力的关联较弱。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仅预测了一小部分非认知能力。这表示不同于过去主要以学业成绩为产出、注重资源投入的方案,以非认知能力为产出的教育投资研究应转向对父母教养态度及策略、教师支持和沟通、同伴支持等与人连接因素的关注。本研究的发现也为教育投资突破家庭禀赋和学校资源约束,促进平等甚至阻断贫穷的传递提供了可作用的路径。
一、引 言
过去十多年,非认知能力的投资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诸多证据表明,非认知能力不仅与个人的学业成绩、未来工作和收入有紧密关系[1][2],同时与其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行为、生活满意度和寿命等有更为密切的关系[3][4]。尤其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随着人工智能取代大量具有程序性特征的工作岗位,非认知能力的需求和报酬还出现上升趋势。[5][6]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一致认同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并认为它是公共资源投入的明智选择。[7]然而,当今中国教育仍然过于偏重认知或考试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学生的心理、情感和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近年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文件,提出“五育”并举、“双减”等措施,致力于改变我国专重学业成绩的学校教育特征,并转向强调学生的社会情感、心理健康等非认知方面的发展。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培养学生的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教育生产研究主要以认知或学业成绩为产出,对非认知能力的探讨却十分有限。因此,在众多的潜在影响因素中,人们不清楚哪些因素对于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是重要的,这制约了对提升学生非认知能力有效措施的探索。
本研究将回应上述问题,用投入—产出框架和贝叶斯模型平均技术(Bayesian
Model Average,简称BMA)探索和识别中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要素。为此,本研究专门开展了一项针对中学生非认知能力的调查,这项调查覆盖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六个省市的5 000余名初高中学生。这项调查收集了学生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父母教养、日常学习生活等可能对其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信息。这些丰富的数据信息使得本研究能使用BMA技术识别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对50多个潜在影响因素的BMA估计,本研究发现与人连接的“关系类”因素——包括父母的教养方式、师生交流、同伴关系和校园欺凌等,是中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而传统的“资源类”因素对中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较弱,家庭经济和社会背景也仅预测了一小部分学生非认知能力。
下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整理了非认知能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介绍非认知能力的数据、测量办法以及BMA估计思想、模型以及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第四部分报告和总结BMA的估计结果,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第六部分是总结和启示。
二、文献回顾
非认知能力是相对于认知能力提出的,用以指代那些不易被学业成绩测量或与智商无关或弱相关的个人特质。[8]与之相似的概念还有社会情感技能、人格特质、心理能力和软技能等。非认知能力的概念及产生背景决定了该领域文献的两大特征:一是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尽管以认知能力或学业成绩为产出的教育生产研究已非常丰富,但对是否应投资非认知能力教育投资的研究还十分有限。二是尽管对经济学家来说,非认知能力投资研究刚开始,但心理学对人格特质、心理技能、社会情感技能等相似概念的影响因素已有长期探索。因此,本研究的文献回顾并不仅局限于教育投资和生产领域,还综合了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的文献。通过文献综述,总结如下发现:
首先,家庭背景向来是解释学生发展及其未来成就差异的重要指标。诸多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贫困、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的学生通常有更差的认知或学业成绩表现[9],并有更多的社会情感和行为问题[10][11]。此外,单亲家庭[12]、兄弟姐妹数量[13]、出生顺序[14]等家庭结构也和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有关。
家庭教养方式通常包括父母在时间和物质资源上的投入、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如协助做作业、讨论学校活动、学习沟通、一起看书、去博物馆等)以及父母的教养风格(parenting
style,即父母在养育子女时的策略等。但已有教育生产研究多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15][16],仅少量关注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非认知表现的影响[17]。心理学领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如父母采取权威型、情感温暖型等积极教养风格对子女在情感、心理上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专制型、放任型、拒绝型、过度保护型等教养风格则多有负面影响。[18][19]此外,有关课外班学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的研究较多[20],但关注课外班学习与非认知能力的关系[21]的研究较少。关于看电视、上网、做家庭作业、睡眠时间等的研究,也多探讨其对学生成绩的影响。[22-24]
其次,在学校教育生产领域,研究者多以学业成绩为产出探讨学校资源的投入和配置[25][26]。仅有限的证据发现,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与学校同伴[27]、师生关系[28]、班额[29][30]等相关。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的校际差异很小(多低于5%),明显低于学业成绩的校间差异(多接近50%)[31-33]。有研究还发现,学校投入因素虽然能解释学生学业成绩,但对学生对学校的态度、学生参与、逃学和出勤率、酗酒和吸毒等的解释力有限。[34]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等数据库检验了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相关因素。[35]OECD与中国合作在苏州开展了一项针对10岁和15岁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调查,并对测评结果做了报告。部分研究还在该数据基础上,用OLS回归检验了与学生社会情感发展相关的因素,如年龄、性别、城乡、家庭和学校因素等。[36]
总的来说,针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教育生产研究才刚开始,已有证据主要来自OLS估计结果。由于OLS估计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37] 本研究将用BMA技术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技术可以处理模型选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帮助研究者从多个潜在变量中找出关键变量。BMA方法过去多用来识别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38][39],现在愈来愈多地被应用于其它社会科学主题的研究。非认知能力是一个新兴领域,用BMA技术探索其关键影响因素,不仅可以为决策和干预提供参考依据,也可以为未来研究者开展有针对性的因果检验提供方向和基础。
三、数据、测量和模型
(一)数据收集
针对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笔者于2017年开展了一项专门调查(student noncognitive skills survey, 简称SNSS)。样本覆盖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六省市的初高中学生。抽样设计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第一阶段抽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各3个省市,并在每省选取一个城市;第二阶段分城区、县城和农村抽样,即初中校选取城区优质名校和一般校各1所、县城一般校1所、乡(镇)一般校1所,高中校选取城区和县城优质名校及一般校各1所。第三阶段在每所学校内部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每校抽取初二年级、高二年级2~3个班,每校约110人。样本较好地覆盖了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和学校背景的学生。但高中阶段仅抽取了普通高中,不包含职业高中和未能上高中的青少年,因此高中阶段青少年数据的代表性具有一定局限性。
具体调查过程如下:首先通过中国儿童中心派驻各地区并熟悉当地教育的工作人员和调查校建立联系,并征得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同意。然后,向每所学校派遣经过统一培训的32名“985”高校研究生(每校2名),由学校抽取两节课的时间组织现场测试。测试手段采用线下纸质问卷和答题卡填答的方式。为了保障学生的填答真实性,避免作假和社会期望偏差等问题,在测试时特别强调了测试数据结果的非考核目的。此外,本调查由中国儿童中心而非具有考核权的教育行政部门出面联系,这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学校虚报的动机,保障了数据的真实性。SMSS调查一共回收5 389份初高中学生问卷,经核验并用甄别题处理填答不认真的问卷后(例如,在对孤僻性的测量中,同时包含了两道截然相反的题目:“Q1.我不喜欢和同学一起学习”和“Q2.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学习”。本研究删除填答结果完全不一致的样本),最终得到初中生有效问卷2501份,高中生有效问卷为2519份,合计5021份。
(二)非认知能力的测量
非认知能力常被用以描述那些不能被智力测验或学业成绩测量的个人特征,或与智商无关或弱相关的人格特质。参考夸兹(T. Kautz)等的研究,非认知能力是指凝结在个人身上并能在未来获益的人格特质、品格和偏好等。[40]有研究者将非认知能力分为“做事类”“人际类”和“情绪类”等三个维度,分别用以描述个人处理学业或事业、处理人际以及处理情绪或情感的能力。[41]以此为框架,并参考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团队等对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框架的研究及其论述[42],本研究选取如下非认知能力指标及其测量工具。
一是学生处理学业或事业的非认知能力,采用达科沃斯(A. L. Duckworth)和奎因(P. D. Quinn)[43]开发的坚韧性量表(Grit-S)测量。坚韧性指个人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热情,它是一种个人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持之以恒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信念的品质。[44]研究表明,坚韧性对学习经历和学业表现产生重要影响[45],同时也能预测体育锻炼行为[46]以及未来生活的幸福和满意度[47]。坚韧性短表是一个5点自评量表,包含兴趣的持续(interest)和努力的维持(effort)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4个题目,如“Q1.我曾经着迷于某个想法或事情,但只是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就失去兴趣了”和“Q2.挫折不会让我气馁”。该量表被广泛应用,在谷歌学术上被引3 000多次。本研究用SNSS分半数据对坚韧性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发现估计的信度和结构效度系数都在理想范围内,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FI[Comparative Fit Index]指比较拟合指数;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指近似误差均方根;SRMR[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指标准化残差均方根;NNFI/TLI[Nonnormed
Fit Index]指非规范拟合指数。Cronbach α=0.71,CFI=0.97,NNFI=0.96,RMSEA=0.05,SRMR=0.03。)
二是学生与人合作的能力,采用乔纳森(D. W. Johnson)等开发的学生社会互依量表(Social Interdependence Scales)进行测量,包括合作性(cooperativeness)和孤僻性(individualism)[48]。合作性指学生想与他人一起学习、相互帮助和促进的心理愿望。孤僻性指个体只专注于完成自己的目标而不愿与他人产生交互影响的特点。研究表明,合作能帮助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并建立更团结、信任的工作环境,因此,人类间的合作对于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49]乔纳森等对122个研究286个结果的元分析发现,合作性比孤僻性更利于产出,是一种更积极的社会技能。[50]合作性量表和孤僻性量表都为4点自评量表,各包括7个题目。合作性量表题目如“Q2.我喜欢和同学分享我的想法和学习材料”。用SNSS分半数据估计其信度系数和结构效度指数都在理想范围内,说明合作性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0.91,CFI=0.94,NNFI=0.92,RMSEA=0.13,SRMR=0.04)。孤僻性量表题目如“Q6.我宁愿独自完成学校作业,也不愿和其他同学一起完成”。用SNSS分半数据估计其信效度系数,发现孤僻性量表信效度良好(Cronbach α=0.88,CFI=0.92,NNFI=0.93,RMSEA=0.11,SRMR=0.06)。
三是学生处理情绪或情感能力的表现,采用罗森博格(M. Rosenberg)的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简称RSE)[51]和拉姆(S. F. Lam)等开发的学生情感投入量表(School Affective Engagement Scale,简称SAES)进行测量[52]。自尊指个体对自己价值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它通常与情绪稳定性人格(emotional
stability)积极相关[53],但与绝望、焦虑等负面情绪呈负相关[54]。研究发现,自尊不仅能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55],也是预测人们的工作收入、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等的显著指标[56][57]。RSE为4点自评量表,一共有10个题项,如“Q2.我认为我有一系列好的品质”。RSE量表及其研究被广泛引用,学术谷歌显示其被引用超过五万次。用SNSS分半数据估计的信度和结构效度系数都在理想范围内,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0.8;CFI=0.94;NNFI=0.92;RMSEA=0.13; SRMR=0.04)。
学校情感投入(school affective engagement)指学生在学校学习和生活中的情感或情绪体验,包括对学习的兴趣、对学校的归属感等。研究表明,积极的学校情感体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并能有效防止学生辍学。[58]SAES量表已在1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使用。它是一个5点自评量表,由9个题目组成,如“Q9.我在这所学校感到很开心”。用SNSS分半数据对其信效度进行估计,发现都表现良好(Cronbach α=0.95;NNFI=0.92,RMSEA=0.09,SRMR=0.05)。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施SNSS调查之前,笔者对上述量表进行了中文翻译、比较、修订以及对110名中学生的试测工作。在试测基础上,比照中文习惯及理解对题目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中文量表用于SNSS正式测试。
(三)影响因素及变量描述
应用人力资本投资框架,本研究将非认知能力的潜在影响因素区分为三类,即家庭禀赋因素、家庭投资因素以及学校投资因素。家庭禀赋因素指学生从父母那里获得的任何潜在资源或特征,并因其“给定的”特征被视为投资约束。后两类指父母在子女健康、教育、生活上的花费和投入的时间以及学校教育的各种投入。[59][60] SNSS调查除了对初高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水平进行测试,还详尽收集了学生的背景信息,为使用BMA技术识别关键因素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具体变量及数据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一是家庭禀赋变量,包括人口特征(性别、民族、独生、地区、本地户籍)、父母婚育特征(婚姻状况、父亲生育年龄、母亲生育年龄)以及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父母月收入、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城乡居住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城乡居住地)。
二是家庭投资变量,包括父母教养投入、父母教养风格和学生的放学后时间安排。其中,父母教养投入包括幼时父母缺位、父母照顾、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等四个方面的指标。父母教养风格包括拒绝型(rejection)、温暖型(emotional warmth)、过度保护型(over protection)三类[61][62]。拒绝型父母采取“拒绝/否认、过度惩罚/严厉”的教养风格,温暖型父母采取“情感上温暖积极并给予理解”的教养风格,过度保护型父母采取“过度保护、干涉”的教养策略。考虑到父母教养投入指标与父母投入资源和时间的关系更密切,因此本研究将其视为“资源类”因素。而父母教养风格则更多表现为父母在养育子女时采取的态度、策略和风格,因而将其视为“关系类”因素。
学生放学后时间的安排包括学生参加课外班(非学科、学科类)、家务劳动的频率以及花在睡眠、做作业、阅读、体育锻炼、和朋友玩、看电视和上网的时间。此外,本研究还将上网行为区分为学习和娱乐,并探索其与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系。
三是学校投资类因素,包括学校的资源、制度以及与人连接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其中,学校声誉、学校所在地(城市、县城和农村)、学校规模、班级规模以及学校资源指数等被视为学校资源类因素。入学考试设置、座位轮换制度、班级随机分配、在校时间、晚自习、社团参加以及上学方式(寄宿/走读)等体现了资源分配的方式,因此也被视为“资源类”因素。师生交流、同伴关系以及校园欺凌体现了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关系,因此被视为“关系类”因素。
(四)BMA方法及模型设计
1. BMA方法
BMA是一种在数据丰富条件下识别关键因素的方法。一般来说,研究者在用计量方法刻画、描述和模拟社会事实时,常因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遇到模型不确定的问题,BMA技术可以帮助确定模型中应包含哪些变量。它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已有观测结果,运用贝叶斯原则来更新先验信念,并计算所有可能模型中基于条件估计的加权平均估计系数。[63] 在多个模型可能适用或存在多种可能因素的情况下,模型本身可能成为干扰因素,影响估计和预测的准确性。而BMA通过应用对候选模型的后验信念,消除了这种干扰,从而产生最佳的预测或参数估计值。
以最简单的多元回归模型为例,假设有k个潜在解释变量x,建立一般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y表示一组因变量,x为一组待选择的回归变量矩阵,β是一组待估计的参数向量。给定自变量的数量k,将可能形成2k个模型,用Mj(j=1,2,3,…,2k)代表。
当对某个未知变量x进行估计时,传统方法是选择一个模型进行拟合,如果拟合效果很好,就用该模型进行估计。然而,可能存在另一个拟合效果同样优秀的模型,而该模型对x的估算结果可能相差很大。那么应该选择哪个模型呢?BMA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它是一种基于贝叶斯思想将模型不确定性纳入考虑的统计方法。
假定真实模型是未知且不可观测的,应由一个模型空间M={M1,M2,…,MK}(由所有可能的模型组成)生成。依照贝叶斯思想,每个模型的权重及其参数的条件估计可以根据数据(D)和先验(priors)确定。因此,给定数据的任何目标系数(βh)的后验分布,可以写成:
其中,βh为待估参数向量,D代表观测到的数据样本, Mj代表模型空间中第j个模型,K表示模型空间中的模型个数。
由式(2)得知,参数向量βh的后验密度分布是模型空间条件下参数βh后验密度分布的加权平均,模型Mj的后验概率P(Mj|D)代表模型j的权重。即给定一个先验分布概率 P(Mj),可以计算每个模型 Mj的后验概率P(Mj|D),如下:
转换成似然函数积分模式,为:
其中,βj表示模型Mj所对应的参数向量, P(βj|Mj)表示模型Mj所对应的参数先验概率分布,P(D|βj,Mj)表示模型Mj所对应的似然函数,P(Mj)表示模型Mj的先验分布。
由式(2)、式(3)、式(4),可计算得到参数向量βj的后验均值(estimated posterior means)与后验方差(associated
posterior variance),如下:
BMA假定未知参数向量βj不再是固定常数,而是与模型Mj一样服从某一特定统计分布,并以后验概率为权重对可能的单项模型进行加权平均,以此作为选择解释变量的客观标准,从而有效处理了建模过程的不确定性问题。一般可通过计算给定变量xk的PIP(posterior
model inclusion probability),即参数与零不同的概率来衡量该变量在模型中的重要性。PIP是所有包括变量xk的后验模型包含概率之和,反映了将特定回归量包含在“真实”模型中的概率,即:
有学者总结了BMA估计的优势:一是可减少模型不确定性被忽略时出现的过度自信;二是在模型不确定下实现最佳预测;三是避免了模型被接受或完全拒绝的经典假设检验;四是相比模型的错误设定,BMA估计相对稳健。[64]然而,BMA也面临计算负担过重、耗时过长的问题。据德卢卡(G. De Luca)和马格努斯(J.R. Magnus)的估计,当有K个变量时,BMA需要估计2k个模型;当K为30时,大概需要150个小时;而K为60时,可能需要1 000年。[65]因此,尽管完整的BMA估计能提供最佳估计能力,但在较多变量条件下,很少能完成完整的BMA计算。为此,拉夫特瑞(A. E. Raftery)等[66]提出了奥卡姆窗口(Occam’s Window)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简称MCMC)方法进行模型选择,以帮助缩小模型范围,专注于那些具有较高后验概率的模型,有效解决模型估计数量过多的问题。
2. BMA模型设计
在用BMA方法探索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时,本研究将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因素变量分为x1和x2两组[67],即:
其中,组x1称为焦点变量(focus regressors),它们是模型中必须包含的变量组。即无论其统计意义如何,都出现在每个回归模型中,因此在模型中起到控制变量的作用。组x2称为辅助变量(auxiliary regressors),它们属于在模型中不太确定因而需要被识别的变量。基于这一思想,应用人力资本投资框架建立禀赋因素模型,以及控制禀赋效应的家庭投资模型和学校投资模型。其中,禀赋因素模型以人口和家庭背景等禀赋因素为辅助变量,用以识别禀赋因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投资模型和学校投资模型分别以家庭投资因素和学校投资因素为辅助变量,加入禀赋因素为焦点变量。当对禀赋效应加以控制时,对家庭和学校投资因素的BMA估计结果,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对其影响效应的探索。
具体到BMA估算时,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分别采用均匀先验(uniform priors)和UIP先验(unit-information g-prior)作为模型先验和参数先验。均匀先验表示在观察到数据之前,所有可能的模型都被认为具有相同概率;UIP是译方纳g先验(Zellner’s
g-prior)的一种特例,其中g参数被设定为样本量n,其优点是为模型参数提供了一个中性先验,使得更多从数据中获取信息,而非依赖于先验选择。研究发现,与其他g先验相比,UIP先验能提供更准确的预测。[68] 此外,在模型选择上,并研究没有采用奥卡姆窗口和MCMC等方法,而是在算力允许的情况下,对所有可能模型进行了完整的BMA估算,并加权平均计算潜在影响因素的后验均值、后验标准差以及后验模型概率 PIP指数。
四、BMA估计结果
本部分将报告BMA的估计结果,并报告所估计变量的后验平均系数(posterior means of coefficient)、后验标准差(associated
posterior S.E.)以及后验模型概率 PIP指数。PIP指数是变量包含在“真实”模型中的概率,用以衡量该变量的重要性。卡斯(R.E.Kass)和拉夫特瑞等还提出了使用PIP值的标准经验法则,并建立以下阈值:<50%表示证据无效果,50%~75%为弱证据效果,75%~95%为有积极效果,95%~99%为强证据效果,>99%为非常强的证据效果。[69]
(一)禀赋模型的BMA估计
表2报告了禀赋类因素的BMA估计结果。其中,禀赋类变量包括人口特征、父母婚育特征及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三个方面,通过估计发现:
第一,性别是预测初中生非认知能力表现的关键因素。初中女生的合作性、学校情感投入水平都稳健高于初中男生,但这一差距到高中阶段失去显著性。东部地区的初中生比中西部地区有更高的孤僻水平,父母离异能稳健预测初中生的低自尊和高中生的高孤僻性,但其他人口特征(包括是否独生子女、民族、是否本地户口、父母生育年龄等)与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不具有稳健关系。
第二,家庭经济因素和中学生的坚韧性、自尊和学校情感投入都表现为稳健关系。家庭经济水平越高,高中生的坚韧性水平和自尊水平也稳健更高。但父亲收入和高中生的坚韧性水平、初中生的学校情感投入的关系却表现为负。此外,房产数量、母亲收入和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未呈现稳健相关。
第三,母亲受教育水平能稳健正向预测初中生的坚韧性、自尊及学校情感投入等;但这一效应到高中阶段却消失了。城市家庭初中生的自尊和学校情感投入水平都稳健高于农村家庭学生;但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是否来自城市地区,未呈现与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的相关性。此外,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和初高中学生的合作性、孤僻性表现有关。
(二)家庭投资模型的BMA估计
表3报告了控制禀赋效应后家庭投资因素的BMA估计结果。家庭投资因素包括父母投入、父母教养风格和学生放学后的时间分配。模型中加入禀赋因素为焦点变量,用以控制禀赋效应。通过估计发现:
第一,父母教养风格是影响中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父母的温暖型教养风格对初高中学生的坚韧性、合作性、孤僻性、自尊以及学校情感投入都产生稳健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亲温暖型教养的影响比母亲温暖型教养的影响更大。与之相反,父母的拒绝型教养和过度保护型教养表现为对中学生非认知能力的负向作用,包括初中生的自尊、高中生的坚韧性、自尊和学校情感投入等。但父母参与指标,包括幼时父母是否缺位、是否主要由父母照顾,以及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等,却并没有表现出和初高中生非认知能力的稳健关系。这说明父母采取“情感上温暖积极并给予理解”的温暖型教养风格,有助于提升中学生非认知能力水平;但如果父母采取“拒绝/否认、过度惩罚/严厉”“过度保护、干涉”等拒绝或过度保护的教养策略则不利于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
第二,针对学生放学后的学习和生活因素,BMA估计发现,家务劳动、体育锻炼以及和朋友玩的时间等是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更多参与家务劳动、体育锻炼的中学生拥有更高水平的坚韧性、自尊以及学校情感投入;而放学后更多和朋友玩的高中生,其孤僻性也相对更低,并拥有更高的自尊水平。此外,虽然上网时间显著负向预测中学生的坚韧性、合作性、学校情感投入水平,但如果学生上网是用于学习而非娱乐,则对其坚韧性、自尊以及学校情感投入有积极稳健的预测效应。研究并未发现和学习相关的时间投入——包括做家庭作业的时间、阅读时间、上学科类辅导班和中学生的非认知表现具有稳健关系。
上述发现和已有文献一致。已有研究多用OLS估计的结果发现,母亲的养育时间投入、父母参与和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较弱甚至有不一致的表现。[70][71]一项对澳大利亚儿童日记数据的分析也发现,父母与子女一起学习的时间对儿童的认知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儿童的非认知发展对父母时间投入却并不敏感,而是受到母亲教养方式的强烈影响。[72]其它大量研究也一致发现,父母教养风格对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一致且影响更大[73-75]。课外补习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内容,虽然一些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的认知能力有显著影响[76],但本研究发现其与非认知能力通常并无显著关系。[77]
(三)学校投资模型的BMA估计
表4报告了控制禀赋效应后学校投资因素的BMA估计结果。学校投资因素包括资源、制度和关系三类。模型中加入禀赋因素为焦点变量,用以控制禀赋效应。通过估计可以发现:
第一,学校资源因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较弱。资源类变量中,初高中学校的城乡所在地、学校规模、班级规模以及初中名校因素的PIP估计值都低于0.5,而学校资源指数也仅对高中生的坚韧性有较弱的影响效应。在高中阶段,名校高中生的坚韧性、合作性和自尊、学校情感投入都显著高于一般高中的学生,但这可能反映了我国中考制度的分流结果。即严格的中考制度使优质和普通生源分别进入重点和一般高中,进而出现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群体差异。
第二,部分学校制度因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表现产生影响。初中校的晚自习制度是稳健负向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键因素,包括学生的合作性和学校情感投入。这表示初中校实施晚自习制度,将显著降低学生的合作性水平,并伤害学生对学校学习的兴趣、归属感等情感投入。在高中阶段,寄宿生的坚韧性、自尊水平都稳健高于走读生。但其他制度因素,包括入学考试、座位轮换制度、班级随机分配、学校时间、社团参加等都没有表现出与学生非认知能力的稳健关系。
第三,学校关系类因素是影响初高中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键因素,并大多达到了非常强的证据水平。其中,有更多师生交流的学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坚韧性、自尊、学校情感投入、合作性以及更低水平的孤僻性。同伴关系更好的中学生也有更高水平的自尊、合作性和更低水平的孤僻性。对遭遇校园欺凌的学生来说,其自尊、坚韧性水平都显著更低,并且也有更消极的学习体验和学校归属感。
上述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发现表现出一致性。如前所述,与学业成绩或认知能力不同,学生非认知能力在学校间的差异通常很小,进而可推论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校内而非校间。本文估计也验证了这一假设,如表4所示,初高中学生非认知能力的校间方差在10%以下,这也预示了学校间因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很有限。但与之相反,学校内部与人连接的因素,包括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以及校园欺凌等,被发现是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这和已有研究的OLS估计结果表现一致。[78][79]
(四)关键影响因素的总结
按照PIP不低于0.5的标准,对表2—4的BMA估计结果进行整理。对于初高中学生的10个非认知能力指标来说,各因素能稳健预测的个数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
一是与人连接的“关系类”因素是中学生多个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父母教养风格、校园欺凌、师生沟通和同伴关系等。
二是家庭和学校的“资源类”因素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较弱。传统上被认为重要的教育投资要素,如课外班学习、学校所在地、班级规模、学校资源以及父母养育时间的投入和行为参与,却很少与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生稳健关系;但青少年参与家务劳动、体育锻炼,以及和朋友玩、上网的时间则与一部分非认知能力发生稳健关系。
三是“禀赋类”因素也仅对中学生部分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尽管家庭经济社会背景通常被认为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或认知能力至关重要,但也仅与学生部分非认知表现相关。
上述结果表示,与资源性投入对认知或学业成绩的重要性相比,学生的非认知发展较少依赖于家庭和学校的资源性投入,即关键的投入要素不再是物质或时间资源的投入,而是父母教养风格、师生交流、校园欺凌和同伴关系等与人连接的关系因素。即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来说,父母在养育子女时采取的态度、策略和风格等,比教育资源甚至时间的投入更为重要。学校教育投资也应从关注学校资源性因素转向更多关注校内与人连接的因素。基于本研究的发现,父母采取温暖型教养风格、增加师生交流、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乃至改善同伴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基于BMA、WALS和OLS估计的比较
为了检验BMA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用WALS(Weighted-average Least Squares)和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方法进行估计,并与BMA估计结果比较。WALS方法是一种由马格努斯等发展的估计技术[80],它为BMA估计提供了一种模型平均技术的替代方案。与BMA估计不同,WALS方法采用加权平均最小二乘估计办法(Weighted-average
Least Squares,简称WALS),基本思想是先根据模型空间中的每个模型条件来估计感兴趣的参数,然后将这些条件估计值作为加权平均值计算无条件估计值。它是一种通过测试前估计器的统计特性来处理对先验无知的办法,因而与BMA估计相比,能极大减少计算负担。德卢卡和马格努斯对WALS和BMA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它们具有一致性[81],因此在本文中被用于检验BMA估计的稳健性。
表6—8报告了WALS估计的t值和OLS估计的显著性系数,并同时提供BMA估计的PIP值,可以发现:一是BMA估计的PIP值越大,相应WALS的t值也越大,同时OLS估计的显著性系数也更低。二是当BMA估计的PIP值不低于0.5 时,相应WALS和OLS的估计结果基本都出现了显著性,即绝大部分WALS估计的t值高于2,而OLS估计的显著性系数也都低于0.05,这说明当以PIP值不低于0.5为标准时,BMA估计结果展示了强稳健性,它可表示某因素在绝大多数模型条件下,都能稳健预测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水平。
五、总结和启示
(一)总结
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经济和非经济价值,但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培养还有待探索。本研究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针对中学生的非认知能力表现及其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专门调查,数据覆盖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初高中学生。二是在丰富的调查数据基础上,应用BMA技术探索中学生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对50多个潜在影响因素的BMA估计基础上,一个重要发现是,与人连接的“关系类”因素是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包括父母的教养风格、学校的师生交流、同伴关系和校园欺凌等。而在传统上被认为重要的资源投入因素,包括课外班学习、学校所在地、学校和班级规模以及父母养育时间的投入等,却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表现影响有限。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也仅预测了一小部分非认知能力。这说明对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来说,关键的投入要素可能不再是传统的物质甚至时间资源的投入,而是父母教养子女采取的态度及策略以及学生所处的与同伴、老师之间的关系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BMA估计的目的是识别某因素在模型中的重要性,而并非解决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于本文发现来说,严格因果关系还有待实验研究或其他因果推断技术的检验。然而,相比过去主要依靠OLS估计但因模型不确定常导致结论的不一致,BMA估计能够通过处理对先验知识的无知来更有效地处理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而使其估计结果比OLS估计更为稳健和保守。此外,BMA估计并不专注于寻找一个最优模型的特征,使其在信息有限的探索性研究中显示出较高价值,包括非认知能力作为一个新兴议题的探索性研究。
(二)启示
如上所述,中学生与父母、教师、学校以及同伴连接的“关系类”因素是其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在不增加物质或时间等资源性投入的情况下,父母可以通过采取温暖积极而非拒绝或过度保护的教养策略等促进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对学校来说,也预示了一个新的改进方向,即与依靠增加资源投入的传统策略相区别,学校通过增加师生沟通、改善同伴关系、减少校园欺凌等提升学生的非认知能力水平。这也为突破禀赋和资源的约束、促进平等甚至阻断贫穷的传递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相比于改变个人或家庭禀赋、增加学校经费等策略,父母和教师在选择如何对待和教养青少年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因此,即便处于经济不利地位,如果父母或教师能选择采取积极的教养或教育方式,也可能保护其免受贫穷的不利影响,甚至弥补资源投入的不足。
二是与过去主要以学业成绩为产出、并专重资源投入的方案相区别,以非认知能力为产出的教育投资研究应从“资源类”要素转向关注与人连接的“关系类”要素。即从重视家庭的经济资源甚至时间投入研究转向探索父母的教育教养策略;从研究学校资源投入转向关注师生交流、同伴关系、校园欺凌等学校与人连接的要素。近年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对人类发展的投资不仅包括时间和市场资源的投入,父母的育儿方式和教养实践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也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投资要素加以研究。[82]而根据本研究的发现,它可能构成了人类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投资要素,并比传统研究关注的资源投入、家庭经济社会背景等禀赋因素更为重要。[83]正如经济学家赫克曼所言:“与处于经济劣势的儿童被高质量地养育相比,经济优渥的儿童被低质量地养育对其发展更为不利”。[84]
参考文献
[1]Poropat, A. E. (2009). A meta-analysis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2), 322—338.
[2]Barrick, M. R., & Mount, M. K.
(1991).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and job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ersonnel Psychology, 44(1), 1—26.
[3]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Skills for social progress: The power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Paris: OECD Publishing.
[4]Strickhouser, J. E., Zell, E., &
Krizan, Z. (2017). Does personality predict health and well-being A metasynthesis. Health Psychology, 36(8),
797—810.
[5]Edin, P. A., Fredriksson, P., Nybom, M.,
& Ockert, B. (2022). The rising return to non-cognitive ski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4(2), 78—100.
[6]Deming, D. J. (2017).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social skills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4), 1593—1640.
[7]Jones, S. M., & Kahn, J. (2017). The
evidence base for how we learn: Supporting students’ social, emotion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WERA Educational Journal,10(1),5—10.
[8]Kautz, T, Heckman, J., Diris, R, ter
Weel, B, Borghans, L.(2015).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 Improving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Promote Lifetime Success. OECD Publisher.
[9]Buis, M. L. (2013). The composition of
family backgrou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both
parents on the offspring’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between
1939 and 1991.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3), 593—602.
[10]Brooks-Gunn, J., & Duncan, G. J.
(1997). The effects of poverty on children. The Future of Children, 7(2),
55—71.
[11]Blau, D. M. (1999).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child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1(2),
261—276.
[12]Radl, J., Salazar, L., &
Cebolla-Boado, H. (2017). Does living in a fatherless household compromise
educational succ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33(2),
217—242.
[13]Fletcher, J. M., & Kim, J. (2019).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non-cognitive Skills: Evidence from natural
experiments. Labour Economics, 56, 36—43.
[14]Black, S. E., Grönqvist, E., & Öckert, B. (2018). Born to lead The effect of birth order on noncognitive
abil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00(2), 274—286.
[15]Fan, X., & Chen, M. (2001).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3(1), 1—22.
[16]Hill, N. E., & Tyson, D. F. (2009).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middle school: a meta-analytic assessment of the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achieve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5(3), 740—763.
[17]Coneus, K., Laucht, M., & Reuβ, K.
(2012). The role of parental investments for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Evidence for the first 11 years of life.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10(2), 189—209.
[18]Pinquart, M. (2017).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with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5),
873—932.
[19]Ali, S., Khatun, N., Khaleque, A.,
& Rohner, R. P. (2019). They love me not: A meta-analysis of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al undifferentiated rejection and offspring’s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50(2), 185—199.
[20]Seow, P. S., & Pan, G. (2014).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articipation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89(7),
361—366.
[21]Piché, G., Fitzpatrick, C., &
Pagani, L. S. (2015). Associations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and
self-regul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5 to 10 years of age.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30(1), e32—e40.
[22]Fan, H., Xu, J., Cai, Z., He, J., &
Fan, X. (2017). Homework and students’ achievement in math and science: A
30-year meta-analysis, 1986—2015.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 35—54.
[23]Jackson, L. A., Von Eye, A., Biocca, F.
A., Barbatsis, G., Zhao, Y., & Fitzgerald, H. E. (2006). Does home internet
use influence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low-income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3), 429.
[24]Curcio, G., Ferrara, M., & De
Gennaro, L. (2006). Sleep loss, learning capaci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Sleep Medicine Reviews, 10(5), 323—3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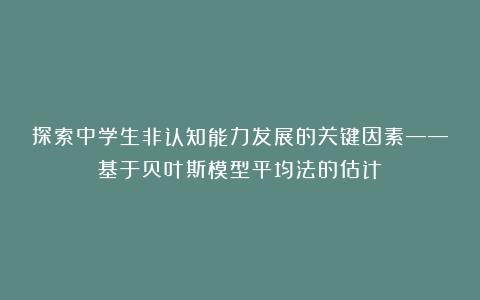
[25]Hanushek, E. A. (1997).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school resources on student performance: An updat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2), 141—164.
[26]Hanushek, E. A., & Woessmann, L.
(2017). School resources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A review of cross-country
economic research. In M. Rosén, K. Y. Hansen, & U. Wolff (Eds.),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pp. 149—171).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7]Gong, J., Lu, Y., & Song, H.
(2021). Gender Peer Effects on Students’ Academic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Evidence and Mechanism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6(3), 686—710.
[28]Roorda, D. L., Koomen, H. M., Spilt, J.
L., & Oort, F. J. (2011). The influence of affec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on students’ school engagement and achievement: A meta-analytic
approa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1(4), 493—529.
[29]Dee, T. S., & West, M. R. (2011).
The non-cognitive returns to class siz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33(1), 23—46.
[30]Fredriksson, P., ckert, B., & Oosterbeek, H. (2013).
Long-term effects of class siz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1),
249—285.
[31]Konu, A. I., Lintonen, T. P., &
Autio, V. J. (2002). Evaluation of well-being in schools-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general subjective well-being.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13(2), 187—20.
[32]Van Landeghem, G., Van Damme, J.,
Opdenakker, M. C., De Frairie, D. F., & Onghena, P. (2002). The effect of
schools and classes on noncognitive outcome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13(4), 429—451.
[33]Opdenakker, M. C., & Van Damme, J.
(2000). Effects of schools, teaching staff and classes on achievement and
well-be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chool
outcome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11(2), 165—196.
[34]Gray, J. (2004).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the ‘other outcomes’ of secondary schooling: a reassessment of three
decades of British research. Improving Schools, 7(2), 185—198.
[35]雷万鹏, 李贞义. 教师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6): 160—168.
[36]袁振国,黄忠敬,李婧娟,张静.中国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报告[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9): 1—32.
[37]Raftery, A. E. Bayesian model selection
in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5(1995),111—163.
[38]Ciccone, A., & Jarociński, M.
(2010).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Will data te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4), 222—46.
[39]Horvath, R. (2011). 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nalysis. Economic
Modelling, 28(6), 2669—2673.
[40]Kautz, T, Heckman, J., Diris, R, ter
Weel, B, & Borghans, L (2015). Fostering and Measuring Skills: Improving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Promote Lifetime Success. Paris: OECD Publisher.
[41]周金燕.中小学生非认知技能的测量及实证表现: 以中国六省市数据为基础[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1(1): 87—108+191—192.
[42]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10): 1—3.
[43]Duckworth, A. L., & Quinn, P. D.
(200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hort Grit Scale (GRI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91(2), 166—174.
[44]Duckworth, A. L., Peterson, C.,
Matthews, M. D., & Kelly, D. R. (2007). Grit: perseverance and passion for
long-term go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6), 1087.
[45]Kelly, D. R., Matthews, M. D., &
Bartone, P. T. (2014). Grit and hardiness as predictors of performance among
West Point cadets. Military Psychology, 26(4), 327—342.
[46]Reed, J., Pritschet, B. L., &
Cutton, D. M. (2013). Grit, conscientiousness, and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for exercise behavior.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8(5), 612—619.
[47]Singh, K., & Jha, S. D. (2008).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nd grit as predictors of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the Indian Academy of Applied Psychology, 34(2),
40—45.
[48]Johnson, D. W., & Norem-Hebeisen,
A. A. (1979). A measure of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9(2), 253—261.
[49]Johnson, D. W., Maruyama, G., Johnson,
R., Nelson, D., & Skon, L. (1981). Effects of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goal structures on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9(1), 47—62.
[50]Johnson, D. W., Maruyama, G., Johnson,
R., Nelson, D., & Skon, L. (1981). Effects of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goal structures on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9(1), 47—62.
[51]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18.
[52]Lam, S. F., Jimerson, S., Wong, B. P.,
Kikas, E., Shin, H., Veiga, F. H., … & Zollneritsch, J. (2014).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student engagement in school: The results of an
international study from 12 countrie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9(2),
213—232.
[53]Robins, R. W., Tracy, J. L.,
Trzesniewski, K., Potter, J., & Gosling, S. D. (2001).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self-estee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5(4), 463—482.
[54]Sowislo, J. F., & Orth, U. (2013).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1), 213—240.
[55]Alves-Martins, M., Peixoto, F.,
Gouveia-Pereira, M., Amaral, V., & Pedro, I. (2002).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2(1), 51—62.
[56]Orth, U., Robins, R. W., & Widaman,
K. F. (2012). Life-span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and its effects on important
life outcom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6), 1271—1288.
[57]Magnusson, C., & Nermo, M. (2018).
From childhood to young adulthood: the importance of self-esteem during
childhood for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s among young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1(10), 1392—1410.
[58]Dotterer, A. M., & Lowe, K. (2011).
Classroom context, school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0(12), 1649—1660.
[59]Becker, G. S., & Tomes, N. (1976).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4), Part 2), S143—S162.
[60]Bonke, J., & Esping-Andersen, G.
(2011). Family investments in children-productivities, preferences, and
parental child car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43—55.
[61]Arrindell, W. A., Sanavio, E., Aguilar,
G., Sica, C., Hatzichristou, C., Eisemann, M., … & van der Ende, J.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a short form of the EMBU: Its appraisal with students in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and Ital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7(4), 613—628.
[62]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许燕.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1): 94—99.
[63]Durlauf, S. N., Kourtellos, A., &
Tan, C. M. (2008). Are any
growth theories robust The Economic
Journal, 118(527), 329—346.
[64]Hinne, M., Gronau, Q. F., van den
Bergh, D., & Wagenmakers, E. J. (2020). A conceptual introduction to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dvances in
Methods and Practi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
200—215.
[65][81]De Luca, G., & Magnus, J. R. (2011).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and
weighted-average least squares: Equivariance, stability, and numerical issues.
The Stata Journal, 11(4), 518—544.
[66]Raftery, A. E., Madigan, D., &
Hoeting, J. A. (1997).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for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2(437), 179—191.
[67][80]Magnus, J. R., Powell, O., &
Prüfer, P. (2010). A comparison
of two model averaging techniqu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growth empir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54(2), 139—153
[68]Eicher, T. S., Papageorgiou, C., &
Raftery, A. E. (2011). Default priors and predictive performance in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with application to growth determinant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6(1), 30—55.
[69]Kass, R. E., & Raftery, A. E. (1995). Bayes facto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0(430), 773—795.
[70]Huston, A. C., & Rosenkrantz
Aronson, S. (2005). Mothers’ time with infant and time in employment as
predictors of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children’s early development.
Child Development, 76(2), 467—482.
[71]Coneus, K., Laucht, M., & Reu, K.
(2012). The role of parental investments for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Evidence for the first 11 years of life.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10(2), 189—209.
[72]Fiorini, M., & Keane, M. P. (2014).
How the allocation of children’s time affect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2(4), 787—836.
[73]Chan, T. W., & Koo, A. (2011).
Parenting style and youth outcomes in the UK.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3), 385—399.
[74]Weiss, L. H., & Schwarz, J. C.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types and older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cademic achievement, adjustment, and substance use. Child
Development, 67(5), 2101—2114.
[75]Deng, L., & Tong, T. (2020).
Parenting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in children. China
Economic Review, 62, 101477:1—15.
[76]Hajar, A., & Karakus, M. (2022). A
bibliometric mapping of shadow education research: achievements, limitations,
and the future.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3(2), 341—359.
[77]Zhao, X. (2019). The Influence of
Shadow Education 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Modern
Economy, 10(3), 945—961.
[78]Baker, J. A., Grant, S., & Morlock,
L. (2008).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s a developmental context for
children with internalizing or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School
Psychology Quarterly, 23(1), 3—15.
[79]Xu, D., Zhang, Q., & Zhou, X.
(2022). The Impact of Low-Ability Peers on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Outcomes
Random Assignment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and Operating Channel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7(2), 555—596.
[82]Cobb-Clark, D. A., Salamanca, N., &
Zhu, A. (2019). Parenting style as an invest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2(4), 1315—1352.
[83]Tramonte, L., & Willms, J. D.
(2010). Cultural capital and its effects on education outcom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9(2), 200—213.
[84]Heckman, J. J. (2011).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The valu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merican Educator, 35(1),
31—35+47.
(责任编辑 范皑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