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的神秘,在于它以千年风沙为笔,将佛国幻境镌刻在崖壁之上;时间的厚重,在于它以朝代更迭为尺,丈量着文明传承的刻度。那些历经千年的飞天、佛陀与瑞兽,在时光长河里诉说着关于生命、轮回与永恒的命题。
当我凝视手中这件“生生不息”的玉牌时,恍若听见洞窟中飘来的梵音,看见三危山巅的月光洒落在青花玉料之上——以匠心为笔,将敦煌的神秘与玉魂的温润融为一体,让一块石头有了呼吸,让一种文化有了温度。
轮回之韵:敦煌符号的当代转译
“生生不息”是“三耳共兔”的诠释。这源自敦煌莫高窟藻井图案,是古人对“三世轮回”的具象化表达。三只兔子共用三耳,首尾相衔,循环往复。在佛教哲学中,过去、现在、未来本为一体,恰如这三只兔子在旋转中模糊了时间的边界,传递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宇宙观。
无相佛端坐莲台,摒弃了五官的具象,这让人想起《金刚经》中“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偈语——真正的佛性不在形貌,而在观者心中升起的觉悟。
八瓣莲取自敦煌壁画中的曼陀罗图腾。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超脱轮回的清净;八瓣则对应佛教“八正道”,是修行者通往觉悟的路径。
而这件作品最巧妙的构思,我认为是玉雕师对于墨色的运用。墨色晕染处化作飞天仙女的侧影,这是对莫高窟“散花飞天”的致敬——仙女飞升的动态定格为永恒的瞬间。墨色恰似云雾,既暗合“飞天”之名,又为作品注入了一抹敦煌特有的奇幻色彩。
玉牌命名为“生生不息”,不仅因三耳共兔的轮回意象,更因它见证了玉雕技艺的传承。从敦煌壁画到和田青花籽料,从北魏画工到当代玉雕师,一种文明以器物为载体,穿越千年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最好注脚。
刀锋禅意:以器载道的东方美学
玉雕师选用新疆和田青花籽料,其玉质温润如凝脂,墨色与青白交织,恰似一幅天然的水墨画。玉雕师以”天人合一”的智慧,令天然瑕疵焕发新生:墨斑化作飞天衣袂,皮壳演为兔耳轮廓,在虚实相生间完成对敦煌符号的转译。作品以方正为骨,弧面作魂,刚柔并济诠释”天圆地方”的东方宇宙观。顶部凹面随光影流转演绎月相盈亏,时空的诗意在方寸间流转。
正面无相佛以极简线条勾勒禅意,佛陀跏趺而坐,衣袂垂落,虽无五官,却因轮廓流畅,令人顿悟。青花纹自肩后蜿蜒,如千年风沙凝成的烟霭,既似敦煌佛光,又似智慧光芒流转。
右侧面下方的三耳共兔纹样,以镂雕技法呈现三只共用三耳、首尾相衔的兔子,刀法流畅,既显玉质温润,又现循环动势。黑皮勾勒兔耳轮廓,与青白玉质形成冷暖对比,暗合夜幕星辰之辉。此纹样与正面无相佛相呼应,前者述生命轮回,后者诠智慧恒常,正是作品点题之处。
背面穿孔处,玉雕师浅绘八瓣莲绽放,花瓣脉络纤细清晰,暗含向心力。最令人惊叹的是背面左端的飞天意象。墨色晕染之处,恰似敦煌飞仙升天之景。仙女双手合十,单脚直立,另一腿盘膝的侧影,生动地展现出飞仙轻盈飘逸、超凡脱俗的神韵。墨色犹如飞仙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为作品增添了一抹神秘而灵动的色彩。
这件作品堪称材质与技法的完美共生。青花玉的墨色晕染本为天然瑕疵,却被玉雕师化作飞天与云雾;皮壳处的黑皮则被雕琢为三耳共兔的纹样,变废为宝。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正是中国玉雕“天人合一”哲学的体现——玉雕师非雕刻者,而是玉魂的唤醒者。
我常想:为何敦煌壁画能千年不朽?为何和田玉能历久弥新?答案或许藏在“生生不息”的刀痕里——那些循环往复的纹样,那些超越形貌的禅意,那些化瑕疵为神奇的智慧,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对过去的复制,而是对永恒的追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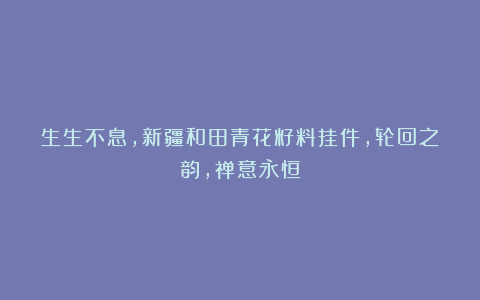
敦煌的风沙仍在吹拂,和田的玉石仍在生长。而这块青花玉雕,将带着三耳共兔的轮回、无相佛的禅意、八瓣莲的圣洁与飞天的灵动,继续讲述一个关于“生生不息”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玉,是人,更是文明本身。
生生不息,挂件,新疆和田青花籽料,大面积留皮,参考白度一级以上,肉质非常细腻,可过灯,润度很好,油分十足,学院派名家精工,尺寸约53*29.3*13.3mm,重37.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