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就如同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深深烙印在了我父亲的记忆里。几十年后,五十多岁的他留着灰白色的平头,有着钢铁工人般结实的体格正端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粗糙且长满老茧的手里握着一瓶小麦酿造的啤酒。“嗯,”他会带着些许迟疑、不自在的神情开口,然后开始讲述那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对他来说,明尼阿波利斯市东北区的昆西街曾是他的家,而夏威夷群岛只不过是《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图片。20世纪30年代末,阿尔·罗杰斯离开家人,加入民间资源保护队工作,之后又投身于美国海军。1941年感恩节那天,海军巡逻飞艇排列在瓦胡岛东北侧卡内奥赫湾的水上飞机坡道上。21岁的航空机械军士阿尔·罗杰斯被分配到了驻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的第12海上巡逻机中队 。
1941年的11月26日,日本联合舰队开始了前往夏威夷群岛的漫长航行,这段不祥的旅程注定会将我父亲与一名日本海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此时,在“苍龙”号航空母舰上,饭田房太中尉,这位日本帝国海军中的后起之秀正在思索着前路如何。他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荣获过天皇嘉奖,是一名在与中国作战中磨砺过飞行技巧且极富攻击精神的战斗机飞行员,不久后他将在瓦胡岛上空声名鹊起。
12月7日,星期日,清晨6点,在夏威夷以北220英里处,第一波飞机从日本航母甲板上起飞。当飞机在大洋初升的阳光洒下的碎云中嗡嗡飞行时,瓦胡岛仍在沉睡,毫无察觉,但在卡内奥赫湾的海军航空站营房里,像往常一样的闲聊和喧闹声在大约7点50分变得格外吵闹。此时,刚和衣躺下的阿尔·罗杰斯(因通宵工作变得疲惫不堪和情绪烦躁)从床上翻身而起、紧握双拳撞开营房大门,朝着那群人中声音最大的水手走去。
突然,头顶上星形空冷发动机的轰鸣声盖过了水手们的嘈杂声,他听到了混乱的呼喊:
“这到底是……?”
“肯定是陆军在搞演习。”
“那些大红圈……”
机关枪开始猛烈扫射。一名水手指着窗外大喊:“是日本飞机!”
营房开始震颤起来。一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过,它的机枪曳光弹朝着行政大楼飞掠而去。混乱中,罗杰斯手忙脚乱地穿上白色礼服裤、蓝色工作衬衫、靴子,戴上白色水手帽——此时制服搭配是否合适已无关紧要。
卡内奥赫遭到了攻击!
日本飞机向航空站猛扑下来,那是一群致命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天空中充斥着爆炸和枪炮声。在一号机库附近,六架 联合公司的PBY-5“卡塔琳娜”水上飞机被大火吞噬。日本人的炸弹撕裂了它们的机身造成燃油箱爆炸,燃起了巨大的火柱和浓烟。顽强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们徒劳用步枪、轻机枪,甚至还有手枪进行反击,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倒下。
入侵者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那些黑乎乎、致命的飞机嗡嗡地向东边天空飞去。作为太平洋舰队的远程侦察力量,卡内奥赫航空站内的PBY水上飞机在黎明时分已经损失殆尽。
上图即为珍珠港遇袭当天,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内一号机库和外面的PBY-5被摧毁的画面。
上图为首波袭击过后,海军官兵们正在齐心协力地拯救一架受损的PBY。日本人在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共摧毁27架“卡塔琳娜”。
罗杰斯穿过灾难现场,直到抵达指定的飞机旁。不远处,PBY水上飞机熊熊燃烧,大火产生巨大且刺鼻的黑色浓烟,滚滚升入蓝色的太平洋天空。当他爬进了他的工作岗位——一架PBY“卡塔琳娜”水上飞艇内时,那里面已经有人了,并且看起来都比他更加老道,这让罗杰斯感到有点紧张和不安。PBY在机身两侧敞开的腰部舱口处都安装有带活动枪架的点50口径机枪和弹链,多余的弹药盒则挂在机身中部的舱壁上。此外,机头炮塔里还备有一挺点30口径的机枪。
“我觉得他们不敢再来了。”一名水手怒气冲冲地说道。
“毕竟,”另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
在噼啪作响的火焰和黑烟中,燃烧着的铝制水上飞机渐渐融化在地面上。此刻,PBY飞艇里的人们心中怒火中烧,渴望着复仇,焦急地坚守着射击岗位,并且努力调整情绪去适应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长久的等待后,一些人离开飞艇去取额外的弹药,还有几个人忙着去找咖啡提神,其中一人还说道:“这会是漫长的一天。”罗杰斯和报务员留在了飞机里继续警戒。
上午9点左右,一号机库外的水手们突然指向天空。原来,由饭田中尉率领的第二批九架日本战斗机正从北方呼啸而来,对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再次攻击。
报务员开始穿过机身向前跑,同时回头对罗杰斯喊道:“他们回来了!你负责点50口径机枪,我去操纵机头的点30口径机枪。”
罗杰斯只是一名航空机械师,并非炮手,根本不会使用点50机枪。于是,他喊回报务员现场指导。那人匆忙向罗杰斯解释道:“这是扳机,这是装弹手柄,这是训练用弹药,每十发就有一发哑弹。”
罗杰斯闻言后,难以置信地叫道:“哑弹!”
“别担心,”报务员急促地解释道,“只要把这个手柄往后拉,就能再次射击。”说完,他就转身匆匆奔向机头,给罗杰斯的基本枪炮操作讲解也就此结束。
敌机向航空站俯冲而下。与此同时,罗杰斯在脑海中快速回忆着刚学的点50口径机枪射击要领。当敌机编队飞近时,他迅速打出一个短点射,但子弹并未击中领队飞机。
零式战斗机一架接着一架,在航空站上空盘旋,所到之处不是死亡就是毁灭。它们再次飞向跑道和机库,枪炮齐射。罗杰斯瞄准目标开枪,子弹在目标后方划出一道道弧线。随着每隔十发子弹拉动一次装弹手柄,他变得愈发紧张。点50口径机枪的哒哒声在PBY的机身内回响,就像在一个55加仑的大桶里发出的声音一样,弹壳随着枪声纷纷落在地板上。
“就像打雉鸡一样,要预判目标提前量。”罗杰斯喃喃自语,“预判那该死的目标提前量!”
日军战机的炮火继续肆虐,把这些珍贵的水上飞艇打得千疮百孔、熊熊燃烧。PBY-5型水上飞艇在空中飞行速度却较慢、姿态优雅,但在地面上它们就像条搁浅的鲸鱼依靠着登岸坡道停在那里,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大型双轮,尾部还装有一个尾轮。水手们在浓烟烈火、日军飞机持续的轰鸣声和机枪的扫射声中四处奔逃寻找着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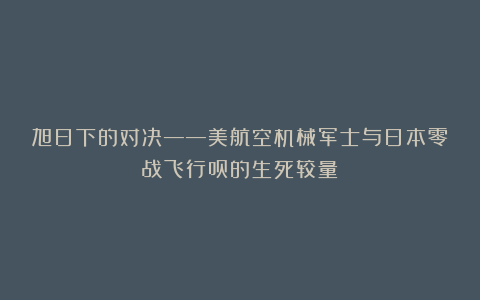
罗杰斯既愤怒又紧张,重新调整短点射方向,瞄准另一队来袭的战斗机。敌机朝着营房、商店、军械库和行政楼飞去,一边飞一边扫射。此刻,在海湾上空,一架孤零零的A6M2型零式战斗机大坡度盘旋着,猛然俯冲而下。
饭田房太驾驶着他的零式战斗机宛如一个带翼的武士,倾斜着机身,穿过浓烟烈火急速俯冲。罗杰斯浑身是汗,心脏狂跳,怒火中烧,他按捺着没有开火。这次他下定决心绝不能打偏。
这架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似乎铁了心要消灭这架飞艇上那些麻烦的炮手,不断地朝着他的目标逼近。零式战斗机的机翼后方冒出一缕烟雾,机头和机翼上的枪炮猛烈开火。在最后一刻,“预判那该死的目标提前量”的罗杰斯打出一个短点射,击中了那架零式战斗机。饭田猛地倾斜机身转弯避开,呼啸着飞过第一大街,军械库方向所有的地面火力都朝着它倾泄着弹药。
片刻之后,饭田的飞行编队重新集合起来,转向瞄准镜山口(卡内奥赫湾对面山脉中的一个山隘口),但饭田自己落在了编队后面。此时,地面上的罗杰斯和报务员注视着这一切等待着。
饭田的僚机,海军中尉藤田立刻判断出问题所在:长机的飞机在漏油,这位日军飞行队长被地面火力击中了。饭田指指自己,又指指地面。藤田想起那天早上在“苍龙号”上他的这位朋友颇具预言性的坚定话语。饭田曾说,万一他无法完成任务,“我会一头撞向敌人目标,而不是尝试紧急迫降” 。饭田挥手让他的队员离开,然后朝海湾俯冲而去。藤田无助地看着他的战友朝着卡内奥赫一头栽下。
饭田的零式战斗机俯冲向水面,然后改平,俯冲和改出的角度都很突然。发动机呼啸着,这架A6M2型战斗机朝着水上飞艇停机坡道和一号机库飞去。
为了引诱对手靠近,罗杰斯离开自己的机枪,拉动了PBY水上飞机舱壁上的辅助弹药架。零式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停机坡道,炮火穿透了正在燃烧的水上飞艇。在最后一刻,罗杰斯猛地回到射击位置上,操起点50口径机枪瞄准饭田的零式战斗机。零式飞机尾部拖着一道白色尾迹,离PBY越来越近。
饭田驾机朝着目标呼啸着直挺挺地逼近,丝毫没有改变方向的意思。罗杰斯猛然扣动了点50口径机枪的扳机,一团烟雾和一丝火焰从零战发动机里冒了出来,饭田再次被击中了!然而他毫无畏惧,继续驾驶飞机倾斜着飞过第一大街,朝军械库冲去。当飞机一头扎向地面时,航空军械士桑兹正用自动步枪朝其猛烈开火。零战机身因撞击变形,巨大的星形发动机从支架上扯脱,不停地翻滚着,最终停在一所房子旁边。饭田房太的尸体被埋在了飞机残骸里。
上图为苍龙号舰战队零战飞行员饭田房太少尉的座机涂装和战术编号
报务员从PBY水上飞机的前炮塔爬回机舱。罗杰斯兴高采烈地喊道:“我们击中它了!”
“我们?”报务员说,“你自己搞定的!机翼挡着我的枪线了,我没法射击。”在战斗最激烈的那些混乱时刻,有好几名军人都声称是自己击落了饭田,但我父亲对那天事件的记忆却从未动摇。
然而,他们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在他们身后,一枚炸弹穿透一号机库的屋顶,然后在内部爆炸,碎片如雨点般落在跑道上,燃起的大火和刺鼻的浓烟遮蔽了天空。
罗杰斯和报务员在混乱中冲向那片火海。一名腿部骨折、全身烧伤的水手从机库残骸中爬了出来。在酷热和浓烟中,他们把这名水手拖到安全地带,然后和其他伤员一起抬上一辆路过的卡车。
随后,罗杰斯独自爬进PBY水上飞艇察看受损情况。油漆起泡、襟翼烧毁、机身被弹片击穿、轮胎爆裂。看样子,这飞机短期内是飞不起来了。不久,命令传来,让罗杰斯拆下机枪去航空站中央的小土坡集合。
随后是紧张的警戒。在接下来漫长的夜晚,远处山丘上偶尔传来的高射炮轰鸣声在海湾上空回荡,曳光弹划破漆黑的夜空。随着谣言四起,已经疲惫不堪的水手们睁大眼睛,警惕地搜寻着从未到来的登陆行动。在科奥劳山脉那边,燃烧着的珍珠港在夜空中发出微光。
12月8日黎明,四周一片死寂,卡内奥赫海军航空站内仍在冒烟。二十七架PBY水上飞艇已被烧成焦黑的残骸;机库成了一堆瓦砾,被大火和浓烟熏黑;死者仍在清点中。
罗杰斯和一名水手从哨位换岗下来,拖着沉重的步伐,经过航空站医务室,朝空袭后仅存的营房走去。
“嗨,水手们,到这边来。” 一个威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原来是驻地医生在向他们喊话。他身穿血迹斑斑的制服,脸上带着疲惫却坚定的神情,一看就是个不一般的人。两名水手都被带到充当临时停尸房的医务室车库,还拿到了锤子和钉子用来制作棺材。
“赶紧动手。” 医生说,“我再去找些帮手。”很快又有四名水手赶到。这位 “医生” 又派了六个人去营房换装,准备参加埋葬任务。
水手们在制作棺材时,两名海军陆战队员开着一辆吉普车来了。他们卸下一个垃圾桶,放在医务室入口旁边。垃圾桶里是在卡内奥赫被击落的唯一一名日本飞行员饭田的遗体。这个垃圾桶一整天大部分时间都放在门口无人问津,直到水手们为他们牺牲的同伴完成了丧葬准备工作后,才被人从垃圾桶里最终抬了进来,放置在了一张木桌上。他的飞行服到处是血渍,遗体遍体鳞伤。
想到那些死伤的水手、遭受攻击的航空站,以及眼前这个曾用机枪扫射他们的人,罗杰斯思绪万千。愤怒、疲惫和极度的困惑取代了他可能对这个倒下的对手怀有的任何情感。
当天晚些时候,一支由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仪仗队用卡车把16口松木棺材运到了海边一个隐蔽的峡谷。在同一地点,饭田中尉的遗体被安葬在了一个单独的墓穴中。
阿尔·罗杰斯默默站在送葬队伍后排的沙丘上,无人注意。他仍穿着白色裤子、戴着帽子和蓝色工作服。一群头戴钢盔、身着卡其军装、手持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穿着白色礼服的水手们整齐列队。所有人都表情严肃地敬礼,送别的枪声在峡谷间回荡。
在海军陆战队为在卡内奥赫突袭中丧生的人们鸣放21响之前,一名号手吹奏了熄灯号。罗杰斯穿着白色裤子,戴着帽子,站在后排,与其他水手一起向阵亡的战友致敬。
葬礼号声的哀鸣渐渐消散在风中与翻滚的海浪声里。对于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人来说,在旭日下的 “耻辱日”(指珍珠港事件 )已然结束,但对于幸存者而言,可怕的太平洋战争才刚刚开始。
珍珠港事件后,罗杰斯在VP-12巡逻机中队服役,足迹遍布太平洋各个角落。解放菲律宾期间,他被分配到轻巡洋舰 “丹佛”号(CL-58 )的航空分队,同时晋升到了一级军士。战后,他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并组建了家庭。1979年3月,当太阳在华盛顿州 “天堂马山” 升起时,他与世长辞,他是 “最伟大的一代” 中又一位逝去的人。
上图左为珍珠港事件时的罗杰斯,右为阵亡的饭田房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