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深处,一组罕见的清末彩色老照片得以流传至今,它们如同时光机般,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变革的时代。这些照片不仅展现了清末社会的风貌,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在清末的福建古田县衙的衙役们,他们手中持有的是板子和鞭子,但这些工具并未赋予他们影视剧中所描绘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形象,相反,这些衙役的衣装显得褴褛不堪,颜色黯淡,甚至有些地方还打着补丁。
清代衙役被归入“贱籍”,法律禁止其参加科举、与良民通婚。据《福安县志》载,福建州县衙役多由破产农民、无业游民充任,官方文书称其为“役卒”“胥役”,地位低于普通平民。
衙役俸禄极低(年俸约6两白银,不足九品文官的1/4),且常被县衙克扣。光绪年间古田县档案显示,当地衙役实际收入依赖“陋规”(如案件受理费、百姓“孝敬”),而非固定薪俸。
古田县属福建延平府,为“冲、疲、难”三等县(政务繁忙、财政困难)。据《福建通志》,光绪朝该县年财政收入约4000两白银,其中70%用于官员俸禄,剩余部分需支付县衙修缮、刑具购置、驿站运营等费用,分配至衙役的装备经费几乎为零。
清末,三位地主老财悠闲地坐在自家的炕头上,面前摊开了一堆零散的铜钱。他们各自手持细绳,一边将铜钱一枚枚地数清楚,一边熟练地将它们串连起来。炕上和桌子上都堆满了成串的铜钱,数量之多,足以让数钱的人数到手抽筋。
清代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占70%以上),货币地租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江南、福建)逐渐普及。据1902年《清实录》载,福建古田县地主对佃农的“分成租”通常达收成的50%-70%,“定额租”则每亩年收谷2-4石(约合200-400斤),折银约1.5-3两。若以铜钱计算,按光绪年间银钱比价1两≈1500文,单户佃农年纳租可达2250-4500文,三位地主面前堆积的铜钱,可能是数十户佃农全年的血汗结晶。
地主手中的铜钱多为“制钱”(即方孔铜钱),官方规定每1000文串为“一贯”,但民间实际操作中常因铜钱磨损、私铸钱掺入而“短串”(如每串仅950文)。三位地主使用的细绳称“钱串子”,熟练者每日可串钱20-30贯(约2-3万文),但长时间数钱会导致手指磨茧、手腕劳损,正如《闽省录》所载:“钱肆伙计数钱,指节皆肿,地主亦不免。”
地主积累的铜钱除用于购置更多土地,还通过“印子钱”(高利贷)扩大剥削。据1905年《福建农工商报》揭露,古田地主放贷月息普遍达3%-5%,若佃农借10贯钱(1万文),一年后需还13-16贯,无力偿还者则被迫“卖田契”“典妻女”。炕上成串的铜钱,可能是数十份田契、人身契约的等价物。
地主的“富裕生活”建立在佃农贫困之上。同期西方传教士记载,古田首富林氏家族“日啖山珍,衣必绫罗”,其宅中象牙烟枪、翡翠扳指等物价值千金,而其名下300亩佃田的耕作者“衣破如鹑,面有菜色”。地主数钱时的悠闲,与佃农“卖屋纳租,拆屋当柴”(《古田县志》)形成残酷对比。
清末之际,当一队外国摄影师踏入这片古老的土地,当地百姓立刻被这一新奇景象所吸引,纷纷聚拢围观。他们不仅对外国人的金发碧眼充满了好奇,更对摄影师手中那个能冒出白烟的“神奇盒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许多人围在一起,交头接耳,猜测着这个神秘玩意儿到底有何用途。
在清末的京师,阜成门作为内城九门之一,承载着重要的交通和物流功能。作为通往京西的门户,阜成门在明清及后来的长时间里,一直是城内煤炭供应的必经之地。然而,这张照片却捕捉到了阜成门外关厢的另一番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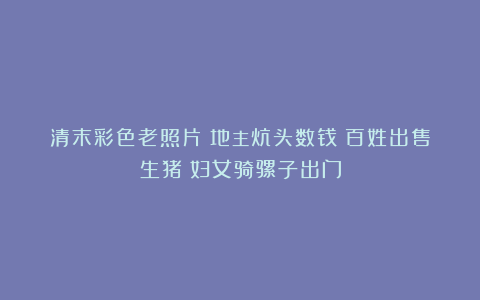
从西向东望去,阜外关厢的道路显得高低不平,泥泞不堪。阜成门自明代起即承担京西煤炭入城功能,因门头沟煤窑所产“京煤”经此运输,故城门洞内壁嵌有梅花石雕(“煤”谐音“梅”),民间称“阜成梅花报春暖”。据《天咫偶闻》记载,每日经阜成门入城的煤车、骆驼队达数百辆(峰),仅1890年冬季,单月运煤量便超200万斤。重载车辆长期碾压,导致关厢道路路基严重受损,形成“车辙深尺许,雨后积水成潭”的景象(1886年《顺天府志》)。
1888年御史弹劾:“顺天府修城工款,每千两实到工者不过三四百两,余皆入官吏私囊。”阜成门多次“修缮”实为敷衍:用黄土覆盖坑洼,雨季即被冲毁,形成“春填秋坏,岁岁如是”的恶性循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英军士兵记载:“从西直门到阜成门的道路,如同被炮弹犁过的战场,泥浆没踝,马车时常倾覆。”
清末,一对父子正在合力抬着一头膘肥体壮的生猪,步履坚定地前往集市。这头猪是他们辛勤劳作的成果,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精心饲养的宝贝。
农民自家极少杀猪,逢年节需买“刀头肉”(约2斤)祭祖,平时若吃猪肉多为“下水”(内脏),价格仅为鲜肉1/3,而是选择将它带到集市上出售,换取一些零花钱,用以购买家庭所需的日常用品。
据《清稗类钞》记载,华北农户“户均养猪2-3头,岁可获利8-12两白银”,相当于佃农半年租粮收入。父子饲养的“膘肥体壮”生猪,需耗时8-12个月,投喂麦麸、野菜、泔水约2000斤,成本约3两白银(含仔猪钱),出栏时体重可达200-250斤,按光绪年间肉价每斤120文计算,可售银24-30两,净利润达800%-1000%。这种高回报使养猪成为“穷人的银行”,但也意味着全家数月心血系于一猪。
清末各地设“牲畜税局”,按猪体重抽税5%-10%。父子可能绕道乡间小路避税,或用稻草覆盖猪身伪装成“病猪”(病畜免税)。1903年《大公报》揭露,直隶税吏常“捏称猪超重,勒索规费”,一头200斤猪竟被算成250斤,多征税银1.5两。
这张照片摄于清末的1904年,捕捉了颐和园荇桥旁的画面。画面上,几名太监正悠闲地坐在船上,他们的举止显得颇为随意,没有宫廷中的拘谨与严肃。这些太监的职责显然是对颐和园进行日常的维护工作,确保湖水的清澈与水道的畅通。
1904年,正值慈禧70岁寿典筹备期,颐和园作为其常住居所,年维护费用超白银30万两(占清廷财政支出0.5%)。荇桥位于昆明湖西北,横跨“万字河”,连接耕织图景区与颐和园主园,因靠近水源地,需每日清理浮萍、杂物,防止淤塞影响宫廷用水。据《颐和园陈设清册》记载,该区域设“河道太监”8名,专司“打捞湖草、启闭水闸、巡察堤岸”,照片中人物即属此职。
但1904年户部,实际拨给颐和园的经费仅15万两,半数被挪用修建“仁寿殿西配殿”以接待外国公使。太监们使用的木船漏缝需自筹麻絮修补,打捞工具(如竹网、铁耙)多为光绪初年旧物。据随行宫女回忆:“每日卯时(5-7点)出工,未时(13-15点)方休,午间仅食窝头咸菜,湖中水冷,冬日手脚皆裂。”照片中太监属“无品级苏拉”(最低等仆役),年俸仅银6两、米6石,需自行承担衣物鞋袜费用。
1904年能进入颐和园拍摄的多为欧美驻华公使、传教士或清廷特许的商业摄影师(如日本山本赞七郎)。此类照片常被用于西方画报的“东方奇观”专题,刻意捕捉太监、宫女等“神秘群体”,以满足猎奇心理。
清末,在遥远的旧金山,有一群华工为了生计,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异国他乡辛勤工作。19世纪中叶,美国因西部开发、铁路建设(如太平洋铁路)等需求,通过《蒲安臣条约》等渠道招募大量华工。据统计,1850-1880 年间约有 30 万华工赴美,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他们从事淘金、开矿、修铁路等高危工作
然而,即便身处异土,面对生活的重重艰难和工作的辛勤付出,他们仍无法摆脱对鸦片的依赖。鸦片,这种令人沉迷的毒品,如同一个无形的魔爪,紧紧抓住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在清末的年代,一名妇女选择了骑骡子作为出行的工具。她的小脚因长期的裹束而无法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稳健行走,因此她不得不借助这种传统的交通工具。尽管她的双脚被束缚,但她的衣着却显得光鲜亮丽,显示出她所在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
在妇女身侧,有一个男子与她同行。他的着装较为粗陋,与妇女的华丽服饰形成鲜明对比。这不禁让人猜测,那名男子是否是她的丈夫。然而,从他们的服饰和举止来看,两人似乎并不像是一对夫妻,男子或许只是她的随从、护卫或是其他身份。
这组清末彩色老照片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面貌。这些照片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我们了解过去、认识自己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