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玉雕的未来到底在哪里?这些年,总有人问我,玉雕是不是越来越没人做了?这门手艺是不是快要失传了?看着老师傅们逐渐老去,仍在坚守的八零后也多已年过四十,行业的青黄不接,确是令人忧心的现实。
不过,在我结识的许多年轻玉雕师朋友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像孟大宇、苗烈等,都是近几年涌现出的玉雕新锐。他们的作品喷薄着一股蓬勃的朝气。可以预见,十年后我们追逐的收藏品,正出自眼下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之手。玉雕的未来,就握在这些九零后手中。
根基之变:从“手艺人”到“艺术生”
传统的玉雕师傅大多是从学徒做起,在作坊里跟着师傅学艺五年、八年,能学到八九成功夫就算出师了。这种传承方式虽然扎实,但也容易囿于门户之见,难以突破既有的框架。
而现在的九零后玉雕师却大不相同。他们多是学院派出身,上过大学,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他们不仅懂雕刻,更懂造型、懂构图、懂审美。这种科班训练带来的不仅是技艺的提升,更是一种艺术视野的打开。
例如,孟大宇擅长的薄浮雕技法,便是在学校里打下的根基。薄浮雕比深浮雕更难,因为它要在极薄的厚度里做出空间感和体积感,这种对空间的精妙理解,正是学院教育的优势所在。可惜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玉雕界的一大损失。
更重要的是,学院派背景让他们能自然地将其他艺术形式的精髓融入玉雕。苗烈在设计时会借鉴国画的“虚实相生”,而孟大宇在雕刻时则运用了西方浮雕的层次处理。这种跨界的融合,让玉雕从一门封闭的手艺,转变为开放的艺术表达。
精神之变:从“做活”到“创作”
过去的玉雕师往往一辈子都在重复相似的题材和技法,能超越师傅的少之又少。但现在的年轻玉雕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匠”,而是拥有独立思想的“设计师”。即便他们也曾进入工厂实践,其目的也绝非复制“师傅的套路”,而是为了积累经验,最终走向“独立玉雕师”的道路。
什么是独立玉雕师?就是自己画稿、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完成的玉雕师。他们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这,正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创客”精神。
苗烈创作的《苏武牧羊》就是这种精神的完美体现。那块戈壁料满皮的原石,是他费尽口舌才让料主切下一片的。他说看到料子上的白点,就像看到了夜空中的繁星,这让他想起黑格尔的名言:“一个民族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他将这份哲思完美地融入了玉雕创作中。
我问他为何钟情于薄浮雕,他的回答发人深省:过于厚重的雕刻不仅浪费材料,也不够环保。薄浮雕的魅力,在于在极有限的厚度中营造层次,如同硬币浮雕,于方寸之间创造立体世界。这无疑更考验造型能力。他直言,当下市场推崇的“杀得深”的雕工,很多时候并非“治玉”,而是在“伤玉”。
听完他的阐述,我深有感触。这一代的年轻玉雕师,已经不是在简单地“做工艺”,而是在用心“做玉”——创作有思想、有温度、符合现代审美的玉雕作品。这种转变,正是玉雕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审美之变:从“守艺”到“破壁”
年轻一代玉雕师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在于他们善于用当代语言讲述传统故事。他们的创作不仅延续了玉文化的血脉,更通过创新的表现方式,让古老的艺术形式与当下生活产生共鸣。
温东霖的创作大胆突破传统形制的束缚,融入夸张的造型语言和抽象的结构表现。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用现代审美重新诠释玉雕艺术,精准地连接着年轻群体的审美脉搏。
赵浩则被誉为“影子天才”,他擅长通过巧妙的光影处理,让玉石在不同角度下呈现出变幻莫测的视觉效果。这种对光影的精准把控,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动感与生命力,为传统玉雕注入了当代艺术的活力。
如果说温东霖是从“形”上进行大刀阔斧的现代化重构,那么赵浩便是在“光”与“影”的维度进行微观探索。他们的创作路径各异,但内核一致:用当代的审美语言,与年轻一代对话,同时保持着对玉文化最本真的敬畏。这种既有创新精神又有文化底蕴的创作态度,正是玉雕艺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看着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我常常感慨:玉雕这门古老的手艺,正在他们手中悄然蜕变。他们尊重传统,但不受传统束缚;他们理解材料,但不止于材料。他们不张扬,不浮躁,只是安静地坐在机器前,一刀一刀地雕着。他们做的不是“商品”,而是“作品”;他们不是“工匠”,而是“创作者”。
我相信,未来的玉雕必将更加多元化、个性化。但无论形态如何演变,玉文化的根脉始终在其中流淌。传统不会被丢弃,我们只是在它的沃土之上,浇灌这个时代的语言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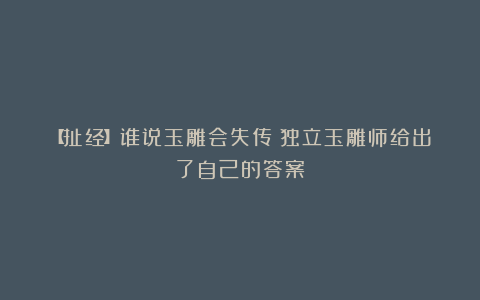
玉雕的未来,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也不在拍卖行的图录中,它就活跃在这些年轻人的指端、凝视的目光和炽热的内心里。只要他们在,玉雕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