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的读法》中犀利地指出了一个文学阅读的普遍现象。“文学研习者最常见的谬误,是直奔诗歌或小说的内容而去,将表达内容的方式抛在一边。这种阅读方式搁置了作品的’文学性’,即面前摆的是一首诗、一部剧或一篇小说,而不是内布拉斯加水土流失报告。文学作品不仅是报告,也是修辞文本。它要求读者阅读时特别精心,对诸如语气、氛围、步调、体裁、句法、语法、韵味、节奏、叙事结构、标点符号、意义暖昧等统称’形式’的元素,要分外留意。”
因此虽然力有不逮,让我们也尽量体味一点布扎蒂讲述故事的形式。场景是医生办公室,时间是那个决定德罗戈命运的四个月的终点,他希望拿到一份体检异常的报告,以此为理由离开城堡。
“您可能不知道,医生,我是误打误撞来到这里的。”德罗戈说道。“亲爱的孩子,所有人都是误打误撞才到这里来的。”医生颇有深意地说道,“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即使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也是如此。”
——起初的对话发生在一个对城堡(体制)仍旧一无所知的人和已被城堡所溶解的人之间。德罗戈隐约心生愧疚,急于辩解;但医生反而极为同情他,并为自己待了二十五年却没有早做打算而懊悔。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懊悔,还是为了开解一个年轻人。
在医生开证明的时候,德罗戈看向窗外,注意到了平时从未注意过的景色。
“他看到庭院里苍黄的围墙伸向了水晶般澄澈的天空中。往围墙外更高的地方望去,还可以看到几座孤零零的塔楼、挂满积雪的歪斜城墙,以及空荡荡的防护坡和小碉堡,这些都是他以前从未注意过的景色。清澈的光线从西侧映照着这些建筑,它们意外地闪耀着一种坚不可摧的生命力。德罗戈此前从未意识到,这座城堡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巨大。他看到在极高处有一扇小窗(也可能是一个射击孔?)朝向山谷。上面应该会有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可能是像他一样的军官,也许还能成为朋友。他也看到堡垒之间的深谷所投射出来的几何形阴影,还看到了悬在屋顶之间的狭窄吊桥、与墙壁齐平且紧闭着的奇特大门,以及陈旧的防护栅栏和其因时间流逝而变形的细长棱角。”
——这是一段静态的环境描写。它有两个鲜明特征:一则,城堡的“苍黄”“孤零零”“歪斜”“空荡荡”与“水晶般澄澈的天空”形成强烈对比,在光线的映照下,城堡显示出“生命力”“复杂”“巨大”等意味着尊严、崇高的特征。它对德罗戈产生的效果就像一个人面对咆哮的大海所经受的震撼一样,也就是,难以无动于衷。二则,从一扇小窗,德罗戈想到还有很多人都未曾认识,再加上看到的“几何形阴影”“狭窄吊桥”“奇特大门”“变形的细长棱角”都代表了还未经历过的城堡的神秘。崇高和神秘,在德罗戈的心中种下难以割舍的种子,即使意识和行动仍执拗地在为脱离做准备,情感却已经未经察觉地放下了生根之锚。
“他看到,在昏暗的庭院里,在灯笼和火把之间,有一些高大又骄傲的士兵们拔出了刺刀。纯净的雪地上,他们排成了一排黑色的队列,像是金属雕塑一般,纹丝不动。军号开始响起时,他们每个人都气字轩昂,庄严肃立。号音在空气中久久回荡,生动嘹亮,直抵人心。”
——这是一段动态的环境描写,出现了士兵。如果说上面的描写只是一些外在的因素,士兵的场景对于德罗戈来说几乎是决定性的。因为他就是士兵,士兵是责任、尊严、团队、精神、荣誉的代名词,是人类群体中最能体现一个共同体可以成就什么的最高代表。城堡只有与士兵合而为一才得以摆脱破败、陈旧、百无一用的境地,号令声、哨声、军号声、脚踩在雪地里的咯吱咯吱声⋯⋯所有这些,赋予城堡以灵魂。德罗戈隐约地开始想到,他的离开令自己成为“孤单的一角”,令城堡成为幻想中的“大圆满”,他们原本可以不必如此。不过此时,一切的心绪都只是在酝酿。
“德罗戈的脑海中浮现出城里的景象,那是一幅苍白的画面——雨中喧闹的街巷、石膏雕塑、潮湿的军营、凄凉的钟声、疲惫不堪的面孔、漫长的午后时光、布满灰尘的天花板。⋯⋯可是在这里,山里的夜晚正在降临,城堡上空的云逐渐消散,好像预示着奇迹将要发生。此时,德罗戈感觉到他的宿命从北方,那个掩映在城墙后面的北方到来了。”
——前面是城堡与自然,这里则出现了城堡与城里的对照。在故事的开头,城里代表着熟悉、家庭、温情、朋友、事业等等与幸福相关联的因素,城堡则是陌生、荒凉、破败、过时、屈辱、孤独的代名词。在医生将要去签字、德罗戈将要获得“解放”的决定性瞬间,上述对照却发生了逆转。城里变得苍白,城堡上空“好像预示着奇迹将要发生”。理性无从解释德罗戈感觉到的宿命,就像在解释学循环中,不可能永远在同一个层次上原地打转,它需要一个突破口,一个光之瞬间。
“医生,”德罗戈几乎是结结巴巴地说,“我的身体状态很好。”
“我知道的。”医生回答道,“您有什么想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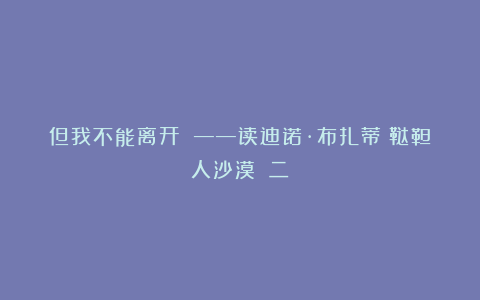
“我很好。”德罗戈重复道,几乎辨认不出自己的声音了,“我的身体状态很好,我想留下来。”
“留在城堡?您不想走了?发生了什么?”
“我说不上来,”德罗戈说,“但我不能离开。”
“啊!”罗维纳惊呼着向他走了过来,“如果您不是在开玩笑的话,我真的很高兴。”
“我没有开玩笑,我没有。”德罗戈说道,他觉得对方的兴奋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别样的压力,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幸福感。“医生,把那张证明扔掉吧。”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在我看来,这是《鞑靼人沙漠》最令人回味不已的一段对话,我感受到了一种德罗戈所体验的瞬间附身的幸福。让我们暂时抛开城堡代表体制或者体制代表规训等等外在视角,回到人的存在。
海德格尔说,我们以为最熟悉自己的时候,其实离自己的存在最远;反之,当看到一个陌生的自己,那是离存在最近的时候。
前一种情况就是假设回到城里的德罗戈,是抛却作家身份在保险机构任职十五年的卡夫卡,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结婚生子、朝九晚五的“常人”生活。之所以离存在最远,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现象的我”之上还有一个“本体的我”,我们忙于生存,生存以外的事情既没有时间关心,也并不真的关心。
后一种情况则是决定留在城堡、并立即体会到“一丝幸福感”的德罗戈,是下班后回到地下室小屋闭门不出的卡夫卡,是突然在某个陌生的瞬间意识到我们本质上必须过“常人”的生活,但在“常人”之上“此在”倔强地将“去存在”作为毕生追求和幸福得以可能的要素。这个陌生的瞬间可能是突遭一场大病(《思想录》陪伴在侧两个月),目睹一个路人毫无缘由的嚎啕大哭(失业、绝症、被离弃、亲人的死亡、投资的巨大失败),听闻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自杀(原因不会比上面更多),奔跑或漫步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在一个咖啡馆被《死神与少女》或者《哥德堡变奏曲》中的某个和弦击中,从母亲暗淡的眼神中突然发现自己对她的伤害⋯⋯等等。
德罗戈之所以“结结巴巴”,是因为他对自己这种转变的震惊,他难以相信自己。意识尚未考虑清楚,灵魂已然被击中。所以德罗戈说不上原因,但却已经决定了。这种决定体现了海德格尔的“决断”和克尔凯郭尔的“纵身一跃”之观念的真理性。如果说存在幸福,只有德罗戈决定不能离开的时刻才是幸福的,其后的二十年,他所体会的无非是幸福的结果,尽管结果不一定是“常人”的幸福。
有关《鞑靼人沙漠》,布扎蒂说过:“这部小说的灵感来自我以前做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夜间编辑工作,我经常有这样的想法,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将永无止境地消耗我的生命,我想,这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想法,尤其是那些在城市中按部就班生活的人。将这种想法转化为一个奇幻的军事世界对我来说几乎是出于本能。”
我们会习惯于、甚至爱上一个奇幻故事包裹下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不甘心仅仅过一种季孟之间的生活。我们不仅渴望、而且通过布扎蒂相信:一种德罗戈式的幸福是可能的。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