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嵩,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熊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犹太人阿利亚是全球移民史的重要议题。以“阿利亚运动中的区域不平衡与族群经验异同”为问题导向,依托Scopus数据库,借助文献管理器软件和统计工具SPSS,对55篇关于欧亚非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学术论文进行系统性综述。研究发现,21世纪国际学界更多关注以色列建国后的阿利亚现象,并逐步突破以犹太复国主义为中心的单一框架,转向跨国、跨区域分析;推拉理论依然是分析阿利亚动因的主要路径,强调多重动力与阻力对不同时期阿利亚运动的交互作用;移民在社会适应中面临的挑战既有普遍性,也因原有阶层背景与文化差异而呈现多样性;来自不同离散地的犹太群体在以色列形成一种文化共生而非单向同化模式。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在知识生产中的持续影响,亚非犹太人阿利亚和中东冲突带来的难民等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系统性综述将定量分析与史学判断相结合,为全球史中跨区域、跨语言议题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创新。
关键词:阿利亚;犹太人;移民;系统性综述;欧亚非;以色列
阿利亚运动通常是指犹太人移民至以色列(或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现象,其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承载了犹太民族复兴、宗教信仰实践、政治战略实施以及文化认同塑造等多重意义,因而是中东和以色列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且复杂多维的主题。19世纪末以降,欧亚非的犹太人阿利亚运动不仅践行了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圣地以色列的宗教理想,深化了犹太民族情感,推动犹太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且反映了全球移民史的多样化特质。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超越传统的单一的民族主义叙事,运用跨区域、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欧亚非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驱动力、移民的艰辛历程、与原籍国和以色列的互动关系。本研究以“阿利亚运动中的区域不平衡与族群经验异同”为核心问题,运用系统性综述的研究方法,依托Scopus数据库,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欧亚非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研究进行科学分析,通过对犹太人阿利亚的动因、移民经历的阻力和移民在适应新社会与身份认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结构化分析,深入认识阿利亚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揭示国际学术界犹太移民史研究的新动向,深化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
何为“阿利亚”
“阿利亚”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现象和使用的概念,始于20世纪初。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实背景下,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伯来大学犹太社会学系的奠基者阿瑟·鲁平率先使用“阿利亚(makes aliyah)到以色列地”和“移民(immigrates)到美国”以区分两类移民,为其后的犹太裔学者将“移民到巴勒斯坦”变成一种独特的犹太移民叙事——“阿利亚”——奠定了最初的术语基础和学术基础【1】。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包括雅各布·莱辛斯基、阿里耶·塔特考威尔、大卫·古列维奇、撒母耳·诺亚·艾森斯塔特等在内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沿着阿瑟·鲁平开辟的道路,开始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强调“移民巴勒斯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人类迁徙,”并从民族性界定阿利亚,认为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是一种受犹太民族主义驱动、以建立犹太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独特移民现象”【2】。他们定义阿利亚专指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突出地将犹太民族认同作为意识形态动机,因此,阿利亚与其他民族的移民无关。这种定义将阿利亚与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结合,成为其后以色列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之一。例如,1991年以色列社会学家埃利泽·本·拉斐尔在研究以色列历史时,延续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强调阿利亚是犹太人向以色列的移民浪潮,由“犹太复国主义——一种世俗民族主义推动”【3】。
与上述定义不同,1994年,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希洛提出,不应该把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行为都称为阿利亚。她对1882年俄罗斯犹太人阿利亚浪潮与1882年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计划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尽管他们都是犹太人且目的地都是“以色列地”,但却有本质不同:前者是为了逃离屠犹暴行的自发移民,不应被视为阿利亚;后者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出于对罗马尼亚犹太人困境的关注”和寻求一个救助犹太社群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阿利亚。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阿利亚的首要目标,在以色列建国前是“拯救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转为“当下的国家建设”【4】。尽管希洛与以色列学术界的主流叙事一样,强调阿利亚的民族性特征和阿利亚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诉求的密切关系,但是,她严格区分犹太人移民的方式和目的,将阿利亚运动重新定义为基于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有组织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地的现象,且其中蕴含着政治、经济和国家建设等现实考量,体现了当代阿利亚叙事与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差异。
21世纪初,以色列海法大学历史学教授古尔·阿罗伊再次聚焦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人移民美国现象,重新诠释阿利亚的定义,指出阿利亚是犹太人移居圣地的活动,包括永久定居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短期旅行、观光等现象;阿利亚的动机不局限于宗教和民族情感,还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5】。尽管以色列学者对阿利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是,阿利亚是一场以圣地为目的地的迁徙现象,其背后有多重动机,得到中外学界的普遍认可【6】。
在重新界定阿利亚内涵的同时,21世纪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焦点由以色列建国前转向以色列建国后,重点观察当代欧亚非犹太人的阿利亚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非犹太人持续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和规模前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政府接纳了大批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境内犹太人口为716700【7】。到2024年1月1日,以色列犹太人口超过7427000,占世界犹太人口的44.3%【8】。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在迁移过程中面临经济、语言、文化的挑战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移民政策的复杂态度,这些共同塑造了70余年来犹太人阿利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学术界围绕以色列建国后的欧亚非阿利亚运动,主要聚焦于三个问题:阿利亚案例与阿利亚的多重动因,移民在政治、外交和法律等领域遭遇的困境与阻力,以及不同犹太群体在融入以色列社会和身份认同上经历的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揭示了阿利亚运动中的区域不平衡与族群经验异同。
系统性综述作为一种方法
系统性综述(systematic review)是一种基于明确方法论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旨在通过透明、可重复的标准化流程,对特定研究问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全面检索、筛选、评估与整合,以减少主观偏倚并形成系统性证据链【9】;其核心特征包括预先制定清晰的纳入/排除标准、采用结构化检索策略、对文献质量进行严格的偏倚风险评估。相较于传统依赖学者主观叙事的叙述性综述,系统性综述通过流程透明化显著提升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与可靠性【10】。这一方法起源于医学领域,现已拓展至多学科,尤其适用于需整合碎片化知识、跨时空比较分析的研究内容。21世纪,国际学术界将该方法应用到移民与族群、社会融合与认同建构等研究领域。例如,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社会史学家雷·辛和玛丽亚·克莱桑,通过系统性综述,梳理1950年至2013年间美国学界关于“种族居住融合”的研究,揭示了该议题研究范式由注重跨族群交往与社会互动的多维整合(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逐步转向仅以人口比例进行衡量的数值整合(numeric integration)的趋势;研究重点从“人们在生活中是否真正交往、是否互相接纳”转向了“居住区域内各族群的数量比例是否均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量化趋势【11】。系统性综述之所以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因其具有双重功能。其一,用于归纳整理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的文献;其二,作为具有明确程序与方法规范的综合性研究范式,强调研究的透明、可重复性、标准化和减少主观偏倚,尤其适合对跨学科、跨时空背景下复杂问题的比较研究与宏观分析。而该方法,无论作为文献整理工具,还是研究范式,在我国学术界处于起步阶段【12】。
在历史研究中,系统性综述的应用非常必要。传统的历史文献综述常受限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好、文献可及性、语言壁垒或意识形态等影响,虽然可在短时间内对少量代表性成果进行主题归类与评价,但是在面对跨时空、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分析和知识碎片化问题时,容易产生关键信息遗漏、解释偏误或结论碎片化,削弱研究的整体性与客观性。阿利亚,作为一个全球人口迁移现象,长期以来成为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新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却高度分散,呈现出语言多元、地区分散、研究路径多样等特征,存在研究碎片化与难以比较的状况。引入系统性综述方法,通过预先设计的全面检索策略、结构化的文献质量筛选评估,以及对文献内容的编码建构,能够系统性整合分散的研究成果,识别传统综述中可能被忽视的叙事冲突或隐含关联。因此,本研究以“阿利亚运动中的区域不平衡与族群经验异同”为问题导向,以系统性综述为研究范式,试图通过减少“选择性引用”避免结论失真,通过严谨的偏倚评估与证据综合,为犹太移民史研究提供更具可信度的知识图谱,清晰揭示既有研究的边界与未来探究的方向,从而为该领域的学术对话建立可验证的方法路径,推动犹太史研究在透明度与严谨性上的方法论创新。
研究者选用由荷兰爱思唯尔出版社运营的Scopus数据库作为核心检索平台,它是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学术数据库之一,收录了超过8700种涵盖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期刊。初步检索结果显示,Scopus中与犹太研究、阿利亚、族群迁移等主题相关的学术文献数量充足,不仅包括《种族与移民研究杂志》(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离散》(Diaspora)《以色列研究》(Israel Studies)、《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和《以色列历史杂志》(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等专业期刊,还拥有多语种、多区域背景的交叉研究成果【13】。相比其他数据库,Scopus更有利于捕捉多语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尤其有助于涵盖非英语语境中被相对忽视的研究文献,从而拓展阿利亚议题涵盖的范围。
确定数据库后,研究者以CHATGPT为辅助工具构建初步检索策略,并在此基础上由研究者加以修订与优化,以确保术语选择的合理性与逻辑结构的严谨性;最终形成的检索公式与关键词如下:[TITLE-ABS-KEY (Aliyah OR “Jewish migration” OR “Zionist migration” OR “Jewish emigrat” OR “Jewish return migration” OR “Jewish repatriation” OR “Jewish immigra*” w/5 Israel) AND TITLE-ABS-KEY(Israel OR Palestine OR Zion OR “Eretz Yisrael” OR Europe OR Africa OR “Middle East” OR Soviet OR “Latin America”)]。依据此公式和检索词,对Scopus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80篇研究全球阿利亚运动的学术论文。
为确保学术论文的相关性和学术性,在文献处理器Zotero【14】和检索式辅助下,对海量文献进行了多维度梳理与分析,结合全面筛选与分层聚焦的方法,提炼出四项筛文标准。第一,论文必须以欧亚非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为主题;第二,论文直接探讨阿利亚的驱动因素,分析历史、社会、文化等背景;第三,论文必须分析移民原籍国或者目的地政府的政策及其影响;第四,论文必须基于案例和实证研究,探讨移民的文化适应、语言习得、社区建设等问题,避免泛泛的理论性讨论。四项标准的最终目的是梳理出与阿利亚浪潮的动因、过程以及移民适应等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之所以聚焦欧亚非犹太人的阿利亚运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地区的犹太社群不仅参与了最早的阿利亚浪潮,而且一直是移民主力军;第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犹太社群持续面临迁徙和社会适应的挑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两位研究者共同参与筛文。首先,根据四项筛选标准对180篇论文的标题、关键词和摘要进行两次筛选,留下166篇涉及欧亚非犹太人阿利亚运动的论文。随后,对166篇论文进行两次全文筛选,间隔7天。然后,剔除不符合标准的文献,包括50篇未聚焦阿利亚、47篇未深入分析政府政策或外交障碍、14篇只作理论探讨而无实证研究的论文。此外,6篇论文因意见分歧经重新筛选,Kappa值【15】为0.92。最终,55篇符合标准的研究论文被纳入分析体系(见图1)。其中,英语论文49篇,德语、法语、俄语、土耳其语、波兰语和捷克语论文各一篇。鉴于最早的论文由以色列社会学家艾姆达·奥尔发表于2003年【16】,本研究将反映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以色列建国后欧亚非阿利亚运动的讨论。
根据55篇论文聚焦的不同犹太群体,将其分为四个群组:沙俄/苏联/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奥地利、德国等;非洲;亚洲。
在众多犹太群体中,苏联解体后的犹太移民浪潮备受瞩目(10篇论文)。巴伊兰大学弗拉基米尔·哈宁博士提出,从1989年底开始,超过120万移民进入以色列,其中约85%来自苏联,这一波大规模移民潮,不仅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讲俄语的犹太中心”,而且对以色列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在促进以色列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加剧了社会政治争议,使相关议题复杂化【17】。
尽管聚焦非洲阿利亚的研究较少(6篇),但其犹太社群因涉及种族、宗教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和多元化挑战,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耶路撒冷谢克特犹太人研究所的玛尔瓦·沙罗夫·玛洛姆博士,聚焦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经历,研究以色列国家建设和治国方略背后的种族和宗教意识形态,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色列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在质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犹太身份。这种质疑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以色列的公民身份、教育机会和最终合法性,并为国家采取措施摧毁他们在以色列的犹太传统、社区结构甚至家庭提供了理由。”【18】这种批判犀利且直击要害。
围绕亚洲阿利亚的讨论最为薄弱(3篇),主要集中在也门、伊朗和印度,其阿利亚始于以色列建国后。本-古里安大学历史学教授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指出,以往研究在观察亚洲移民在新生犹太民族国家的经历时都强调了以色列的核心作用,然而新的研究认为,“以色列只是犹太人大逃亡的一个参与者,阿拉伯国家、中东的大英帝国、北非的法兰西帝国、美国和国际犹太组织(尤其是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种复杂性,在也门、伊拉克、利比亚犹太人的案例中,尤为明显。他试图超越以往研究强调以色列的“救赎”和犹太人被原籍国“驱逐或欺骗”的叙事,对大规模移民“进行一种新的、淡化意识形态的、更具历史和批判性的审视”【19】。
基于55篇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和观点,结合SPSS【20】与WPS作图工具,制作图2、图3和图4,用结构图示方式,呈现对国际学术界围绕以色列建国后欧亚非阿利亚运动的动因、阻力以及移民在以色列所经历的挑战三个维度问题的结构化、系统性分析。
以正文图2为例展示SPSS所制作的草图
犹太人阿利亚的动因
以色列建国后,由不同离散地犹太人汇聚成的阿利亚浪潮,是由推力、拉力与犹太人自身能动力共同编织的一场持续且复杂的人口迁徙(图2)。21世纪的学者们对犹太人阿利亚的历史与现实的剖析,逐渐超越了单一的“逃离迫害”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将其描绘为与民族理想、现实利益及国际局势互动的系统工程。
在学者们的视野里,对抗反犹主义与改善经济状况是促使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在反犹主义盛行的发达地区,逃离迫害的驱动力更强;而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改善生计的诉求更为重要。必须指出,尽管反犹主义作为犹太人阿利亚的驱动因素被提到的次数最多,但是往往都作为研究背景出现,学者未提出新的阐释。
经济因素对移民决策发挥重要且复杂的作用,既是促使移民的关键动力,有时也成为阻碍。在以色列建国前,经济因素常常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奥地利社会学家加布里埃莱·安德尔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形势对奥地利犹太人阿利亚发挥了重要影响;对于陷入经济困境的犹太群体,巴勒斯坦不仅为其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而且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机会【21】。同样,海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阿萨夫·沙米斯认为,经济因素在第一次阿利亚浪潮时期(1882—1903年)和第二次阿利亚浪潮时期(1904—1914年)尤为显著,许多犹太人以农业工人的身份来到巴勒斯坦,在建立基布兹和其他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2】。而悉尼大学犹太史学家苏珊娜·拉特兰认为,以色列建国后经济因素可能抑制移民意愿,苏联犹太人身上便体现了这种矛盾:许多人选择西方国家而非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生活“更艰苦”【23】。因此,经济因素的具体影响,取决于移民的处境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原籍国和目的地的经济环境。
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常常受到其内心对圣地的宗教归属感的驱使,是其自主选择与主动行动的体现。犹太教经典对“应许之地”的神圣叙事与耶路撒冷在离散犹太人心中的象征地位,为阿利亚注入了深厚的文化与精神意义。正如奥地利学者安德尔所指出的,部分虔诚的犹太家庭将迁往以色列地视为履行神圣使命的过程;在其移民决策中,宗教考虑最重要,甚至“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保持距离”而自发移民【24】。同样,加州大学人类学家奥马尔·布姆的研究表明,摩洛哥南部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是基于自身对其历史与巴勒斯坦之联结的想象,而这种历史记忆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更易争取摩洛哥犹太人的认同,因而赋予阿利亚更深层的文化意义【25】。而巴伊兰大学博士多里特·约瑟夫强调,20世纪30年代中欧犹太女性移民巴勒斯坦,并非仅仅为了躲避迫害,而是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其使命和目标,她们从“犹太复国主义元叙事”中找到移民的正当性和价值感【26】。这些研究表明,尽管学术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意见不一,但是对阿利亚动因的分析已经从单一的意识形态驱动,即政治驱动的框架,转向关注移民个体如何主动利用历史叙事与意识形态建构其行动逻辑。
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政府通过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塑造,对全球犹太人的移民决策施加了广泛影响,这两个方面的举措成为阿利亚的主要吸引力。玛洛姆博士强调,1950年以色列《回归法》作为一项基本国法,为犹太群体的大规模移民提供了制度保障【27】。以色列外交官雅科夫·利夫内与阿里尔大学历史学教授约西·戈尔茨坦,聚焦20世纪50年代苏联犹太人的命运,指出以色列政府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成立移民组织纳提夫(Nativ),缓慢推动犹太人移民;在1955年苏以关系恶化后,成立专门支持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机构(Bar),通过多种渠道向国际社会传播苏联犹太人受压迫的信息,“让我的人民离开”成为以色列推动苏联犹太人移民行动的重要口号。迫于以色列的努力和国际社会压力,1956年苏联政府表态支持以“家庭团聚”为目标的移民,将近有五万犹太人离开苏联,其中99%阿利亚到以色列【28】。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利奥拉·霍尔柏林博士,聚焦以色列政府如何通过塑造和构建历史记忆这种更为隐秘的手段来吸引移民,指出以色列政府通过1962年和1982年两次纪念“1882年第一批欧洲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活动,将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历史意识形态化,使其符合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框架,向全球犹太人表明离散中的犹太人“回归故土”和“建立民族家园”的可能性【29】。
然而,以色列政府的移民政策并非向全世界的犹太人完全开放。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扬·西奥多·祖尔彻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移民机构(Sohnout)以“社会职业、健康和年龄”为筛选标准,让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优先来到以色列【30】。这表明,阿利亚运动不仅受到新生的犹太民族国家的吸引,而且实实在在推动了其国家建设。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扬·西奥多·祖尔彻的论文标题及摘要
在跨国史兴起的背景下,英国托管当局对犹太人的移民政策【31】、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努力【32】、离散地犹太社群的经济援助、美苏等国的政策和干预等国际因素【33】得到关切。具体而言,土耳其国立大学博士穆罕穆德·阿里·杜兰发现,英国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数量在一战后显著增长;但是,当阿犹冲突爆发后,英国立刻采取限制犹太移民的措施【34】。针对二战时欧洲犹太难民未能成功抵达巴勒斯坦的经历,佛蒙特大学历史系的苏珊娜·施拉夫施泰特指出,意大利法西斯遣返犹太移民的政策与国际犹太救援行动的迟缓,共同阻碍了意大利难民的阿利亚【35】。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指出,二战后,美国犹太人,通过犹太事务局和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资助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前往以色列。
本古里安大学历史学教授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的论文标题及摘要
悉尼大学历史学家苏珊娜·拉特兰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她聚焦20世纪50年代苏联犹太人移民运动中的“退出现象”,在离开苏联的犹太人中,有些选择在维也纳中转站改变目的地,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而非以色列,此时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美国将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移民列为难民,积极协助苏联犹太人申请赴美签证,并在其移民过程中提供帮助,这使得许多苏联犹太人认为美国经济机会多,生活更具吸引力,进而选择前往美国,而非以色列;彼时国际上的犹太组织强调“自由选择”观念,也为苏联犹太人选择前往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思想和舆论支持。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美国不再给苏联犹太人难民身份,减少对其经济援助和移民配额,使其前往美国的难度加大;同时,犹太组织的立场也发生转变,认为以色列更需要犹太移民【36】。因此,犹太移民现象不仅是犹太人的历史,而且是全球力量博弈、各国政策互动、美国与犹太组织合作的产物,凸显了跨国因素对犹太移民浪潮施加的重要影响。
综上,以色列建国后,欧亚非犹太人阿利亚运动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集体迫害和经济窘境构成的原籍国生存危机,是犹太人移民的最直接推力;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以色列吸引移民的政策是最主要的拉力。同时,离散犹太人并非被动受力的个体,其代代相传的对“应许之地”的宗教想象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始终为这场迁徙注入内在生命力。在此过程中,全球犹太组织搭建的救助网络如隐形桥梁,冷战期间美苏对中东地区的争夺则成为地缘杠杆,共同推动移民决策。
犹太人阿利亚遭遇的阻力
犹太人的阿利亚,不仅在民族国家建立前受到种种限制,而且在以色列建国后,依然受到不同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见图3)。
学者们的共识是,犹太人阿利亚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来自原籍国对其公民移民以色列的严格管控,许多国家通过限制护照发放、禁止财产转移、采取敌对态度阻止犹太人离开。日内瓦大学哲学博士拉卢卡·马特奥克指出,罗马尼亚政府在二战结束后的限制政策,使许多犹太人不得不以非法移民方式进入以色列【37】。苏联也有类似情况【38】。俄罗斯哲学博士塔季扬娜·梅德韦杰娃等指出,当苏联与以色列外交关系因中东局势而紧张时,直接暂停向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颁发护照【39】。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弗里德曼提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领导人,“将想要离开苏联的犹太人视为’工人天堂’的叛徒”【40】。可以说,国家主权与移民控制在犹太移民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促使学界进一步探讨国际移民政策、民族身份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殖民主义和大国竞争使犹太人的移民过程更加复杂。美国社会史家劳伦·班科发现,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当局鉴于阿拉伯人的反对,曾禁止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并建立了一套监控和管理“不受欢迎”移民的制度,“使个体和群体移民面临诸多困难,甚至被禁止”【41】。同样,捷克民族史学者布兰卡·苏库波娃指出,捷克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地区最主要的困难是英国托管政府所发放的许可证数量不足,难以满足移民需求【42】。梅德韦杰娃博士等研究者指出,当美苏在中东博弈时,以色列卷入其中,与社会主义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导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犹太人的移民渠道受阻【43】。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注意到,1956年中东战争之后,埃及、伊拉克的犹太人受到迫害与暴力攻击,或被驱逐,或以难民身份寻求移民以色列【44】。可见,殖民主义、冷战地缘政治与移民控制在阿利亚运动中处于动态关联,并会迟滞特定犹太群体的阿利亚。
以色列主流社会对境外犹太人身份认定的争议,涉及族裔差异、宗教观念与实践,这种争议本身也成为移民的阻力。以法国学者祖尔彻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尽管1950年《回归法》正式确立了向所有犹太人(无论是否信教)及其非犹太家庭成员开放移民的政策原则,但是1952年开始以色列实行了选择性移民政策。以色列首席拉比和宗教事务部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定具有权威性,只有获得他们的认可,才有可能被认定为“犹太人”并获得移民资格。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认为选择性移民政策阻碍了犹太人前往以色列,并促使以色列政府于1954年底以“从船到村”政策取而代之,所有符合《回归法》规定的移民可自由入境【45】。玛洛姆博士指出,以色列对非洲犹太移民的身份认定存在争议,因此,以色列通过向贝塔犹太人(Beta Israel)提供以阿利亚为主题的培训,“重新定义犹太人内涵,影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阿利亚之旅。”由于非洲犹太社群的经济与知识水平普遍较低,以色列政府遂利用修正后的《回归法》限制其移民【46】。这种身份认定争议和以身份定位作为限制移民的工具,皆暴露了以色列国家构建过程中犹太人及以色列社会“犹太性”的内在矛盾。
以色列建国初期接收移民的能力有限,难以提供足够的住房、工作机会和基本服务,这些也是制约移民规模的重要因素。波兰历史学家艾娃·韦格日恩指出,尽管以色列《回归法》宣称所有犹太人都有权移民,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困境迫使其优先接纳有助于国家建设的群体,如青年与熟练工人,而将年长和需要照护的移民视为“国家财政的负担”【47】。祖尔彻也提出相似看法。由于接收移民能力有限,以色列试图筛选移民,遭到批评后,“犹太事务局采取了模棱两可的行动”:一方面,继续参与和推动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另一方面,将自由入境的新移民安置在“发展镇”和边境地区,限制他们迁徙至其他地方,从而违背了“自由移民”的原则【48】。英国阿伯丁大学亚历山德拉·塞科林博士认为以色列针对特定群体制定了筛选机制,该机制将伊朗犹太人归类于“非紧急”犹太人,并排除在50年代初“拯救难民”行动之外【49】。以色列移民局的官僚主义和办事效率低下也被学者诟病为“阻碍移民及其定居”【50】。
综上所述,学界对阿利亚的研究逐渐从民族主义叙事转向强调移民政策、国家主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并重视分析原籍国限制移民的政策、接收国有限的接收能力、围绕移民犹太人身份认定的争议、严格筛选机制的阻力等方面,这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犹太人阿利亚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及其对犹太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犹太移民的社会适应
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犹太移民在适应以色列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图4所示,学者们发现,犹太移民在以色列的适应路径较为复杂:希伯来语习得与就业困难是所有移民面临的基本问题;宗教实践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催生出某些群体的特殊困境;而原籍国文化的代际传承与以色列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使犹太身份认同成为移民经历中的关键议题。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移民群体发展出不同的文化融入策略,以应对从原籍国到以色列、以色列社会结构不断重塑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形成了既扎根过去又面向现实的双重认同结构。
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德国等国家的犹太移民采取多种策略融入以色列。以色列历史学家马科斯·西伯尔和波兰历史学家韦格日恩都指出,这些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后,需要面对语言、职业、阶级的转型以及社会隔阂带来的问题【51】。据玛丽华盛顿大学教授詹妮弗·格鲁克里奇的研究,为提升适应能力,移民群体自发组织行前的语言和职业技能培训【52】。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根纳迪·埃斯特赖克指出,波兰犹太组织允许外国犹太救济组织介入移民事务,以促进阿利亚的顺利进行【53】。根据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学博士米兰·拉多万诺维奇的研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南斯拉夫【54】。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博士拉凯菲特·扎拉希克,聚焦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神经学家,发现他们作为难民到达巴勒斯坦后,面临工作岗位不足以及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社群的不信任态度等挑战,但这些神经科医生通过成立专业学会、调整科研方向使之适应巴勒斯坦环境与人口特点,其专业能力为以色列建国后医疗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5】。
来自苏联、俄罗斯的移民,与其他欧洲移民的社会融入路径,略有不同。梅德韦杰娃等指出,他们在以色列同样遭遇了多重挑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语言障碍、职业资历认证困难等阻碍了“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社会融合”,但是,良好的教育经历和技术专长,使苏联移民比其他移民群体更容易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他们中许多人进入以色列高科技领域就业【56】。哈宁博士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来自苏联的俄裔移民社区,包括约300个得到政府正式认可的社区自治协会;这不仅反映出职业优势催生了俄罗斯犹太人的自治能力,也反映出以色列社会对多元文化和社会异质性的高度接纳。苏联移民“在安置过程中获得的相对自治促进了新移民群体内部治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发展”【57】。
整体上,欧洲犹太移民,在融入以色列社会的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调适与共生模式:既通过本土化策略实现文化适应,又依托原籍国遗产维系文化记忆,呈现了文化再生产的多维特征。德国文学博士詹妮弗·格鲁克里希指出,德裔犹太移民既将席勒、贝多芬、歌德等德国文化符号纳入身份谱系,又通过《诗篇》吟诵和安息日仪式强化犹太文化认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德国遗产和犹太遗产都是我们的”,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核心【58】。土耳其犹太移民通过民间舞蹈的形式,既延续土耳其传统,又在以色列民族化过程中建构新犹太身份认同【59】。这些犹太群体,通过文学、艺术与日常实践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共生模式,并在双重文化认同的张力中完成了新犹太身份的重构,而这种双重认同模式又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
尽管非洲犹太移民的社会融入面临宗教、文化与种族多重挑战,但他们仍表达了强烈的犹太认同和对独特“犹太性”的坚持【60】。玛洛姆博士发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贝塔社群,在移民前通过“希望(Tikvah)”犹太社区中心的希伯来语培训和宗教仪式学习,以期“以色列化”,但是定居以色列后,因其独特的宗教仪式而受到主流社会对其犹太正统性的质疑,他们被以色列政府和主流社会认定为“不够犹太”的群体,并陷入就业难和经济贫困的窘境,“其公民权利和社会融入遭遇严重挑战”【61】。这种结构性矛盾催生出他们独特的融入路径。德国汉堡大学索菲亚·德格-穆勒博士等,强调贝塔群体在保留独特的祈祷仪式、传统音乐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同时,其祷告词和宗教仪式也逐渐吸纳了拉比犹太教的元素【62】。这种文化融合,既是贝塔犹太人表达犹太归属感的方式,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适应过程中为获得身份认同所进行的调整与妥协。
耶路撒冷谢克特犹太人研究所的玛尔瓦·沙罗夫·玛洛姆博士的论文标题及摘要
亚洲犹太移民,特别是伊朗和印度的犹太社群,既保留了原有宗教与文化特色,也逐渐融入了拉比犹太教传统,丰富了以色列社会文化融合的多样化特征。部分学者关注到,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在以色列普遍面临经济贫困和社会边缘化,格利琴斯坦称之为“赤贫的难民来到了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得不忍受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困难【63】。祖尔彻指出,以色列政府的移民政策倾向于优先接收青壮年男性,造成许多伊朗犹太家庭的分离;统一安排定居点的做法,导致他们难以凭自己的技能在定居点附近找到适合的工作,进一步加大了他们适应新社会的难度【64】。塞科林博士指出,伊朗犹太社区领导力较弱,相较于其他移民群体,在以色列面临更大的生存困难【65】。印度裔学者阿莎·苏珊·雅各布也认为,印度裔犹太人虽对阿利亚有强烈认同,但抵达以色列以后仍普遍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归属感的缺失等问题【66】。
然而,本-古里安大学社会学家葆拉·卡巴洛反对上述观点,认为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积极建立正式组织、采用民主运作方式、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并批评移民政策,这些做法严重影响了以色列的移民政策。这些犹太人在适应的过程中展现出积极的能动性,因此,他们并非“被动、依赖性强、没有话语权”的群体【67】。
总而言之,各犹太移民群体在适应以色列社会的过程中,都展现了对原籍国和以色列的双重认同,但是,他们在语言障碍、职业挑战和生活方式差异等方面表现出共性的同时,也因为受教育程度、经济基础和宗教实践的不同,其被接纳程度和适应速度又呈现出差异。大体看来,欧洲移民群体能够积极应对挑战,迅速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而来自埃塞俄比亚、南非、伊朗和印度等国家的移民群体更依赖精神信仰的支撑和以色列政府宽松的政策,融入新环境显得相对缓慢。这些不同的适应模式揭示了以色列的多元文化特征和移民社会融入的复杂性。必须强调,他们共同面对的是一个按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标准建立和治理的以色列社会,不同离散地犹太群体融入以色列的过程并非单向度的同化,而是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文化共生模式。以色列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社会结构和族群关系在阿利亚运动中经历了持续的重塑。
结 语
以系统性综述为方法,对学术界围绕欧亚非阿利亚运动的研究成果进行跨语言、跨地域、跨学科的结构化分析,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新尝试。相较于传统的叙述性综述,系统性综述强调问题导向、检索过程的透明性与可复制性以及结论的结构性、可视性,其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在面对大量碎片化的文献时构建清晰的知识图谱,更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成果重建和学术对话的研究范式,先构建分析框架,再进入史料或者文献评估与论证。因此,该研究范式兼具文本研究和问题研究的特征,可以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生成机制。
本研究正是围绕“阿利亚运动中的区域不平衡与族群经验异同”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在呈现以色列建国后不同地区犹太人阿利亚之共性与差异的基础上,揭示当前国际学术界对跨区域犹太人口迁徙的研究框架依然遵循由鲁道夫·赫伯尔(1938年)与埃弗雷特·李(1966年)系统总结的推拉理论【68】;同时,也揭示出当前犹太移民史研究中的区域偏好与失衡——欧洲犹太人的经验仍占主导地位,亚洲与非洲犹太移民的处境则相对边缘化。这种倾向不仅源于史料分布和不同犹太群体的历史参与程度,也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在知识生产中的持续影响,导致21世纪以来中东冲突影响下的亚、非犹太人阿利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依然被忽视,也导致对以色列社会异质性、“犹太身份”的多重性及结构性张力等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
当然,系统性综述在历史学的运用仍面临一定挑战,包括文献分类标准的界定、非英文文献收录的局限,以及文献筛选标准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等。这些问题提示历史学者在应用该方法时需作调整,例如,反思文献分类逻辑、拓展文献获取渠道,并保留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即承认其价值取向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同时,维护历史研究固有的解释空间与批判视角。未来若能更充分地将定量的文献分析与定性的史学判断相结合,将为全球史中跨区域、跨语言议题提供一种结构化研究范式和方法创新,为历史学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在此致谢!)
【1】阿瑟·鲁平:《犹太社会学》(Arthur Ruppin,Soziologie der Juden),柏林:犹太出版社1930年版,第112~113页;参见古尔·阿罗伊:“两种史学:以色列史学和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美国,1881—1914”(Gur Alroey,“Two Historiographies:Israeli Historiography and the Mass Jewish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881—1914”),《犹太季刊》(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第105卷第1期(2015年12月),第110~111页。
【2】他们的观点见以色列海法大学历史学教授古尔·阿罗伊的研究,参见古尔·阿罗伊:“两种史学:以色列史学和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美国,1881—1914”,《犹太季刊》第105卷第1期(2015年12月),第110~115页。
【3】埃利泽·本·拉斐尔、斯蒂芬·沙罗特:《以色列社会的族裔、宗教和阶级》(Eliezer Ben-Rafael and Stephen Sharot,Ethnicity,Religion and Class in Israeli Societ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4】玛格丽特·希洛:“1882—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移民政策”(Margalit Shilo,“The Immigration Policy of the Zionist Institutions,1882—1914”),《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第30卷第3期(1994年7月),第599、6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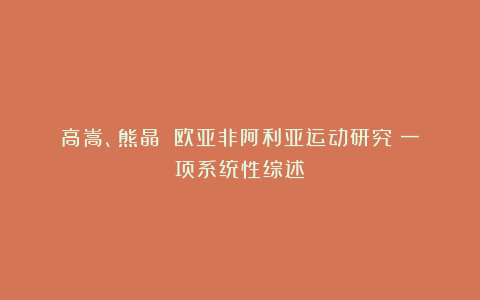
【5】古尔·阿罗伊:“两种史学:以色列史学和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美国,1881—1914”,《犹太季刊》第105卷第1期(2015年12月),第99~129页。
【6】中国学者认为阿利亚泛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活动。参见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潘光:《以色列国在此奠基──试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1期,第159页。
【7】“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人口(1517年至今)”(Jewish &Non-Jewish Population of Israel/Palestine 1517—Present),犹太虚拟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ewish-and-non-jewish-population-of-israel-palestine-1517—present,2024—05—09/2025—04—17。
【8】“重要数据:1882年至今全球犹太人口统计情况”(Vital Statistics:Jewish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1882—Present),犹太虚拟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ewish-population-of-the-world,2024—01—01/2025—04—24。
【9】朱利安·希金斯、萨莉·格林:《科克伦干预措施系统综述手册》(Julian PT Higgins and Sally Green,Cochrane Handbook for Systematic Reviews of Interventions),科克伦协作组织(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2011年网络版,https://handbook-5-1.cochrane.org/index.htm#chapter_1/1_2_2_what_is_a_systematic_review.htm。
【10】哈米德·穆萨普尔等:“临床医学中系统综述背后的理论基础:一个概念框架”(Hamideh Moosapour,Farzane Saeidifard,Maryam Aalaa,Akbar Soltani and Bagher Larijani,“The Rationale behind Systematic Reviews in Clinical Medicine:A Conceptual Framework”),《糖尿病与代谢紊乱杂志》(Journal of Diabetes &Metabolic Disorders)第20卷第1期(2021年4月),第919~929页。
【11】雷·辛、玛丽亚·克莱桑:“什么是种族居住融合?1950—2013年研究综述”(Ray Sin and Maria Krysan,“What is Racial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 Research Synthesis,1950—2013”),《种族与族裔社会学》(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第1卷第4期(2015年),第467~474页。
【12】国内第一篇系统性综述出自医学界,参见胡桂、赵明、傅鹰:《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致肝损害的系统性综述》,《药物流行病学杂志》1998年第2期,第78~83页;国内使用系统性综述的代表性研究来自图书情报管理领域,参见汤志伟、郭雨晖:《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利用:基于CNKI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情报杂志》2018年第7期,第176~181页;在考古学领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学者们使用系统性综述分析甲骨文识别技术研究的现状,参见刘洋等:《甲骨文识别技术研究现状与展望》,《知识管理论坛》2023年第2期,第115~125页。
【13】仅使用“(Jewish immigra*) or Aliyah*”作为检索词,在“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中检索出3437份文献,其中“Article”(即期刊文章)类别文献有2158份,检索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
【14】Zotero是一款开源文献管理软件,可用于文献资料的采集、分类与注释,在本研究中用于整理55篇有关阿利亚的研究文献,以辅助归纳分析与图示制作。
【15】Kappa值是一种衡量两位或多位编码者在分类判断上一致性的统计指标,被广泛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系统性综述、元分析等领域,以衡量研究筛选或编码过程的可靠性。Kappa值的取值范围为-1到1,数值越高表示一致性越强;通常认为,0.41~0.60为“中等一致”,0.61~0.80为“高度一致”,0.81以上则为“非常一致”。
【16】艾姆达·奥尔、艾迪·玛纳和约瑟夫·玛纳:“以色列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苏联青少年的移民身份:文化特异性的组织原则”(Emda Orr,Adi Mana and Yosef Mana,“Immigrant Identity of Israeli Adolescents from Ethiopia and the Former USSR:Culture-Specific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欧洲社会心理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第33卷第1期(2003年),第71~92页。
【17】弗拉基米尔·哈宁:“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的政治经历:模式、精英和运动”(Vladimir Khanin,“Russian-Jewish Political Experience in Israel:Patterns,Elites and Movements”),《以色列事务》(Israel Affairs)第17卷第1期(2011年1月),第55~71页。
【18】玛尔瓦·沙罗夫·玛洛姆:“吃,祈祷,等待:等待阿利亚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的非正式以色列犹太教育”(Marva Shalev Marom,“Eat,Pray,Wait:The Informal Israeli Jewish Education of Ethiopian Youth Awaiting Aliyah”),《犹太教育杂志》(Journal of Jewish Education)第89卷第3期(2023年8月),第308~338页。
【19】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从叙事到历史: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犹太人从伊斯兰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新视角探讨”(Esther Meir-Glitzenstein,“From Narratives to History:New Perspectives on Mass Emigration of Jews from Islamic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50s”),《以色列历史杂志》(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第42卷第1~2期(2024年8月),第1~24页。
【20】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是一款常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处理与图形分析软件。
【21】加布里埃莱·安德尔:“’从一个正在沉没的世界逃离’:1933—1938年从奥地利移民的犹太人”(Gabriele Anderl,“’Departure from a Sinking World’:Jewish Emigration from Austria between 1933 and 1938”),《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第66卷(2021年10月),第58~78页。
【22】阿萨夫·沙米斯:“超越抽象劳动:重思第二次阿利亚劳动意识形态中农耕手工工具的作用”(Asaf Shamis,“Beyond Abstract Labor:Rethinking the Role of Farming Hand Tools in Second Aliyah Labor Ideology”),《犹太文化与历史》(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第22卷第1期(2021年2月),第52~67页。
【23】苏珊娜·拉特兰:“分歧的愿景:在全球舞台上与苏联犹太人移民有关的辩论”(Suzanne D.Rutland,“Conflicting Visions:Debates Relating to Soviet 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Global Arena”),《东欧犹太事务 》(East European Jewish Affairs)第47卷第2~3期(2017年2月),第222~241页。
【24】加布里埃莱·安德尔:“’从一个正在沉没的世界逃离’:1933—1938年从奥地利移民的犹太人”,《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第66卷(2021年10月),第58~78页。
【25】奥马尔·布姆:“从’小耶路撒冷’到应许之地:犹太复国主义,摩洛哥民族主义与农村犹太移民”(Aomar Boum,“From ‘Little Jerusalems’ to the Promised Land:Zionism,Moroccan Nationalism,and Rural Jewish Emigration”),《南非研究》(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第15卷第1期(2010年3月),第51~69页。
【26】多里特·约瑟夫:“从德国犹太人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欧犹太女性移民至托管巴勒斯坦的生活故事中的叙事策略”(Dorit Yosef,“From Yekke to Zionist:Newarrative Strategies in Life Stories of Central European Jewish Women Immigrants to Mandate Palestine”),《以色列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第33卷第2期(2014年8月),第185~208页。
【27】玛尔瓦·沙罗夫·玛洛姆:“吃,祈祷,等待:等待阿利亚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的非正式以色列犹太教育”,《犹太教育杂志》第89卷第3期(2023年8月),第308~338页。
【28】雅科夫·利夫内、约西·戈尔茨坦:“’让我的人民离开’:以色列打开苏联移民大门的行动肇始”(Yacov Livne and Yossi Goldstein,“’Let My People Go’:The Beginnings of Israel’s Operation to Open Soviet Immigration Gates”),《苏联和后苏联评论》(Soviet and Post Soviet Review)第47卷第3期(2020年),第357~377页。
【29】利奥拉·哈珀林:“’第一个’定居点建立周年纪念与犹太复国主义纪念活动的政治性,族裔与种族研究”(Liora R.Halperin,“Anniversaries of ‘First’ Settl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Zionist Commemoration,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族裔与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第 44卷第6期(2020年2月),第1068~1087页。
【30】扬·西奥多·祖尔彻:“剖析移民机构:1948—1960年以色列犹太移民局行政实践研究”(Yann Scioldo-Zürcher,“Autopsie d’une Agence d’Émigration:Étude des Pratiques Administratives du Département de la Alya de l’Agence Juive Pour Isra⊇l,1948—1960”)[法语],《欧洲移民国际问题评论》(Revue Europe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第36卷第1期(2020年10月),第11~29页。
【31】劳伦·班科:“排除’不受欢迎分子’:托管巴勒斯坦对共产主义者、流民、罪犯与病患的处理”(Lauren Banko,“Keeping Out the ‘Undesirable Elements’:The Treatment of Communists,Transients,Criminals,and the Ill in Mandate Palestine”),《帝国与联邦历史杂志》(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第47卷第6期(2019年2月),第1153~1180页;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从叙事到历史: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犹太人从伊斯兰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新视角探讨”,《以色列历史杂志》第42卷第1~2期(2024年8月),第1~24页。
【32】古尔·阿罗伊:“穿越动荡之海:英属托管初期(1919—1929)前往巴勒斯坦的航行”(Gur Alroey,“Migrating over Troubled Water:The Voyage to Palestin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British Mandate,1919—1929”),《犹太文化与历史》(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第22卷第3期(2021年7月),第214~215页。
【33】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从叙事到历史: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犹太人从伊斯兰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新视角探讨”,《以色列历史杂志》第42卷第1~2期(2024年8月),第1~24页。
【34】穆罕默德·阿里·杜兰:“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犹太冲突为背景的皮尔委员会决策及阿拉伯人对土耳其的期待(1929—1939)”(Mehmet Ali Duran,“Decisions of the Peel Commission on the Arab-Jewish Conflicts in Palestine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Arabs from Turkey,1929—1939”)[土耳其语(文献原文为土耳其语,因为拼写的关系,这里使用其英文译名)],《巴勒斯坦研究公报》(Bulletin of Palestine Studies)第10期(2021年冬季号),第57~80页。
【35】苏珊娜·施拉夫施泰特:“不是去巴勒斯坦,而是费拉蒙蒂:1939—1943年’班加西小组’失败的非法移民行动”(Susanna Schrafstetter,“Ferramonti,not Palestine:The Failed Aliyah Bet of the ‘Benghazi Group’,1939—1943”),《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第37卷第3期 (2023年冬季号),第373~389页。
【36】苏珊娜·拉特兰:“分歧的愿景:在全球舞台上与苏联犹太人移民有关的辩论”,《东欧犹太事务》第47卷第2~3期(2017年2月),第222~241页。
【37】拉鲁卡·马特科:“1949年的阿利亚:作为记忆载体的罗马尼亚犹太人未刊移民申请”(Raluca Mateoc,“The Aliyah of 1949:Unpublished Migration Requests of Jews from Romania as Vehicles of Memory”),《见证者》(Martor)第24期 (2019年),第97~108页。
【38】雅科夫·利夫内、约西·戈尔茨坦:“’让我的人民离开’:以色列打开苏联移民大门的行动肇始”,《苏联与后苏联评论》第47卷第3期(2020年),第357~377页。
【39】塔季扬娜·梅德韦杰娃、伊戈尔·雷若夫、玛丽娜·斯特鲁科娃:“苏联与以色列:1967—1991年政治对抗背景下的文化对话经验”(Татьяна Медведева,Игорь Рыжов,Марина Струкова,“СССР и Израиль:опыт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в условия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1967—1991 гг.”)[俄语],《俄罗斯历史杂志》[Journal of Russian History (RUDN)]第22卷第2期(2023年),第289~302页。
【40】罗伯特·弗里德曼:“莫斯科与耶路撒冷:历经波折的75年”(Robert O.Freedman,“Moscow and Jerusalem:A Troubled 75 Year Relationship”),《以色列事务》(Israel Affairs)第29卷第3期(2023年),第492~511页。
【41】劳伦·班科:“排除’不受欢迎分子’:托管巴勒斯坦对共产主义者、流民、罪犯与病患的处理”,《帝国与联邦历史杂志》第47卷第6期(2019年2月),第1153~1180页。
【42】布兰卡·苏库波娃:“捷克的犹太人口与移民:原因、论证、后果(1918—1939年)——20世纪犹太人迁移问题研究”(Blanka Soukupov,“Židovské obyvatelstvo zemí a í léta 1918—1939” K problematice migrací ve 20.století”)[捷克语],《斯洛伐克民族学》(Slovenský Národopis)第70卷第1期(2022年),第16~29页。
【43】塔季扬娜·梅德韦杰娃、伊戈尔·雷若夫、玛丽娜·斯特鲁科娃:“苏联与以色列:1967—1991年政治对抗背景下的文化对话经验”,《俄罗斯历史杂志》第22卷第2期(2023年),第289~302页;拉鲁卡·马特科:“1949年的阿利亚:作为记忆载体的罗马尼亚犹太人未刊移民申请”,《见证者》第24期 (2019年),第97页。
【44】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从叙事到历史: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犹太人从伊斯兰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新视角探讨”,《以色列历史杂志》第42卷第1~2期(2024年8月),第1~24页。
【45】 扬·西奥多·祖尔彻:“剖析移民机构:1948—1960年以色列犹太移民局行政实践研究”,《欧洲移民国际问题评论》第36卷第1期(2020年10月),第11~29页。
【46】玛尔瓦·沙罗夫·玛洛姆:“吃,祈祷,等待:等待阿利亚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的非正式以色列犹太教育”,《犹太教育杂志》第89卷第3期(2023年8月),第308~338页。
【47】艾娃·韦格日恩:“离开波兰行动:1956—1958 年卡塔伊尔·卡茨及其对波兰的外交使命”(Ewa Węgrzyn,“Operacja Wyjazd z Polski:Katriel Katz i jego dyplomatyczna misja w Polsce,1956—1958”)[波兰语],《犹太研究》(Studia Judaica)第50卷第2期(2022年12月),第291~307页。
【48】 扬·西奥多·祖尔彻:“剖析移民机构:1948—1960年以色列犹太移民局行政实践研究”,《欧洲移民国际问题评论》第36卷第1期(2020年10月),第11~29页。
【49】亚历山德拉·塞科林:“1951年伊朗犹太人的阿利亚:伊朗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历史分析”(Alessandra Cecolin,“Iranian Jewish Aliyah in 1951: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Iranian Jewish Emigration to Israel”),《族裔与民族主义研究》(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第18卷第3期(2018年),第221~236页。
【50】劳伦·班科:“悲痛、婚纱与官僚迫害:一场悲剧之后的“准难民”经历(1941—1946)”(Lauren Banko,“Grief,a Wedding Veil,and Bureaucratic Persecution:Becoming Refugee-adjacent in the Aftermath of Tragedy,1941—1946”),《移民与少数族裔》(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第39卷第2~3期(2021年9月),第155~185页。
【51】马科斯·西尔伯:“波兰移民想回去: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的回归移民和国家建设政治”(Marcos Silber,“Immigrants from Poland Want to Go Back:The Politics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in 1950s Israel”),《以色列历史杂志》(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第27卷第2期 (2008年),第211页;艾娃·韦格日恩:“寻求重返波兰:’哥穆尔卡阿利亚’移民在以色列的个案研究(1956—1960)”(Ewa Węgrzyn,“Seeking a Return to Poland.The Case of the ‘Gomulka Aliyah’ Immigrants in Israel,1956—1960”),《克拉科夫犹太文献》(Scripta Judaica Cracoviensia)第16期(2018年),第124~125页。
【52】詹妮弗·格鲁克里奇:“父亲、歌德、康德与里尔克:教养理想、第五次阿利亚与德裔犹太人在伊休夫的融合”(Jennifer Glucklich,“Father,Goethe,Kant,and Rilke:The Ideal of Bildung,the Fifth Aliyah,and German-Jewish Integration into the Yishuv”),《号角》(Shofar)第35卷第2期(2017冬季号),第21~53页。
【53】根纳迪·埃斯特赖克:“逃离波兰:1950年代的苏联犹太人移民”(Gennady Estraikh,“Escape through Poland:Soviet 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1950s”),《犹太历史》(Jewish History)第31卷第3/4期(2018年6月),第310页。
【54】米兰·拉多万诺维奇:“移民催生移民——论犹太人从南斯拉夫向巴勒斯坦/以色列移民的连续性”(Milan Spawning Migration-On Continuity in Jewish Emigration from Yugoslavia to Palestine/Israel”),《20世纪史》(Istorija 20 Veka)第38卷第2期(2020年5月),第187~202页。
【55】拉凯菲特·扎拉希克:“作为难民身处巴勒斯坦的神经科医生:1933—1945”(Rakefet Zalashik,“Psychiater als Flüchtlinge in Palästina 1933 bis 1945”)[德语],《神经学家》(Nervenarzt)第84卷第7期(2013年),第869~873页。
【56】塔季扬娜·梅德韦杰娃、伊戈尔·雷若夫和玛丽娜·斯特鲁科娃:“苏联与以色列:1967—1991年政治对抗背景下的文化对话经验”,《俄罗斯历史杂志》第22卷第2期(2023年),第297~298页。
【57】弗拉基米尔·哈宁:“俄裔犹太人在以色列的政治经历:模式、精英和运动”,《以色列事务》第17卷第1期(2011年1月),第55~71页。
【58】詹妮弗·格鲁克里奇:“父亲、歌德、康德与里尔克:教养理想、’第五次阿利亚’与德裔犹太人在伊休夫的融合”,《号角》第35卷第2期(2017冬季号),第21~53页。
【59】埃拉扎尔·本-卢卢:“跳出你的阿利亚之路:对土耳其犹太移民在以色列适应与融合的一个人类学考察”(Elazar Ben-Lulu,“Dancing Your Aliyah Passage: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Acclimatis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urkish Jewish Immigrants in Israel”),《以色列事务》(Israel Affairs)第30卷第1期(2023年12月),第173~192页。
【60】艾姆达·奥尔、艾迪·玛纳和约瑟夫·玛纳:“以色列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苏联青少年的移民身份:文化特异性的组织原则”,第71~92页;丽贝卡·瑞吉曼:“迁往故土:以色列的南非犹太人”(Rebeca Raijman,“Moving to the Homeland:South African Jews in Israel”),《移民与难民研究》(Journal of Immigrant &Refugee Studies)第11卷第3期(2013年),第259~277页。
【61】玛尔瓦·沙罗夫·玛洛姆:“吃,祈祷,等待:等待阿利亚的埃塞俄比亚青年的非正式以色列犹太教育”,《犹太教育杂志》第89卷第3期(2023年8月),第308~338页。
【62】索菲亚·德格-穆勒、乔纳斯·卡尔松:“流动的歌声:论贝塔以色列人礼拜仪式CD”(Sophia Dege-Müller and Jonas Karlsson,“Songs that Travel:A Review Article of the CD BOX the Liturgy of Beta Israel”),《交织的宗教》(Entangled Religions)第11卷第1期(2021年),第1~32页。
【63】以斯帖·梅厄-格利岑施泰因:“从叙事到历史: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犹太人从伊斯兰国家大规模移民的新视角探讨”,《以色列历史杂志》第42卷第1~2期(2024年8月),第1~24页。
【64】扬·西奥多·祖尔彻:“剖析移民机构:1948—1960年以色列犹太移民局行政实践研究”,《欧洲移民国际问题评论》第36卷第1期(2020年10月),第11~29页。
【65】亚历山德拉·塞科林:“1951年伊朗犹太人的阿利亚:伊朗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历史分析”,《族裔与民族主义研究》第18卷第3期(2018年),第221~236页。
【66】阿莎·苏珊·雅各布:“阿利亚:村子里最后的犹太人——喀拉拉邦犹太人历史的诗学”(Asha Susan Jacob,“Aliyah:The Last Jew in the Village-A Poetics of the History of Jews in Kerala”),《南亚评论》(South Asian Review)第42卷第3期(2020年10月),第218~233页。
【67】葆拉·卡巴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以色列犹太人:移民协会与公民影响力”(Paula Kabalo,“Israeli Jews from Muslim Countries:Immigrant Associations and Civic Leverage”),《当代中东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第6卷第3/4期(2019年),第324~337页。
【68】鲁道夫·赫伯尔:“城乡迁徙的原因:德国理论述评”(Rudolph Heberle,“The Cause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43卷第6期(1938年5月),第932~950页;埃弗雷特·李:“迁徙理论”,(Everett S.Lee,“A Theory of Migration”),《人口统计学》(Demography)第3卷第1期(1966年),第47~57页。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7期
编辑:赵俊华
审核:安 瑞
监制:苗书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