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历史学博士,吉林省教育学院讲师。
摘要:俄国国家学派是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在俄国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史学流派。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是国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国家是他们将俄国历史概念化的核心话语。他们同异并存地阐释国家观念,从地理因素、殖民史观、世界视野等维度解释俄国历史。两者历史分期观念的不同,折射了历史解释方式的差异。索洛维约夫将俄国史分为氏族制度和国家两个时期,强调政治活动作用,反对按时间线索进行分期。克柳切夫斯基按时间线索进行分期,从多种因素综合角度解释历史。两者从不同角度叙述了俄国史学史。这为他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叙事方法或史学史支撑。从国家观念、历史分期、史学史书写方面将两者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俄国国家学派史学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俄国国家学派;谢·米·索洛维约夫;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观;历史分期观念
俄国国家学派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俄国众多史学流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名称,是因为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1】。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中期,国家学派作为俄国史学发展史上持续存在近百年的俄国史学流派,经历了三代传承与演变。谢·米·索洛维约夫(S.M.Soloviev,1820—1879)是缔造国家学派和推动国家学派传承的核心人物,他与鲍·尼·契切林(B.N.Chicherin,1828—1904)和康·德·卡维林(K.D.Kavelin,1818—1885)一起成为国家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V.O.Kliuchevskii,1841—1911)成为国家学派的核心领军者,通过自身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为俄国史学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克柳切夫斯基与瓦·伊·谢尔盖耶维奇(V.I.Sergeevich,1832—1910)、亚·德·格拉多夫斯基(A.D.Gradovskii,1841—1889)和费·伊·列昂托维奇(F.I.Leontovich,1833—1911)同属国家学派第二代历史学家。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到20世纪中期之前,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米鲍·尼·留科夫(P.N.Milyukov,1859—1943)成为国家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
谢·米·索洛维约夫半身像
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分别是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这两个时间节点上俄国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研究与俄国时代发展进程同向而行,都在历史书写中表达了支持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的主张。1847年,索洛维约夫成为莫斯科大学编外教授,并于1871年至1877年担任莫斯科大学校长。从1851年至1879年,索洛维约夫写作了29卷《远古以来俄国史》。1879年10月4日,索洛维约夫逝世。从1879年开始,索洛维约夫的学生克柳切夫斯基担任莫斯科大学编外教授,开始讲授俄国史。“《俄国史教程》是克柳切夫斯基的代表作。这是他在莫斯科大学三十年来讲课和研究的综合成果。”【2】《俄国史教程》一共五卷,前四卷在克柳切夫斯基生前出版,第五卷由其学生整理后于1921年出版。这对师生在俄国史教学岗位上的薪火相传,也推动着俄国国家学派的发展和代际转移。
就国外国内学术研究状况来看,关于俄国国家学派的研究,学术界基本以人物思想分析的形式进行。英语学界的研究角度有:按时间线索分别叙述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的史学思想【3】,解释索洛维约夫历史书写思路的成因、影响以及克柳切夫斯基的评价【4】,索洛维约夫与特纳边疆观念的比较研究【5】,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观的解析【6】等。俄语学界从思想来源【7】、历史观【8】、殖民观【9】和史料整理【10】等方面研究了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从俄国历史进程观和史学史价值【11】方面评析了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国内学界从国家学派史学对俄国社会史研究兴起的价值【12】、国家学派的古罗斯文明观【13】、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观【14】和克柳切夫斯基的学术史意义【15】等维度进行了分析。这些成果聚焦于特定的史学专题或历史学家,研究透彻而深入,但鲜有对19、20世纪之交国家学派发展历程的专门论述。同时,国家学派在俄国发展了近百年的时间,其三个阶段各有代表人物,他们的史学思想既有传承,也有嬗变,目前鲜见对他们思想的分析比较。这为本文从史学比较角度研究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史学思想同异,进而呈现国家学派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学术启示和线索。
《历史问题》杂志2002年第6期封面
两者国家观的解释
从时代背景来看,克柳切夫斯基大学求学阶段(1861—1865)正处于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这一俄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在大学期间,克柳切夫斯基热情洋溢地关注国家现状和未来命运问题。在面对“守旧”与“维新”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与学术倾向中,克柳切夫斯基选择了后者。因此,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国家学派学术理念——“国家是历史进步的主体和动力,国家在俄国’阶层的奴役和解放’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6】——成为克柳切夫斯基的心灵归属。
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在核心概念上的一致之处,也是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的逻辑起点。作为继索洛维约夫之后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克柳切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之间一致性的最明显体现是,他们都从“国家”这一观念和立场出发解释俄国历史发展进程。在国家概念的界定上,索洛维约夫在《远古以来俄国史》前言中将领土统一、联系密切、内源发展和持续改革看作国家的四个基本属性。“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向读者预先说明作品的主要概念,而不是将俄国历史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时期,而是要将它们联系起来,探究主要现象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形态之间的直接连续性。”【17】这表现在他对俄国历史研究中的“诺曼起源说”、顺序继承制、蒙古人入侵对俄国历史的影响以及俄国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的回答中。克柳切夫斯基解释国家概念的基点是下述四个基本维度:“地理状况、历史状况、国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四邻”【18】。就这四个基本概念所代表的历史视角而言,可以明显表现出克柳切夫斯基与前述索洛维约夫国家观念之间的相似或一致之处。
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1-2卷,社会经济出版社1959年版封面。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思想出版社1987年版封面。
关于地理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索洛维约夫认为地理环境是塑造俄国历史独特性的根本因素:“相较于西欧地理环境,俄国地理环境决定了俄国历史在边疆特征、周边民族关系、行政区划方面的独特性。”【19】按索洛维约夫的叙述,由地理环境塑造的俄国历史独特性之一是,俄国地形以平原为主,缺少西欧国家由山脉区隔的边疆壁垒。因此,西欧相对较早走上国家发展道路,而俄国的国家形成要经历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过程。索洛维约夫的这一历史判断是值得商榷的,但确实表现出他对地理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用的重视。同样,克柳切夫斯基承认“人们始终处于或者适应于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或者适应于自然的力量和活动方式的状态……自然界的影响还表现在由它引起并且也影响它自身的人类活动中”【20】。从“地理状况”这一维度出发,克柳切夫斯基评述了“土壤地带和植物地带的作用”“河流系统的影响”和“奥卡河-伏尔加河两河流域及其作用”。在“国家的自然环境”这一术语层面,克柳切夫斯基同索洛维约夫一样,分析了“森林”“平原”和“草原”三个维度及它们各自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关于地理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之间除了上述共性之外,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克柳切夫斯基并不像索洛维约夫那样强调“地理状况”和“自然因素”对俄国历史发展的根本性意义。尽管前述索洛维约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并未将地理因素的作用绝对化,但在俄国历史起源问题的解释中,他仍遵循从地理或自然环境到人的历史解释方向。例如,索洛维约夫曾指出:“有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靠近大海,促成职业的多样性、劳动分工、地产的形成等。而俄国是一个没有自然边界、易于入侵的巨大平原。”【21】在这一历史解释立场之下,1851年出版的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一卷遭遇相互矛盾的评价。评论界主要关注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关于地理因素决定性影响论题的新颖性”【22】。也就是说,俄国评论界将索洛维约夫看作一位信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历史学家。与此不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在理解自然界对人类影响的时候,也应当看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作用。在这种作用过程中,也反映出自然界的某些特点。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对自然界进行的文化加工,有一定的限度,并且一定要秉持谨慎态度”【23】。就此看到,克柳切夫斯基在“人与自然”这个俄国历史解释维度,更着意强调“人”的因素。这也是克柳切夫斯基在理解地理环境与人的作用关系问题上,比索洛维约夫更富有辩证意识的表现。
罗斯大公权位继承制度问题进一步显现了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国家观念的差异。在索洛维约夫历史解释中,罗斯大公权位继承制度是优先权制。“王公们持有整个家族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观念。这体现于下述事实中:所有王公都有一位年长王公。这位年长王公始终是整个家族的年长者。”【24】年长王公具有继承大公权位的优先权,也是大公的合法继承人。不同于父子相承的世袭制,优先权制度使大公权位不会局限于任何特定的王公支系家族。任何年龄长、辈分高的王公家族成员都有继承大公权位的可能性。关于罗斯大公权位继承制度描述,克柳切夫斯基使用的术语是顺序继承制。虽然所用术语不同,但克柳切夫斯基表述的顺序继承制与索洛维约夫的优先权制在内涵上是相同的。两者的不同在于,对罗斯大公权位继承制度历史作用的评价上。索洛维约夫持积极的评价态度,认为优先权制有助于维护王公家族的统一性和俄国领土的统一性。尽管索洛维约夫也注意到优先权制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导致王公内讧的危险,但更强调优先权制在领土统一、王权集中等方面对俄国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而克柳切夫斯基对顺序继承制持完全批判态度,认为古代俄国动乱根源就在于这种继承制度【25】。
殖民史观是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在阐释俄国国家历史时共有的观点。索洛维约夫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提出殖民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俄国帝国形成和领土扩张过程。“殖民是一个社会经济过程,来自都市区的移民到殖民地定居,占据并开发未曾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26】关于殖民的历史作用,克柳切夫斯基“重点探讨了东北罗斯殖民的两个后果——民族后果和政治后果。在叙述俄国人在东北罗斯殖民的民族后果时,克柳切夫斯基是结合芬兰人构成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来考察罗斯部落形成过程的”【27】。从历史角度来说,俄国历史是俄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在外显层面,这是俄国领土不断扩张的过程。关于俄国国家领土扩张的直接推动力,克柳切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都认为是俄国历史上的殖民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同索洛维约夫一样,克柳切夫斯基所谓的殖民是俄国人由于生存需求或环境逼迫而扩展或迁移定居点的行动,并不是中文语境中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语境下的“军事征服”和“武力扩张”,两者也完全没有赋予“殖民”这一术语侵略和扩张的含义。
在某种意义上,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都不约而同地隐匿和回避了俄国人在历史上向外扩张中的“暴力性质”。两者所谓的“殖民”,其直接和根本意义就是俄国人的“和平”移民和迁居过程。索洛维约夫通过将“殖民”仅看作一个社会经济过程,将殖民“非暴力化”;克柳切夫斯基则通过术语替换方式实现这一点。以《俄国史教程》第一卷为例,克柳切夫斯基使用多个意义等同于“殖民”的术语。在论述俄国人向外拓殖的历程时,克柳切夫斯基除了用“殖民”(第十七讲、第十八讲)之外,还有“迁居”(第八讲)、“移民”(第九讲)、“流迁”(第十六讲)等。在术语使用方面,克柳切夫斯基之所以存在多个术语并用的情况,是因为他认为俄国历史上的殖民现象是由俄国“人民”发起的,是“自发”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对俄国历史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一点体现在苏联学者对克柳切夫斯基殖民观点的下述概述:“殖民活动对社会现象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理论,使克柳切夫斯基……把着重点放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居民身上,认为他们能够推翻丧失发财致富来源(对外贸易、战争和内讧)的工商业显贵和军事服役贵族显贵的统治,从而使王公的政权获得优势。”【28】在此引用苏联学者的这种学术评价,从一个侧面说明克柳切夫斯基在解释俄国国家历史时对殖民观点的侧重。
两者相同之处的另一个体现是,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都明确表现出了世界史的理念。他们都强调在世界历史视野或多个民族国家语境中研究俄国国家历史。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索洛维约夫从多个欧洲民族国家视野书写与研究俄国历史,也从书写实践中体现出在世界历史视野下审视俄国历史的诉求与实践。“随着新王朝(指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开始了。这标志着俄国现在是欧洲众多强国中的国家之一……在18世纪下半叶,我们观察到一种新趋势。事实证明,俄国单纯为了物质福利而采纳欧洲文明的做法是不够的。出现了对精神、道德教育的需求。”【29】克柳切夫斯基按照这种思路解释国家的民族性和世界意义:“在国家内部,民族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个体,也是历史意义上的个体。国家中的民族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并且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世界意义。”【30】在俄国史学思想上,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历史书写中的世界意识可以溯源至有“俄国史学之父”之称的尼·米·卡拉姆津(N.M.Karamzin,1766—1826)。卡拉姆津在《俄国旅行者信札》中从全欧洲的视野记录了自己游历西欧的思考:“’民族’的东西,在’人类’的东西面前不值一提,最重要的事情是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而不是怎么成为一个斯拉夫人。”【31】卡拉姆津是一位文学家兼历史学家,他所处时代俄国专业化的历史研究还未正式出现。随着19世纪中叶俄国国家学派形成,俄国历史研究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因此,卡拉姆津之前表达的世界意识在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的著作中获得了专业的史学表达。
上述比较内容是从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之间的共性着手,以此分析两者在学术理念上的联系和传承。这一部分的比较还涉及两者在共性之外的差异。因为两者虽有师生关系和学术传承,但各自作为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期国家学派发展史上不同时段的代表人物,在秉持同一种学术理念和学术话语时,对其具体的阐释和运用也一定存在不同。上述比较研究对两者共性的阐释并没有也无法穷尽他们之间存在的学术共性,只是按前后行文语境和论证需求,选取了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国家观念中有代表性且能够形成鲜明对照之处进行论述。俄国史或国家史是俄国历史学家历史书写中具有普遍性的选题。或者可以说,每个时代的俄国史家都重新书写俄国史。本文中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的著作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这符合历史研究的常情,也说明俄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即使历史书写主题相同,每个历史学家呈现的俄国史书写往往各异其趣。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同属国家学派成员,在核心话语和学术理念上存在延续性和继承性。但作为两个独立的历史书写者,他们之间在历史时间观念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两者历史分期观念的分析
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在历史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对待俄国历史分期问题的不同态度。具体来说,索洛维约夫不主张按时间线索对历史进行分期。在《远古以来俄国史》第四卷中,索洛维约夫介绍了当时俄国学界的历史分期观点。在历史分期上,当时俄国学界的做法是以重要历史事件为中心进行划分。可以作为历史分期界标的重要历史事件有八个:“这些都是历史确实向新的方向发展的关键事件。历史学家在这些发展处停滞,用这些发展来划分时期。这些事件是雅罗斯拉夫一世去世,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统治,13世纪的第五个十年,伊凡·卡利达掌权,黑暗的瓦西里去世和伊凡三世掌权,旧王朝消亡和新王朝崛起,彼得大帝掌权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32】在这些关键事件的基础上,俄国学界存在“三分法”和“二分法”两种历史分期方法。俄国历史分期“三分法”的具体内容是:“一些学者开始选择上述事件中最重要的,创造了俄国历史的三个重要时期。古代时期,从留里克到伊凡三世。中间时期,从伊凡三世到彼得大帝。新时期,从彼得大帝到现代。”【33】而俄国历史分期“二分法”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一些学者不满于这些时期划分,认为只有两个长的时期,彼得之前和彼得之后。”【34】第二种观点的基本内容是:传统上,大多数历史学家以11世纪中期雅罗斯拉夫去世为界,将俄国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俄国历史学家认为,俄国产生于第一个历史阶段。在第二个历史阶段,俄国就分裂了。第一个时期称为诺曼时期,诺曼人及诺曼人的活动处于俄国历史舞台的中心。第二个时期称为封地时期,最为突出的是王公之间的战争【35】。
索洛维约夫对这些历史分期方法持否定态度并解释了原因:“通常,每位新的学者都努力证明前辈划分的错误之处,努力证明在前辈学者划定的时间线后发展仍在继续。前辈学者用来描述新时期的特征,在这之前就显现出来了。这样的争论是无尽的。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事情突然中止,也没有任何事情突然开始。新事物开始时,旧事物仍在继续。”【36】从总体上来说,索洛维约夫认为,任何以特定时间或重要事件为节点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都会引起上述所列“分期术语”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的争论。这种“名”“实”争论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是无限延续的,也证明了历史分期方法的无效性。另外,索洛维约夫否定历史分期的更重要原因是他自己的历史观念。“氏族制度”和“国家”是索洛维约夫解释俄国历史的两个核心术语。在他看来,俄国历史就是“氏族制度”和“国家”正在逝去和正在生成的过程。这两个过程虽然是不同和前后相续的,但因为历史过程本身的绵延性和连续性,难于从精确时间和历史分期角度精确分期。
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3-4卷,社会经济出版社1960年版封面。
从这一立场出发,索洛维约夫还证伪了上述历史分期“二分法”的第二种观念,即诺曼时期和封地时期。就诺曼时期来说,索洛维约夫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诺曼人与斯拉夫人关系问题。“一些学者试图将诺曼人制度与罗斯封地时期联系起来,说封地制度下罗斯王公之间的关系源于诺曼人。这样的尝试是可笑的,也是不成功的。因为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部落中,无法发现与俄国王公之间的关系相似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任何地方由兄弟而不是其儿子继承王公之位,王公权位也不是基于氏族中的最长者。只有在斯拉夫部落中能够看到类似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现象完全是而且只属于斯拉夫人。”【37】“事实上,斯拉夫国家的建立,有芬兰人和诺曼人的参与。然后,活动中心立即南移到斯拉夫人的第聂伯河区域。第聂伯河区域成为中心,这是斯拉夫人原则完全占据主导第五代的原因。”【38】索洛维约夫从根本上认为,诺曼时期的俄国历史是属于斯拉夫人的,为了罗斯利益服务的,其本质并非诺曼的。因此,认为俄国历史上存在一个“诺曼时期”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就封地时期来说,索洛维约夫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关于俄国历史分裂性与统一性的问题。“在这个时期,罗斯与其他有机形成的王国相似,划分为由不同统治者统治的部分。进一步研究,显而易见的是,表面上分裂的领土保持着统一性。这是因为不同统治者彼此之间保持着联系,并且依附于首领。”【39】在这个问题上,索洛维约夫的态度是,即使在封地时期,俄国历史仍然是统一的。因此,呈现分裂状况的“封地时期”并不是俄国历史的发展趋向和本质。就此,索洛维约夫认为,由任何关键历史事件划分的不同历史阶段之间,都是紧密关联、不分彼此的。索洛维约夫拒绝任何严格的历史分期方法,无论诺曼时期、封地时期,还是蒙古时期、君主主义时期等。索洛维约夫对待严格历史分期的否定态度,是他整体的有机发展观念使然。在他看来,任何事件、时段都隶属于一个整体发展历程之中。这一发展历程的趋向是统一的现代国家。但从历史知识角度来看,索洛维约夫这种截然否定历史分期的做法是武断的,忽视了历史学“时间”维度的意义和价值。
与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分期观点不同,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明确遵循按照时间线索进行历史分期的方法。从前述两者共有的殖民史观来说,克柳切夫斯基按照下述线索解释俄国历史:“俄国的历史是一部迁移、殖民的历史。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根据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把俄国史分为四个时期。”【40】它们分别是:8至13世纪,以第聂伯河为中心的城市、商业罗斯时期;13至15世纪中叶,以伏尔加河上游为中心的自由农业时期;15世纪中期至17世纪前20年,军事农业时期;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农奴制时期。除此之外,就《俄国史教程》的五卷内容(共86讲)而言,克柳切夫斯基也分别设定了不同的历史分期:第一卷,从古代至封邑时期(1-20讲);第二卷,从莫斯科兴起至16世纪末(21-40讲);第三卷,从17世纪到17世纪80年代(41-58讲);第四卷,从17世纪末到1762年宫廷政变(59-74讲);第五卷,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亚历山大二世农奴制改革(75-86讲)。在历史分期问题上,克柳切夫斯基没有索洛维约夫那种纠结心态,也并未将前后相继或共时存在的各种历史分期观点看成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因此,在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历史叙述中,我们能发现不同维度的历史分期方式和节点性事件,读来也有明晰的时间印记。
历史分期观念不同,背后隐含和折射的是历史解释方式的不同。在俄国历史解释中,在俄国历史起源问题上,索洛维约夫强调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在俄国历史发展问题上,他强调以王公、沙皇为代表的政治人物活动的核心历史作用。克柳切夫斯基在对待地理环境、政治人物作用的态度上,与索洛维约夫有相同之处,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多因素论观点。不同于索洛维约夫具有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倾向的观点,克柳切夫斯基将地理、政治等诸多因素整合到他理解的、作为多种因素共同和协同作用结果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界在历史过程中,是作为有人类社会生存的国家的自然条件来理解的……个人、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自然条件,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种基本历史力量。”【41】《俄国史教程》的特点与意义。“正如一些研究克柳切夫斯基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新历史宣言。克柳切夫斯基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社会学取向。”【42】克柳切夫斯基的学生M.K.柳巴夫斯基梳理了克柳切夫斯基在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方面的贡献:“我们深入探讨了各个问题,研究了动荡时代,彼得,立陶宛俄国的转型,俄国最高权力和国家的历史,税收,俄国乡村的命运,俄国城市的过去,从莫斯科州的南部郊区到莫斯科附近的地区,再到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北部的农民世界。”【43】克柳切夫斯基深入探讨的众多俄国历史论题,反映出他在全欧洲历史视野中关切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史学意识。柳巴夫斯基的上述概述反映出克柳切夫斯基在总体历史观上的变化。克柳切夫斯基在其学术生涯中,前期追随西方派思想和与西方派思想同声相应的国家学派史学。但随着俄国改革历程经历的曲折和自身政治观点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克柳切夫斯基态度趋于保守,也更偏向斯拉夫派思想。因此,克柳切夫斯基后期的整体历史解释态度是:拒绝外在,主张内在;拒绝西方化,主张俄国化。相较之下,索洛维约夫终生支持西方派观点,并未发生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克柳切夫斯基这一总体历史解释立场也是他与索洛维约夫的差异所在。两者学术思想的同异造就了俄国国家学派的学术时间线,镌刻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俄国史学史。与此同时,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也在各自历史书写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追述俄国史学史。这成为另外一个将两者进行史学比较的维度。
两者史学史书写的比较
除了上述对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史学阐释外,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这一对师徒在各自著作中都对俄国历史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史学史分析。从18世纪开始,以彼得大帝的大臣、历史学家塔季谢夫的《俄国史》为代表,依托俄国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等学术机构和大学,俄国历史学研究开始逐渐走上了西欧历史学的学科化发展轨道。这是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进行史学史书写的学术前提。这也使他们二人在回溯俄国史学史过程中,将关注焦点都聚焦在18世纪之前的俄国史学史。在俄国史学史分析上,两人的差异主要是自觉程度和关注对象有所不同。就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而言,“根据克柳切夫斯基在本书中使用的所有资料,就可以了解《俄国史教程》的史料基础了。他所引用的资料一般都经过他细心的史料学分析”【44】。相较于克柳切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并未自觉和有意识地梳理史学史。就整体而言,史学史内容在29卷《远古以来俄国史》中所占比重是非常少的。根据笔者统计,其中仅有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和第六卷中以“文化”命名的章节有与史学史相关的叙述。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远古以来俄国史》行文风格主要是“直陈其事”,索洛维约夫笔墨重心是书写俄国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很少交代学界就某个历史事件研究上存在的不同学术观点。
在史学史研究的关注对象上,索洛维约夫既关注古希腊史学家,也关注俄国的编年史传统。比如,在《远古以来俄国史》开篇叙述俄国历史起源时,索洛维约夫提到了荷马、希罗多德的相关记述。他肯定了希罗多德将地理因素作为古代罗斯发展根本原因的历史解释【45】。索洛维约夫注意到古代希腊史学成就,这与他曾在西欧游学两年的学术经历有关。而西欧历史学家一般会将史学史追述至古希腊。他熟悉也认同19世纪兰克、基佐等西欧历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西方史学在19世纪初期即已为俄国学界知晓。其重要原因是,1812年拿破仑战争使俄国学界不得不关注来自西方的入侵者的历史及其思考方式。19世纪初期,俄国史学处于业余研究与专业研究杂糅状态。例如,俄国当时代表性的史学家卡拉姆津1816至1818年出版的《俄罗斯国家史》前八卷中虽有基于档案考察的史实描述,但主要研究方法或者说同时也作为文学家的卡拉姆津自己钟情的史学方法是浪漫主义的文学修辞方法。这使当时俄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索洛维约夫在历史书写中呈现和运用了西方史学代表人物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这反映了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史学与西方史学交流日益加强的趋势。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在俄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俄国史学遗产对索洛维约夫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之一是索洛维约夫在其历史著作中所梳理的俄国编年史传统。比如,在叙述13和14世纪俄国历史时,索洛维约夫比较了当时俄国北方编年史和南方编年史的区别:北方编年史叙述冷静刻板,南方编年史叙述语言生动;北方编年史以北方作为整体叙述空间,南方编年史叙述则以南方存在的各个公国如基辅、沃里尼亚等为叙述空间【46】。在叙述这一俄国史学史状况时,索洛维约夫的行文语气是平和公允的,并没有倾向北方或南方编年史传统的学术评价。结合《远古以来俄国史》的行文和写作,可以看到两种区域编年史传统都影响了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始终运用“全罗斯”这一学术话语,将国家统一作为俄国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这反映了北方编年史传统的影响。而《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受众首先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这使索洛维约夫在写作中既有专业史家的冷峻,也有历史教师授课语言的灵动。这种叙事风格可以共同追溯到上述北方与南方两种编年史传统。通过这一俄国史学史叙述,索洛维约夫不仅继承了俄国编年史的叙事传统,也铭刻了自身史学研究在不断变动的俄国史学史进程中的地位。
相较而言,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的价值是分析和呈现了18世纪之前俄国历史学起源时期的状况。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历史学在18世纪之前俄国的体现是编年史的编修。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五讲、第六讲和第七讲以《始初编年史》为中心,专门叙述了俄国史学史发展上的这个编年史阶段。就文本来讲,克柳切夫斯基从《始初编年史》历史渊源、编纂者、编纂方式和所汇集年表方面着手分析,呈现了12世纪俄国编年史家的历史观,并结合他自己所处时代关注的“俄国史开端”这一问题阐释了《始初编年史》的史料价值。克柳切夫斯基将《始初编年史》看作俄国编年史发展历程中的一部开创性和典范性作品。“因为它是真正的始初编年史,因此更有价值。后来的编年史编纂都以它为样板,直接延续它并且尽力模仿它。”【47】克柳切夫斯基按照整体与部分的逻辑阐释《始初编年史》在俄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始初编年史》是整体,而它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学界引用或提及频率较高的《往年纪事》,也包括学界不那么熟知的《弗拉基米尔时代罗斯受基督教洗礼的传说》和《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编年史》。为了清晰呈现《始初编年史》的内容、方法和价值,本文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论述,以下面的表格形式表现出来【48】。
根据表1,克柳切夫斯基表明了俄国史学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文本《往年纪事》与他集中论述的《始初编年史》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年纪事》是《始初编年史》的文本构成内容。在国内俄国史学史研究中,一般将《往年纪事》看作俄国历史学起源时期的典型文本。例如,朱寰、胡敦伟两位先生在《往年纪事》中译本前言中写道:“《往年纪事》是古罗斯国流传下来的第一部编年史,是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平原各族人民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49】在此,有关俄国史学发展史起点问题,克柳切夫斯基和国内学界两种认知观点呈现的差异,并不是孰对孰错、相互证伪的关系。因为正如《往年纪事》译者介绍的,《往年纪事》是否是古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在俄国学界本就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在俄国史学史上,历史学的发展传统可以追溯至12世纪初的《往年纪事》,“一般认为1113年编纂的《往年纪事》是基辅罗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编年体通史”【50】。自此以后,以修道院为修史主体,以俄国王公为俄国修史事业的主要支持者,编年史编修成为俄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学术实践。《往年纪事》之后出现的由诺夫哥罗德教会修士编写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索菲亚编年史》,既记录了世俗的政治事务发展历程,也承载了神职人员本身信奉的神意历史观念。在编年史这一史学体裁之下,14世纪出现了修士拉夫连季编写的《拉夫连季编年史》,15世纪出现了由都主教福季主持编写的《全罗斯编年史》,16世纪出现了著名的《尼康编年史》,17世纪出现了《新编年史》。俄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系列编年史,从世俗王公政治和莫斯科国家的角度来看,确实保存了俄国古代政治发展历程的有关信息。克柳切夫斯基就此评论道,俄国编年史家“确定了历史叙述的特点,创立了历史叙述的体裁,建构了严密而完整的世界历史观”【51】。但是,如前所述,从另一方面看,这一系列编年史的直接实践者和编写者是教会神职人员,由此赋予这些编年史以神本主义特色。俄国哲学家С.Л.弗兰克的分析表明了这种状况,“在俄国,最初的国家政权不是从世俗化和神权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是产生于东正教信仰内部”【52】。从这些俄国编年史体现的宗教面相来看,可以类比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史学观。在这一前提下,12至17世纪的俄国编年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其中记录的人类事件和历程看作上帝意志的注脚。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这一时段内俄国历史学发展的特征,也是俄国历史学还未走上专业化道路的表现。
刘爽《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兼论俄罗斯史学的功能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封面。
克柳切夫斯基以《始初编年史》展开的俄国史学史分析,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俄国史学发展史的认知。可以说,《始初编年史》之后出现的各种编年史作品在成书体例、内容和方法上,都沿袭了《始初编年史》的做法。从12世纪至17世纪这五百年,可以看作俄国史学史上的编年史时期。克柳切夫斯基不仅指出了《始初编年史》在这一漫长时期史学编纂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准确地判定了这一时期俄国编年史宗教属性和世俗属性并存的特征:“佩切尔斯基修道院就像一个聚光点,将罗斯生活的众多分散的光线汇聚起来。在这些汇聚起来的光线照耀下,一个善于观察的僧侣比任何一个世俗的人能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罗斯世界。”【53】在这类描述和判断中,克柳切夫斯基阐明的是,修道院是俄国编年史编纂中心,僧侣是直接负责史书编纂的主体。应该说,克柳切夫斯基的这一认知为国内学界认识18世纪之前的俄国史学史发展历程提供了一条线索和一把钥匙。从国内学界有关这一时段的俄国史学史研究成果来看,克柳切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认可和传承。可以看到,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以不同方式和自觉程度叙述了18世纪之前的俄国史学史。这不仅为他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史学史支撑,也为俄国史学史书写保留了重要素材。
结 语
相较于他的老师索洛维约夫而言,作为学生的克柳切夫斯基在回溯俄国历史过程中,将研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向,也是克柳切夫斯基在索洛维约夫基础上推动国家学派史学研究继续发展的表现。具体而言,索洛维约夫前述从地理环境、宗教传播、殖民过程和国家形成等方面呈现的俄国历史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外部的”西欧国家的历史历程为标杆和评价标准的。就历史观念角度来说,索洛维约夫虽呈现了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独特性,但“西方化”立场仍是他历史意识的一个主要面相。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解释俄国历史的角度和核心术语沿袭了索洛维约夫,但更着重从俄国“内部的”历史历程进行解释和评价。米留科夫回忆他在第一次与他的老师克柳切夫斯基见面时,克柳切夫斯基向他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是什么?即使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前两讲仍回答着这个问题……这些需求或要求包括,拒绝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从外部提出的计划或目标;每个想要研究俄国历史的学生’要从一个共同的科学问题——人类社会内部的有机演化——出发研究一切。’”【54】克柳切夫斯基这里所谓的“内部”不仅是俄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进程和事件,而且指“从俄国看俄国”的价值评判立场。在俄国思想史上,由此呈现的状况是:从恰达耶夫“完全肯定西方,完全否定俄国”的立场,到索洛维约夫“着眼俄国与西方共性的同时呈现俄国特性,从西方看俄国”,再到克柳切夫斯基“从内部解释俄国史,从俄国看俄国”。这一系列学术人物和思想立场的传承,体现了西方派和隶属于西方派的国家学派的思想谱系,也从历史解释角度展示出这些代表人物之间的差异。这些学术共性和差异的呈现是各个学者所处时代和学术环境塑造的结果,也是本文从史学比较角度论述的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国家学派发展史和俄国史学史上所处地位的独特标识。
在历史学方面,当时在俄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尼·米·卡拉姆津于1816年至1829年间出版的12卷《俄罗斯国家史》。该书文辞优美,句法精炼,但缺少历史学著作必备的准确性,不注重原始史料的运用。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在史实描述中反映出高超的文学才能……甚至含有艺术夸张的成分”【55】。卡拉姆津在俄国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但他的文学风格使他的历史研究缺乏理性的评判和思考。如前所述,索洛维约夫与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研究中表现了明确的史学史意识。这也是两者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史料意识的体现。他们整理俄国史学史的过程,也是收集和分类俄国历史研究可靠史料的过程。这种史学史意识反过来又为他们各自的国家观言说和历史分期观点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俄国史学史时间线上,两者的这一做法弥补了卡拉姆津史学研究专业性不足的缺憾,赋予俄国历史研究专业性。从这一角度衡量,从索洛维约夫到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国家学派发展历程,也是俄国史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的历程。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以及图片配文均由作者提供,在此致谢!)
【1】曹维安:《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31页。
【2】张蓉初:《译者序》,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张草纫、浦允南译:《俄国史教程》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ⅵ页。
【3】斯图尔特·麦金泰尔等主编,岳秀坤等译:《牛津历史著作史》第4卷上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391~3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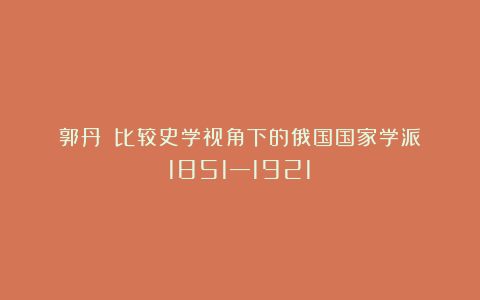
【4】卡尔·雷德尔:“谢·米·索洛维约夫与多民族史”(Carl W.Reddel,“S.M.Solov’ev and Multi-national History”),《俄国史》(Russian History)第13卷第4期(1986年冬季),第355~366页。
【5】马克·巴辛:“特纳、索洛维约夫和’边疆假说’:开放空间的民族主义意义”(Mark Bassin,“Turner,Solov’ev and ‘Frontier Hypothesis’:The Nationalist Signification of Open Spaces”),《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65卷第3期(1993年9月),第473~511页。
【6】罗伯特·伯恩斯:“克柳切夫斯基论俄国多民族国家”(Robert Byrnes,“Kliuchevskii on the Multi-national Russian State”),《俄国史》(Russian History)第13卷第4期(1986年冬季),第313~330页。
【7】Л.П.贝尔科维茨:“Г.Ф.米勒的俄国史学史评价”(Белковец Л.П.,“Г.Ф.Миллер в оценк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88年第12期,第111~122页。
【8】В.А.基塔耶夫:“重估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Китаев 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щкола в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время переоценки”),《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5年第3期,第161~165页。
【9】Ш.希利:“谢·米·索洛维约夫’殖民’理论的出现和来源”(Сили Ш.,“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источники теории《Колонизации》С.М.Соловьева”),《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年第6期,第150~154页。
【10】С.А.尼基丁:“俄国帝国历史学会”(Никитин С.А.,“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рус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7年第3期,第3~19页。
【11】Т.埃蒙斯:“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Эммонс Т.,“Ключевский и его ученики”),《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0年第10期,第45~61页。
【12】刘爽:《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75~83页。
【13】周厚琴、曹维安:《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对古罗斯文明的研究》,《世界历史》2012年第4期,第98~110页。
【14】郭丹、周巩固:《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理念及其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7~127页。
【15】朱剑利:《论克柳切夫斯基的学术思想》,《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61~65页。
【16】曹维安:《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第33页。
【17】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1卷(Соловьев 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Тома 1),莫斯科:社会经济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18】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Ключевский В.O.,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Часть 1),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79、88页。
【19】郭丹、周巩固:《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理念及其价值》,《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1页。
【20】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Ключевский В.O.,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Часть 1),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79、88页。
【21】С.С.德米特里耶夫,И.Д.科瓦尔琴科:“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他的生活、工作、科学遗产”(Дмитриевым С.С.,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Д.,“Историк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ев.его жизнь,труды,науч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1卷(Соловьев 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Тома 1),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按,这处引文源自1988年至1989年出版的《远古以来俄国史》8卷选集,该版本仅在此处被征引一次。本文其他各处《远古以来俄国史》引文,均出自1959至1966年出版的该书29卷全集。
【22】Ш.希利:“谢·米·索洛维约夫’殖民’理论的出现和来源”,《历史问题》2002年第6期,第153页。
【23】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Ключевский В.O.,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Часть 1),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79、88页。
【24】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2卷(Соловьев 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Тома 2),莫斯科:社会经济出版社1959年版,第344页。
【25】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79~198、378、378、42页。
【26】Ш.希利:“谢·米·索洛维约夫’殖民’理论的出现和来源”,《历史问题》2002年第6期,第152页。
【27】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79~198、378、378、42页。
【28】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79~198、378、378、42页。
【29】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1卷,第59页。
【30】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79~198、378、378、42页。
【31】尼古拉·卡拉姆津著,安德·卡恩译:《俄国旅行者信札》(Nikolai Karamzin,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牛津:伏尔泰基金会2003年版,第294页。转引自斯图尔特·麦金泰尔等主编,岳秀坤等译:《牛津历史著作史》第4卷上册,第381~382页。
【32】【33】【34】【35】【36】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4卷(Соловьев 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Тома 4),莫斯科:社会经济出版社1960年版,第651、651、651、652~653、651~652页。
【37】【38】【39】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4卷,第653、653、655页。
【40】张荣初:《译者序》,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ⅶ页。
【41】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40页。
【42】【43】Т.埃蒙斯:“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历史问题》1990年第10期,第48、49页。
【44】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379页。
【45】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1卷,第60页。
【46】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第4卷,第638页。
【47】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04页。
【48】表格具体内容参见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96~100页。
【49】朱寰、胡敦伟:“译者前言”,拉夫连季编,朱寰、胡敦伟译:《往年纪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ⅲ页。
【50】刘爽:《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兼论俄罗斯史学的功能与特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51】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91、100页。
【52】С.Л.弗兰克:《俄国革命的宗教历史意义》,В.索洛维约夫等著,贾泽林、李树柏译:《俄罗斯思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53】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91、100页。
【54】Т.埃蒙斯:“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历史问题》1990年第10期,第47页。
【55】戴桂菊:《尼·米·卡拉姆津——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第95页。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9期
编辑:赵俊华
审核:安 瑞
监制:苗书梅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