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北京钓鱼台——阿普,你快看,门口是谁?”廖承志嘴角一勾,指着空荡荡的门口。经普椿顺着手势回头,什么都没看见,再回座位时,丈夫已经把那小块晶亮的肥肉吞得干干净净。“我可什么都没吃。”他眨了眨眼。圆桌旁的几位西方客人先是愣住,随即大笑,气氛一下子被点燃。
那一年,廖承志做完冠状动脉搭桥术回国不久。医生留下两句箴言:少油、忌烟。可七尺男儿碰上肥肉,总有点割舍不下。经普椿坚决执行医嘱,筷子像警棍一样寸步不离。廖承志只好动脑子,才有了这场“小戏法”。举动稚气,却把两人四十二年的深情写得淋漓。邓小平听说此事,闲谈时调侃:“老廖是’妻管严’。”廖承志哈哈一笑:“好管,管的是命。”
镜头倒回四十七年前。1933年春,上海。16岁的经普椿第一次走进何香凝家,端水、扫地、陪老人说话。那时廖承志正因地下工作被关在南京老虎洞,生死未卜。谁也想不到,这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小姑娘,会成为他此生的牵挂。
当年秋末,廖承志获救返回上海,在母亲病榻旁见到了阿普。她耐心熬药、帮忙翻身,一双眼睛澄澈得像装不下杂质的泉水。情愫悄悄冒芽,但时代不给恋人闲情。两个月后,他接到去川陕苏区的指令,只来得及塞进信封一句话:若真心,请等我两年。
两年被战争轻易拉长。长征转战、延安窑洞,他走过千山万水,那封回信却始终没落到手里。直到1937年夏,他收到母亲来信:“阿普未嫁。”这一句话让他在七月的延河畔激动得直咳。毛泽东知道此事,递给他一支烟,说:“革命让人分离,也让人重逢,你再写一封吧。”他当天就写:我身心如昔,望勉力进步,共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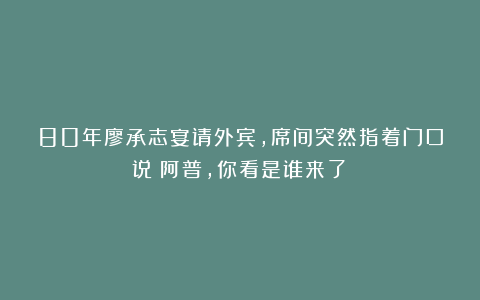
香港成为两人真正的聚首地。1938年1月,轮船靠岸,他隔着人群喊“阿普”,嗓音带着久违的颤抖。他们在皇后大道租下小屋,前面卖茶,后面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经普椿既是夫人,也是情报联络员,深夜守着暗号与密电。日军特务来敲门,她会冷静地把茶叶样本推到对方面前:“买茶还是抄家?”一句话往往让对方尴尬离去。
然而战场并未停歇。1942年,廖承志在乐昌被捕,关押泰和马家洲集中营。酷刑、暗杀、美人计轮番上阵,他在墙皮剥落的牢房里写下《诀普椿》:“应为女中杰,莫图空节名。”那是至暗时刻的托付,也是绝不言败的宣言。
1946年春,他被营救出狱。重庆街头,他在《新华日报》刊登短短几十字:廖承志寻阿普。三天后,他听到熟悉的脚步声。经普椿从成都赶来,一句话没说,先摸了摸他瘦到凸出的肩胛骨,眼眶瞬间湿透。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先后主管侨务、对外友协,日程排得像脚本。夜深时,他常推开家门,悄悄问一句:“阿普,醒着吗?”经普椿会点灯,把热汤递到手边。医嘱上的“少油”成了家里雷打不动的戒律,连女儿都记得父亲对肥肉的两难表情。偶尔,廖承志躲到阳台叼一支烟,还没点着,就听见身后轻咳,他立刻举手投降:“缴枪不杀。”
1983年6月10日,首都医院。仪器灯光闪烁那一刻,他的脉搏停在75岁,守在病床旁的经普椿捏着他冰凉的手,声音低到只剩呼吸:“老廖,你欠我的寿面还没吃。”她知道,再无人答应。
晚年回忆录里,经普椿写道:“五十年风雨,一半坎坷,一半欢颜。”她删掉了重叠的形容,只留下数字与事实,仿佛再多情绪都不及一句“老廖叫我阿普”来得真实。
再说那顿1980年的宴请。客人散去后,经普椿在车上轻声问:“肥肉好吃吗?”廖承志呵呵直乐:“太香。但下不为例。”窗外晚风掠过,街灯把两位白发夫妻的影子拉得极长,像一部无声的纪录片,播的是相守,写的却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