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0年前的冠冕谢幕,谁会在意?在灵宝铸鼎原那个叫西坡的小聚落,盛夏的一个清晨,人们悄悄走向中央广场,像是一场家族的默契。野茉莉花早已凋零,但空气里还残存着什么未完的事情。前一晚,一张熟悉的脸突然消失了,这个人不是普通村民——他的离世,在村中好比天塌了一角。那一天的葬礼,成了我们窥见庙底沟时代秘密的一个微光口子。
现如今,西坡不过是晋陕豫交界处一块遍布苹果树的小村,村里人,从田地里带着泥巴抽空唠嗑,谁还记得脚下曾是五千年前的“世界中心”?没人。祖辈们也许偶尔说起那座黄帝的“衣冠冢”,但剩下的记忆就像苹果香气一样,随风消散在山坡。可这片土地,曾是真正热闹的地方——二十多个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围绕着西坡,像一场史前的大集市。
真正让这场故事有味道的,是考古人蹲下身子,拿着小铲子,耐心挖一点土,看看能不能从西坡找出点过去的痕迹。聚落被沟壑和河流环成一个圈,广场四角半地穴房屋像守护者,整个村子像是被专门设计过的。想象一下,5300年前的晨曦下,村民们从各自低矮的土屋出来,走向广场中央。大家默然排队,等着为那个“重要人物”送行。没人搭话,大概只有脚踩黄土的声音。生活就是这样,平时谁也不言语,可到了某个节点,全村人都得来。
庙底沟,彩陶的时代。其实,谈起中国文明,更像是在饭桌上反复端出一道老菜,几百年了还剩下相同的花样:鸟、鱼、花,有的图案像极了乡下阿婆织布时随手画的凤鸟,有的排列又像水塘边看见的水草。彩陶风行北至长城、南到长江,东抵大海,西出甘青——当时的人们,也许隔着千里看到彼此的纹样,心里不禁犯嘀咕:“那个村子会不会也有我的亲戚?”考古圈里流行说这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浪潮。我倒觉得,或许本质上就是“谁家彩陶最花哨,谁家孩子今年娶不上媳妇”,大家学得格外起劲。
可别以为彩陶就是那些老瓷瓶的事儿。在20世纪之前,庙底沟文化就像只剩花瓶的家史,没有人知道这些制陶的手是怎样的人,什么脾气,什么身份——他们究竟想什么?是光想炫耀,还是有着别的心事?这些谜,说起来像小镇传八卦,总在等有一天能真相大白。
史前文化那阵子,拼的可不是一村一陶那么简单。辽宁西部的红山,庄重得像古村落的大祭坛;往下游走,大汶口,“富人”都用象牙做发饰,简直是在显摆。安徽凌家滩,“土豪”们玉器多得能填满墓床。那年月,分界线像村头那条小河:谁家房子盖得多,谁家墓穴铺得厚,谁就有话语权。中原往往被讲成是龙的故乡,可考古人拿着刷子扫来扫去,彩陶之外没什么能与四野比拼的“炫技”。这就像大年夜,四邻八乡烟花齐放,中原这儿,只点一根小火柴。
是中原真这么寡淡?苏秉琦先生于是就说了句“满天星斗”,他意思是:咱们文明不是单一的树,是一片杂乱生长的丛林。可也有人不服,想看看中原到底还有什么秘密没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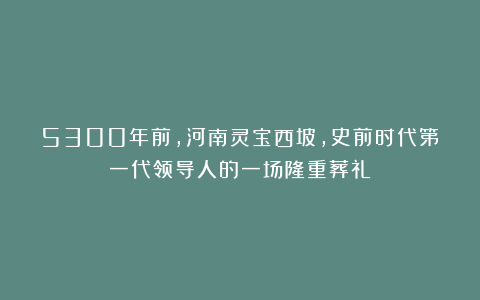
1999年的一春,考古队穿着泥靴,一路踩到灵宝西坡。历史里说黄帝就在铸鼎原铸过鼎,可考古人不吃这套神话,还是盯紧地上的土坑和陶片。经过统计,铸鼎原聚落分了等级,大村小村互为依存。北阳平最大,西坡紧随其后,而那五十万平方米的西坡现存最好,像是岁月特有的眷顾。等级化聚落,就像咱们如今的小镇,有了县城就有镇,有镇就有村。这细枝末节,其实也能从侧面看出社会分化:谁家土地多,谁家权力大,是社会进步的缩影。
钻探开始,考古人像做工的老汉,一层层往下挖。2001到2002年,在聚落中心发现一处大房子,编号叫F105,光室内面积就能请上几百人吃席,大到能办村头庙会。2004年又捅开了一处五边形半地穴房屋(F106),设计复杂,地面是七层泥巴铺成的,就连墙上、柱子上也满是刷过的红色颜料。说起来,这房子不是盖给普通人的。就像谁家祖上传下的老院,平常人进都不敢进一脚。
像F105这样的房子,有学者算过,一百多号人得干上三个月。这么大的工程,只为上层用。“大会堂”或“黄帝的宫殿”?谁知道呢。反正用途绝不是平日里接待亲家,估计是祭祀、议事的所在。
我们讲回葬礼的那天。茉莉花谢,像是命运的伏笔。西坡的居民低头把消息传出,有威望的、躲在苹果树下耍脾气的、田埂上忙活的,都知道得有个不寻常的送别。整个葬礼,大概连邻近村子都被惊动。隆重,不光是纪念逝者——也是社会阶层在舞台上的一次亮相。身份、地位都要在这天亮出来。
2004年,就在南部壕沟外,考古队找到了墓地。接下来发掘,三十多座墓葬,主角就在其中,编号M27。细致研究后发现,墓主165厘米高,三十来岁。身子裹着麻布,锁骨歪斜,膝盖之间只剩一指宽的缝隙,还能感受到包裹的紧密。墓穴朝向偏西——是不是为了傍晚落日?没人明说。埋尸填土的泥里夹杂着各种树叶、果实,尤以野茉莉的小果最为醒目。复原葬礼的时间线,靠这微小的线索串了起来。木板铺在墓口上,盖着精细的麻布和朱砂,起个辟邪、敬祭的作用。两个大口缸,沿口也抹了朱砂,估计是地位象征。
葬礼流程很长,大家从广场走出,穿过壕沟,来到墓地围成圈。尸身安放在墓室中央,随葬品规矩放在脚下。麻布、木板一层层覆盖,最后用泥土封好,堆起坟丘。那一瞬,所有的仪式都落了地。
那么,这墓主究竟是谁?35岁男子,身高适中,但最扎眼的,是那两颗没有了的下门齿——这不是意外,生前拔掉的,算是“潮流风尚”。黄河下游也流行这类习俗。肋骨曾断过,愈合痕迹说明人家不是体弱书生,搞不好是村里参加某种角力、竞技活动的健将。胃里曾有过大量寄生虫卵,吃猪肉比别人大得多。这猪肉,不是逢年过节,普通人没人常吃。大口缸随葬——并非人人有份。这些道道,专属于“领导层”:能号令一百人搭房子,能在邻村葬礼上当嘉宾。
头骨和另一个大型墓M8形态近似,大概率是同一家族。史前的“官二代”,大约就是这样传权传位。谁说五千年前就没阶层?
而且这种“领导人”不只西坡有,红山各地祭祀中心,女神庙里的贵族,大汶口的权杖与象牙,凌家滩的玉猪,都是同一时代的“超级玩家”。北方注重宗教仪式,东方吆喝精美随葬品,南方玉器烂漫一地,中原却一点也不铺张。西坡M27里就十来件陶器,最能体现身份的还是那两个大口缸。是不是因为中原这地方早就“重实不重奢”?大项目、大房屋,大聚落更能说明地位。
更妙的是,这些高等级墓葬之间的器物,隐隐有交流。比如大口缸,河南、山东、安徽、环太湖几处都有类似款式,用的不光是器物本身,也许是葬礼同一套礼仪,被不同地方模仿、认同。红山与凌家滩的玉器样式也极其相近,这不是流传,更像是当时的领导者互访,带来的经验和“技术转让”,像我们小时候村里几个能工巧匠串门学艺。
这些交流,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我们的圈子”。当时,西坡的主人公或许曾在大型建筑里讲述自己千里之外的见闻,画出类似《山海经》里的“地图”,把一路的奇闻异事告诉聚落同伴。大家围着火堆,听他讲外地的玉器、异样的图案,脸上是又惊又羡的表情。领导者走南闯北,带回的不只物品,更多是“天下”的概念——咱们不是各自为政,是有交流、有互动的小世界。
“最初的中国”,其实就是一群互相串门、偶尔比拼但也彼此认同的聚落领导者。五千多年前,“程序”已经被悄悄按下——后世的文明能走这么远,和那时的交流、组织、工程有脱不了的联系。
三皇五帝到底是不是神话?没人能给准信,但看着这些“超级大墓”留下的证据,你不禁怀疑传说是不是也沾上了点真事。英雄业绩,也许就是一场隆重的葬礼、一座庄严的房屋。西坡仍在发掘,土里还藏着故事。考古人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刮去每一层泥,一点点还原那个时代的热闹与深情。我们今天走在灵宝苹果林的小路上,不知不觉踩过了五千年前的“舞台”。
失落、团结、探索……人类的根,总在这些无声的大事和无人可辨的小细节中,悄悄地被保存着。也许,真正的“文明根系”,就藏在一场夏末沉默的送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