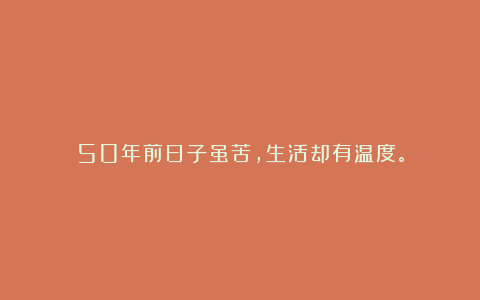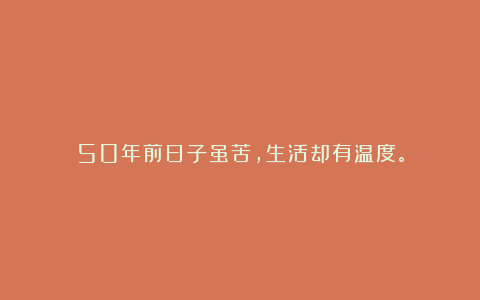 月光洒在窗台,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还愿意回到50年前吗?那时,父亲刚进机床厂当学徒,母亲在街道办的缝纫社踩着踏板机,他们的青春裹在蓝布工装里,像墙角那株总也浇不蔫的仙人掌,带着粗粝的生命力。
若真能穿过时光的褶皱,最先撞见的该是清晨的公共水龙头。铝制脸盆碰撞的脆响里,张婶会塞给母亲半块肥皂,李叔扛着扁担哼着《东方红》去挑水。那时没有智能闹钟,却有此起彼伏的开门声,邻居们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织成一张细密的网,把每个家庭都兜在里面。不像现在,对门住了三年,还记不清对方的长相。
工厂的广播喇叭该是另一重记忆。父亲说,那时的天总比现在蓝,烟囱里冒出的烟也是直的。车间里的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颤,却盖不过工人们的号子声。谁要是革新了技术,名字能在厂报上挂半个月,食堂会多给俩白面馒头当奖励。不像现在,办公室的空调吹得人发冷,KPI 像悬在头顶的钟摆,敲得人心里发慌。
最让人念旧的,该是那些带着温度的票证。粮本上的数字精确到两,布票要攒着给孩子做新衣,就连买块肥皂都得托熟人。母亲总说,那时的日子像本明细账,一分一厘都要算计着过,可人心却亮堂。邻居家包了饺子,定会端来一碗;谁要是生了病,全楼的人都要跑去探望。不像现在,手机里存着几百个联系人,真正能说上话的,却没几个。
可真要回去,怕是也难。想起父亲手上的老茧,母亲眼角的细纹,那些被岁月磨出的痕迹里,藏着多少不易。冬天没有暖气,要靠煤球炉取暖,早上醒来,被角总结着层白霜;夏天没有空调,摇着蒲扇整夜难眠,天亮时浑身是汗。买台缝纫机要攒半年工资,看场电影得提前三天排队,想给远方的亲戚寄封信,要等上半个月才能收到回信。
更让人犹豫的,是那些被时代框住的可能。父亲总说,要是当年能考大学,他想当工程师。可那时的命运,像被按在既定轨道上的火车,很少有转轨的机会。不像现在,你可以辞职去学画画,也能背着包去周游世界,哪怕失败了,也有人说 “从头再来”。
月光洒在窗台,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还愿意回到50年前吗?那时,父亲刚进机床厂当学徒,母亲在街道办的缝纫社踩着踏板机,他们的青春裹在蓝布工装里,像墙角那株总也浇不蔫的仙人掌,带着粗粝的生命力。
若真能穿过时光的褶皱,最先撞见的该是清晨的公共水龙头。铝制脸盆碰撞的脆响里,张婶会塞给母亲半块肥皂,李叔扛着扁担哼着《东方红》去挑水。那时没有智能闹钟,却有此起彼伏的开门声,邻居们的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织成一张细密的网,把每个家庭都兜在里面。不像现在,对门住了三年,还记不清对方的长相。
工厂的广播喇叭该是另一重记忆。父亲说,那时的天总比现在蓝,烟囱里冒出的烟也是直的。车间里的轰鸣声震得人耳膜发颤,却盖不过工人们的号子声。谁要是革新了技术,名字能在厂报上挂半个月,食堂会多给俩白面馒头当奖励。不像现在,办公室的空调吹得人发冷,KPI 像悬在头顶的钟摆,敲得人心里发慌。
最让人念旧的,该是那些带着温度的票证。粮本上的数字精确到两,布票要攒着给孩子做新衣,就连买块肥皂都得托熟人。母亲总说,那时的日子像本明细账,一分一厘都要算计着过,可人心却亮堂。邻居家包了饺子,定会端来一碗;谁要是生了病,全楼的人都要跑去探望。不像现在,手机里存着几百个联系人,真正能说上话的,却没几个。
可真要回去,怕是也难。想起父亲手上的老茧,母亲眼角的细纹,那些被岁月磨出的痕迹里,藏着多少不易。冬天没有暖气,要靠煤球炉取暖,早上醒来,被角总结着层白霜;夏天没有空调,摇着蒲扇整夜难眠,天亮时浑身是汗。买台缝纫机要攒半年工资,看场电影得提前三天排队,想给远方的亲戚寄封信,要等上半个月才能收到回信。
更让人犹豫的,是那些被时代框住的可能。父亲总说,要是当年能考大学,他想当工程师。可那时的命运,像被按在既定轨道上的火车,很少有转轨的机会。不像现在,你可以辞职去学画画,也能背着包去周游世界,哪怕失败了,也有人说 “从头再来”。
那日整理旧物,翻出父亲的工作证。黑白照片上的青年眉眼清亮,胸前的钢笔别得笔直。忽然明白,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某个具体的年代,而是那时的纯粹与热忱。是邻里间无需设防的真诚,是为了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执着,是物质匮乏却精神丰盈的踏实。
若真能回去,我想在傍晚的路灯下,看父亲和工友们讨论技术革新;想在周末的操场边,听母亲和姐妹们唱《南泥湾》;想在供销社的柜台前,感受攥着票证期待的雀跃。但我知道,这终究只是念想。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馈赠与局限,就像现在的我们,既有网络世界的便捷,也有钢筋森林的疏离。
晨光爬上书桌时,我轻轻合上父亲的工作证。或许,最好的选择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带着那些珍贵的记忆,把当下的日子过得有温度。就像母亲说的,日子好不好,不在有多少东西,而在心里亮不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