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的一个深夜,太行山上刮着刺骨寒风,八路军前线总部却刚结束一场痛痛快快的军民联欢。灯火熄灭后,山谷里本该只剩犬吠与哨声,谁料一记短促的枪响划破夜空,把所有人惊得浑身一激灵。冲进警卫宿舍的人看见,二十出头的警卫员王满新仰面倒在床板上,手还扣着扳机,血迹顺着枕边流下。
现场极静,只有一种几乎听不出来的颤抖——王满新的未婚妻梅芳捂住嘴站在角落,双肩抖得像筛子。保卫部长杨奇清随后赶到,他蹲下扫视地面,没有凌乱的搏斗痕迹,也没有撕扯的衣角,唯独一只被撕碎的彩荷包赫然在侧。经验告诉他,这事绝不会只是“丢人现眼”那么简单。
次日破晓前,杨奇清把梅芳单独带到值班室。煤油灯跳了一下火苗,昏黄光线里,梅芳抽噎着陈述:“俺跟满新在屋里,被人撞见不正当关系,他一时想不开……”这套说辞语气流畅得近乎排练,杨奇清听完没吭声,只在记录本上画了个圈。他心里清楚,王满新是全团公认的老实人,条令背得滚瓜烂熟,自尊心强,却不至于为这一点脸面开枪自尽。
三年前的那枚流弹忽然闪进他脑海——彭德怀在前沿指挥时险被击中,正是王满新飞身一挡,才保住了彭副总司令的性命。也难怪彭德怀在听完汇报后只说了一句:“他救过我,必须彻查。”命令一出,前线总部的保卫力量全体动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案子很快出现突破。第三天清晨,情报员在镇上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逮住了梅芳与一名年轻男子碰头。男子递出一本《古文观止》,梅芳动作娴熟地塞进挎包,便要起身离开。桌上那瓶高粱还没开封,四名便衣已前后卡住出口。
经讯问,《古文观止》不是读物,而是日军“益子挺进队”用于交接暗号的道具。青年男子口风极硬,直到对比笔迹、破译暗格纸条后,才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联络员。梅芳也露出了真面目——她原本是王满新的老乡,家乡被扫荡时被日军拘押,后在利诱和恐吓下屈服,受训成为女间谍。任务只有一个:利用与王满新的婚约,寻找机会刺杀彭德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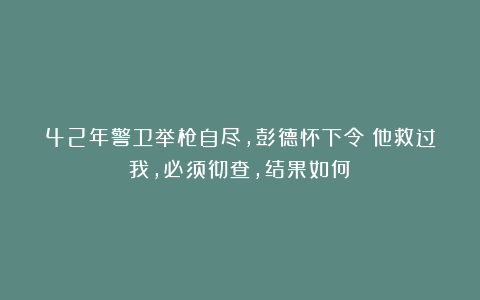
王满新的身边是刀枪不入的警戒层,外人难以接近,梅芳决定“曲线救国”——先把未婚夫拉下水,再以内部人身份制造机会。军民联欢那晚,她故意频频示好,边说边暗示王满新:只要除掉彭德怀,立刻可以携巨额赏金远走。他当即翻脸,一巴掌扇了过去,扯碎荷包准备当夜去报告。
短短几分钟内,他陷入一个极度纠结的死局。报告吧,梅芳可以反咬“一男一女不正当”抹黑自己;不报告,又无法阻止刺杀阴谋。试想一下,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兵面对如此复杂局势,精神压力有多大?最终,他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阻断梅芳:自戕。枪声响起瞬间,他既保护了首长,也保全了自身清白。
杨奇清后来在案卷里写道:“此案唯一不能弥补的是生命。”王满新的牺牲迫使保卫部重新评估情报防线,随即扩大了对“C号作战计划”的反侦察规模。不久,八路军在晋东南一带连续破获数起潜伏案件,日军暗杀行动就此折戟。
彭德怀得知真相,久久无语,只把王满新的姓名亲笔写进警卫处烈士册,叮嘱道:“警卫线就是生命线,绝不能再让年轻的枪口对准自己。”后来总部进行干部培训时,这个案子被反复提及,既是保密教育的范例也是心理防线的警示——隐蔽战线里,情感和信仰的较量往往比子弹更致命。
梅芳与那名特务最终被依法处决。档案留下两行审讯结尾:“被俘时神色恍惚,称未料到王满新宁死不屈。”这种错愕映照出游走在利益漩涡中的人对信念的低估。八路军保卫机关随即更新条令:凡警卫、通信等要害岗位,婚姻变动与亲属往来必须逐级备案,任何个人不得私自接纳“亲属”留宿。
值得一提的是,王满新的家书后来被搜出,上面只有寥寥两句:“孩儿在外一切平安,莫挂念。盼捷报传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普通士兵最质朴的心愿。恰恰是这种朴素,把他和无数年轻战士一起,焊在了抗战钢铁阵线上。
杨奇清每回翻到那封家书,总要把烟头摁灭。他对身边助手低声说过一句:“以后再听到子弹响,宁可敌人倒下,也不能让自己人先倒。”这句话并未被记录进正式文件,却在保卫系统口口相传,成了太行山间另一道无形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