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刚到深秋,北方的风仿佛总带着点儿苍凉味道。1939年11月里,有个噩耗忽然在晋察冀军区传开:白求恩医生“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死别本不是新鲜事儿,可这一次,不单是聂荣臻这样的将军,连普通的伤员、炊事员、还有那些送药的小伙子,听说后心里都塌了一块似的。“他怎么就这么去了呢?”不少老八路到现在,说起这天,还是会红着眼眶抽两口旱烟。
聂荣臻那个下午,把白求恩临终前的信拿出来,看着那密密麻麻的中文字,手指头都在抖。其实,那封遗书内容说复杂不复杂,说简单还真不简单。白求恩在信里把自己生前最后的“家当”和念想,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什么相片、日记、还有几张记者拍下来的胶片,全要转回加拿大老家。地址还清楚得很——多伦多威灵顿街十号门。可他又嘱咐托蒂姆·布克分发,生怕家里人看得太沉重,想来那份“体贴”,谁看了都得叹口气。
有意思的是,他连那两张行军床都惦记着,说让聂荣臻夫妇留着。英国皮鞋,还有马靴马裤,分别嘱咐给身边几位老朋友——吕正操、贺龙。要说这些“破烂玩意儿”没啥值钱的,可那份心意啊,却让收的人没法拿得坦然。哪怕就是张旧床、双皮鞋,那也是个念想,是一份活人替死人守着的情分。
信里头还絮叨着药品的事——这种“唠叨”,战士们最熟。他写道,要每年备好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贵也得买”。明知道买这些药,要多花两三倍的钱,他还是放不下。那年头,疟疾、贫血说发作就发作,白求恩比谁都清楚,药能救命。他嘴里骂着“没完没了的病号”,可到了熬药熬夜,还是眉头都不皱一下。别人图个名声,他却只怕落下一个。
读到信的最后一段,聂荣臻有点顶不住。说是自己“这两年”,过得既快乐又觉得有意义。可他又惦念前妻——一个远在万里以外的女人。白求恩特意请求加拿大那边的组织给前妻拨一点生活费用,还嘱咐让她知道“我其实是快乐的”。字数不多,话却有点辣嗓子。很多人问过聂荣臻,从前白求恩聊家事吗?他只说:“几乎不提。”可一切到临终,这人的柔软都化在几句话里了。
再往前追,白求恩其实是个“洋医生”,1890年降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他老家的氛围就怪正经,父亲是传教士,家里有风琴、圣经和一屋子的勤俭规矩。但小白求恩偏不走牧师路子。听说祖父就是有名的外科医生,常年赤手空拳跑遍村庄,给人割盲肠、拔牙拔到半夜,见惯了人命关天。这些“壮举”,在小白心里扎下根。
他十七岁报了医学院,学医倒是顺风顺水。后来跟护士弗兰西丝谈恋爱,两人火速结婚。别看白求恩一向勇猛,在这段婚姻里却温顺得像只猫。北美大萧条时期,医院里常见各种穷苦病人,他也曾冒着极大风险走街串巷义诊,自家甚至开过几餐救济厨房。可这段安稳说来短暂。白求恩在三十岁刚出头时突然肺里出了毛病。别的医生还在嘀咕,他早把自己胸片挂到光下——结核,跑不了。他不想把疾病传给老婆娃娃,二话不说干脆离了,自己搬到山里疗养。
在山里那几年,他试着在自己身上搞起人工气胸疗法,就是拿根管子往肺里放气,自己调试。后来人们常常提起这事,说他既是医生也是病人,这胆量,不是学来的。其实那玩意儿可危险,隔壁病人死几个,他也没慌。撑到痊愈再回多伦多,人活了、名也大了,但心却冷了半截。
有意思的是,治好病后夫妻俩折腾着复婚,过了不久又闹翻了。谁也说不清弗兰西丝是什么想的,离婚后两人却还常写信、见面,有时街坊见着,也就笑笑不问。或许,这段乱七八糟的感情,也让白求恩后来干什么都不那么“留后手”了。
到了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揣着手术包跑到马德里前线。他自己写过,“战壕下冒死做手术,死人堆里剥下还能用的纱布”。用他的话说,“咬牙救人,有时候其实是自己找罪受”。西班牙的浴血让他不光学到救伤员的办法,更看破了战争的荒唐。没几个月,他的“输血队”干得有声有色,这帮洋面孔医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少后来成为全球人道医疗骨干,那都是在炮弹泥坑里“磨出来的”。
1938年,他漂洋过海到了中国。来的时候,身边就带着一箱药,一个随身小提包。围着八路军总部转了一圈后,主动请缨要去最凶险的冀中。吕正操还记得,见他第一顿饭,就端上几样炖菜、窝窝头。白求恩看也不看,扒拉几口就往救护队跑。说到底,这个加拿大医生一天天没个闲着。手术、讲课、写病案,连夜猫子都没他精神头好。“为啥不累?”有人问。吕正操回忆他只回一句:“战士等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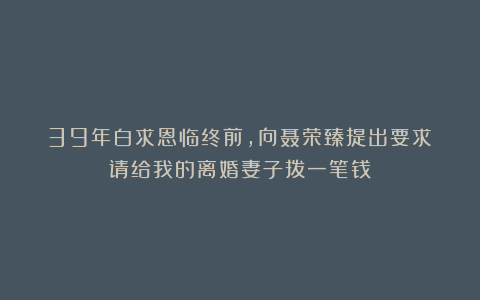
这一点,其实在许多老战士心里留下记忆。宋家庄一仗,八路军大胜,3000米外就是前沿阵地,白求恩在帐篷里带着十几个中国乡村医生连夜剥土豆皮那样给伤员刮创口,外头炮火都快把油灯打灭了,他连头都不抬一下。他指挥着用苇席、破布做急救带,还中英文夹杂骂着战壕太窄、夹板太短。可只要看到成排伤员不必截肢、能走出战场,白求恩就笑得像个大孩子。
说起齐会那三天三夜,连八路军最硬气的卫生兵都服气。白求恩连续做了上百台手术,饭菜端来他拿消毒水一洗就吃。睡觉?压根没工夫。战士们背地哭,说“老白扒层皮救咱们命,他自己一瘦都成皮包骨头了。”恰巧那阵正是他四十九岁生日,别人生曰子,他台灯下照着病脚缝,连蛋糕都没看上一眼。
“他是个能把自己耗干的人。”后来,吕正操再回忆,常常一句带哭腔。其实白求恩自己心里有数,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过,“我这年龄,在这,算老战士了。”乍一听有人当作自豪,其实是无奈——战场上活过几十的能有几个?看多了年轻人牺牲,白求恩也变得少说多做。
与其说他是医术高明,倒不如讲他为救命什么都能想。他带头做血库,发动整个村子抽血救人。为了推广无影灯、还有卢沟桥式野战担架,用铁丝、木料和衣背心就地取材,硬生生把欧洲先进办法嫁接到华北小村庄。有人调侃他太抠门,其实白求恩把分文不剩的钱全用买药、缝线去了。有一回他亲自给自己抽血,又要去手术台继续干活,助手险些拦不住。
不幸的是,他还是没熬过最后一关。1939年早冬,某次紧急手术里刀意外划破了手指。按说,这种情节很多电影都拍过,只有真正在前线做过野战医生的,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土、汗、血、细菌,伤口根本顾不得细说消毒,抗生素又远远不够,败血症很快席卷全身。他知道后果,也不休息,实在扛不住才躺下。
最后一次与吕正操见面是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那天白求恩又瘦了一圈,走路能听见鞋底嗒嗒响。他没多寒暄,边聊边听炮声,一听爆炸,拎起急救箱一溜烟冲出门。吕正操气得追不上,后来只能摇摇头说“这人没救了,他心都系到战士身上去了……”
白求恩短短一年多,把自己一双手和一桶热血都留在了中国。有熟悉的兵说:“老白没打过枪,可救的命、挡的子弹,比谁都多。”这一点,就是后来每个医学院都会立雕像、每家烈士陵园会竖铜牌的根本原因。他一生没剩下什么值钱玩意儿,死时手头只剩下一点医疗笔记、几双旧鞋、几袋药瓶。能留给前妻的,也只有一笔向组织“请求”的补助。
后来石家庄修了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国医学院都树他铜像。讲这段故事,没人说“伟大”两个字,反倒更多人念叨,“这样的人,这样做事,这样待人,咱以后还见不见?”白求恩,那个不肯停歇的洋医生,那个写下“快乐日子”却把快乐埋在土地下的人——如今只留下一地风声,让后来的人在静下心去听时,突然湿了眼角。
世事漂泊,有些人的存在,注定不能被冠上“成功”“圆满”这些字眼。白求恩,这位把命交给中国土地的医生,他留下的,是我们的乡愁和敬意——一直不会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