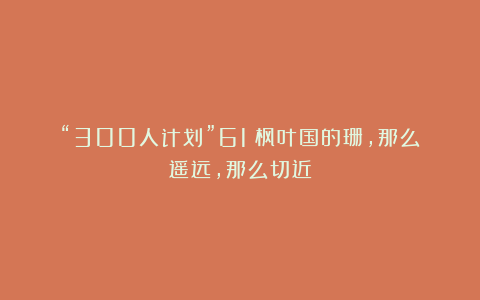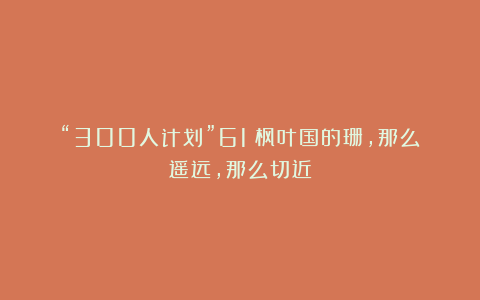|
枫叶国的珊,那么遥远,那么切近
珊算是班上甚至学校的风云人物。她家是老南京,住在城南瑞金新村,父母是南京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和工程师。她的起点在我们许多人之上,所以没有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人的局促、羞怯与自卑,不会也不用像我们那样习惯性地低头和人说话。
她风一样地穿梭在校园里,松弛而自由,这样落落大方地做自己,正是我的向往和期待。
她几乎能轻松地与所有人说上话,包括一些我仰望而不得靠近的。这让我一度有些气馁,甚至嫉妒,便选择了远远地站立,冷冷地旁观。
她去演话剧《雷雨》,她去紫金山跳舞,她和别的班、别的系同学打得火热……我们在彼此的世界之外。
她的热与我的冷、她的高光与我的寂寞,像两个平行的世界,很长时间都没有过交集。
但三观相似,总是有种莫名的感觉让心暗戳戳地联结着。
有次登紫金山,我们刚好站在一起,我们看着同一个远方,感慨了同样的世界和同样的美。
毕业后她留校,参与了学校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创建,她是那个学院的元老之一(所以这次聚会,我特意去拍了新闻学院大楼和新闻学院第一届学生捐赠的长凳,发给她)。
毕业后,偶然地,我们联系上,她说“我要去栖霞看你”。当时郊区车要晃晃悠悠两个多钟头,路很颠簸,还很难挤到座位。当她抱着一个有半米多长的长毛绒狗狗站在我宿舍时,我欢喜地把我人生第一个大公仔抱进了怀里,同时用一个灵魂拥抱了另一个灵魂。
我们在那个土屋里聊了些啥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只公仔陪伴了我,又接着陪伴了我儿子。
后来,她去苜蓿园看我儿子啃自己的胖脚丫,我去瑞金新村吃她妈妈做的素鸡;她把北京爱情交给我保管,我把南京爱情交给她评判;我们用一个不寐的长夜去探讨人生,又用紧俏的一个白日去丈量中山陵的梧桐道……
两颗心的接近原本就没有那么复杂,交换过一些思想、分享过一些故事,再共度过一些时光,足矣。
1989年夏天,“春天的故事”刚刚结束,她过来跟我说:她要出国,去加拿大。
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家园,怎么舍得?我远在郊区都还没想着挪窝,她却把到手的一切说扔就扔了。都说“舍得舍得”,“舍”是为得,但她却不是冲着“得”,而是冲着未知、陌生、遥远,以及一切新的可能。
这么早就超越物质奔形而上去了,让在俗世里每日斤斤计较长短得失的我,惭愧。
一个文科生,她在那里竟然修了高等数学,懂了微积分,去金融行业做了理财顾问,干着很专业的活,拿着很高的薪水,受很多人的追捧。太不可思议、太超乎想象了。
五十岁过后,她嫌金融业节奏太快,又改行去做了私校老师,时间自由,假期充足。看她在学生毕业时被包围、被依偎的画面,满满的快乐与自豪。
跳舞是她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跳着跳着,就跳到了高处,最后拿了多伦多舞蹈节的大奖,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看她穿着高跟鞋、在华丽丽的舞台上丝滑地移步、旋转、摆头,简直酷毙了。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珊,她的阶梯下,是清一色的白人。
疫情那年她去南极,拍美到极致的冰川和企鹅。在这之前,她的足迹已遍布全世界,她在南美的沙滩晒太阳,在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在北欧看极光……她替我摄取了我向往的那些画面。
从一名大学新闻系老师,到一名金融分析师,到私校老师,到舞者、行者,她就是我心中的六边形战士。
每一件事她都做得认真、做得出色,做得有滋有味又精彩纷呈,不潦草、不将就、不虚空。与每一段时光都友好相处,与这世界的每个侧脸、每幅断面,都安然相拥。
南京“大萝卜”,本就开阔;时空转换、岁月打磨后,更是宽广。
她经历过不同的爱情,既投入,又清醒,她相信爱情却又不沉迷于爱情,这态度领先于时代,应是当今年轻人的榜样了。
她把自己爱情中的参与者分享给我,享受其中的美好,摒除其中的渣滓。或陶醉、或抽身,呵护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从不失去自己。
她父母一开始觉得女儿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很高的地位、很多的钱、很美满的婚姻),还有点小埋怨。
她不辩解、不追求,依旧在自己的轨道上继续着自己的人生。
后来二老移民过去,一住就是二十多年,最后终老在多伦多。她照顾他们,做他们的翻译、司机、陪护,参与了他们老去的全过程。
二老有自己的思想惯性和情感归宿,在中西文化碰撞上常常火花四射,代际冲突和文化冲突在所难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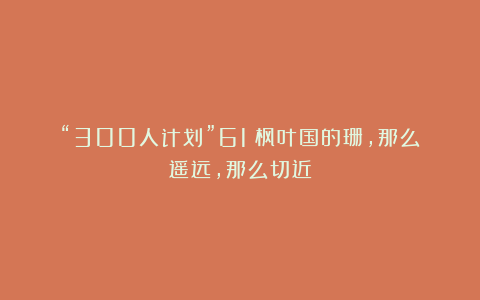 这是个漫长的季节,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和很多很多的智慧与耐心。
她收敛了所有的锋芒,把最温情、最长情的陪伴给了他们。
2008年夏天,我在纽约短期学习,她专程飞过来陪我喝下午茶。她酷爱咖啡和起司,在酒店或饭馆与人聊天时,语言、神情、动作已趋于西化。
后来我到水牛城,她带着她爸妈和她妈自制的一大堆南京菜,从大瀑布的那头驾车来到大瀑布的这头,中途还走岔了道,折腾半天,只为请我共进晚餐。
她大多数的回国,我们都有相见,有时候在南京,有时候在深圳,还有一次竟然是在喀什。
我们在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戏水、捡石头,让一切的美好在葱岭之上高高飞扬。
她带着强烈的高反与我一起登上慕士塔格冰川,在冰山之父前起舞、欢呼。
这是个漫长的季节,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和很多很多的智慧与耐心。
她收敛了所有的锋芒,把最温情、最长情的陪伴给了他们。
2008年夏天,我在纽约短期学习,她专程飞过来陪我喝下午茶。她酷爱咖啡和起司,在酒店或饭馆与人聊天时,语言、神情、动作已趋于西化。
后来我到水牛城,她带着她爸妈和她妈自制的一大堆南京菜,从大瀑布的那头驾车来到大瀑布的这头,中途还走岔了道,折腾半天,只为请我共进晚餐。
她大多数的回国,我们都有相见,有时候在南京,有时候在深圳,还有一次竟然是在喀什。
我们在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戏水、捡石头,让一切的美好在葱岭之上高高飞扬。
她带着强烈的高反与我一起登上慕士塔格冰川,在冰山之父前起舞、欢呼。
我们一起去大巴扎淘花帽子、花裙子和挂毯,去阿依布拉克家晚餐,去果园摘果子,把维吾尔族风情满满地揣在怀里。
今年春天,我们有幸在南京再相聚,高邮花下走,姑苏晃小舟,苏韵绵绵语不休。
她曾拍自家的花园给我看,里面有花,还有各种豆角和果子,她把自己又变成了一个花工。
她说,她在大瀑布那里有座小木屋,等着我一起去观瀑、听风。
感觉好远、又好近啊。
-我在随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