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婉儿,出生在30年代的湘西,那时山里穷,所以一种奇特又荒唐的陋习便悄然衍生。
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一般都会到山外“狃”个女人来生孩子,这一习俗被称为“扭花”。
(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租。)
我家男人是个痨病鬼,为了给他治病,我不得不抛下自己三个月大的崽儿去给别人传宗接代。
狃我的人家住在“借母溪”,这村子世世代代靠“狃”女人来延续香火,地名便也由此而来。
刚抵达村口时,我忐忑的向“狃子客”打听狃我那人怎么样。
(狃子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介,媒人。)
狃子客说:“筷子夹肉,两根光棍。”
我接着问,“那狃我的是老几?”
“哥俩。”
狃子客的话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我即将同时服侍两个男人……
我恳求狃子客帮我另寻一户人家。
可对方反而觉得是我占了便宜,
说:
“两个男人伺候你,妹子,你有福了……”
“可我还是只想跟一个!”
我急切的说道。
“山里穷,
一家能狃一个女人续后就很不容易了,
到时候分不清是哪个的亲儿。
兄弟两个也就能尽心的去抚养,
妹呀,
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
我极力抗拒。
狃子客见状却提醒我,雇主付的定金已经进了我男人的口袋,这事已是板上钉钉了。
听到这儿,我知道我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
在这腐朽的习俗下,女人时常被当做工具,是可以用银钱换来换去的东西。
没人会在乎我们的感受,就在我愣神之际。
突然,山里传来打猎的枪声,我吓得手帕掉进了河里。
当我不知所措时,河里的船夫用竹竿将我的手帕挑起,送到我跟前。
我还没来得及道谢,那人已撑着竹筏离去。
他那宽厚的背影让我心里生出了一丝暖意。
晚上,我被送到卢家。
我坐在房间里,听见隔壁狃子客和雇主家的谈话,
“狃子伯,这是一半的狃花钱,你先拿着,等那女人给我们生了娃,剩下的另一半再给你。”
在入洞房前。
卢家两兄弟跪在祠堂前,祈祷父母在天之灵保佑卢家有后。
“父母在天之灵,保佑卢家有后!”
接着两兄弟为了公平起见,于是用瓦罐做了一个沙漏。
沙漏约定一人一罐沙的时间,随后作为大哥的卢大先一步来到房间,他还贴心的端来一碗蛋花汤。
看清对方的脸后,我们都愣住了。
没想到卢大就是白天帮我捞手帕的那个船夫大哥。
我在惊愕中失手把手里的蛋花汤碗掉在了地上。
“没事儿吧?”
老二在门口探出头来问。
“没、没事儿。”
老大冲他喊了一声。
卢大蹲下身帮我脱鞋,然后颤抖着手解开我的纽扣。
因为白天的事,让我对卢大有了几分好感,同时我也知道自己狃花女的责任,所以整个过程中我很配合。
可谁知看似强壮的卢大没到一分钟就缴械投降了,直到沙子即将流完。
他这才接受自己不行的事实,看着他气馁的样子,我轻声安慰道,“男人第一次都这样,再试一下。”
话音刚落,就听见楼下的卢二在急促的敲击瓦罐。
我害怕的一把抱住卢大,问到
“卢大,我能只跟你一个人吗?”
我能感觉到卢大对我也有几分喜欢,
可卢大犹豫过后,深知不能破坏兄弟情谊的他还是起身离开,去换楼下的卢二进来。
我听见卢大对卢二说道:
“老二,慢着点儿,她是个可怜人……”
我忐忑不安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虽是合理合规的扭花女,可同时面对两个男人,我还是感到很别扭。
就在这时,我看见桌上有一只蜈蚣,听着卢二急切上楼的脚步声。
情急之下,我把手伸向桌上的蜈蚣。
果然那蜈蚣一口把我的手指咬出了鲜血。
疼的我急跳脚。
这时老二进来一看我的样子竟然说道:
“别急啊,我哥不行,我可以的,”
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示意我也坐下。
我转过身来,伸出手指头,给他看流血的手指头,低着头说:
“蜈蚣咬我了,啊,痛……”
卢二一把抓住我的手,问道:
“什么时候被蜈蚣咬的?”
然后他扭头看到桌子上的蜈蚣,赶忙扭头去找家伙事儿去了。
我带着哭腔喊了声:“卢大……”
卢大赶忙冲了进来,得知我被蜈蚣咬了之后,他毫不犹豫的用嘴帮我把毒血吸了出来,卢二见此情形,也没再强迫我跟他洞房,扭头出去了。
我这才逃过了这一劫,可我还得在他们家待整整一年,想到这,心口就沉的喘不过气。
晚上睡觉时,我躺在陌生的地方辗转反侧,想起小时候我娘给我洗澡的时光,
“小咪起蒂了,长大喽,明天呀,要带你去咪子山拜一拜。养的肥肥大大的,将来呀,奶个胖娃娃……”
“娘,我不想让它太大,好丑……”
“傻瓜,大了好大了,才漂亮。”
想起娘来,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就掉下来了。
“娘,咪子长大了。奶了个胖娃子,可还是没好命啊!”
娘要是知道她捧在手心里的闺女如今成了给人借腹生子的扭花女,她肯定是要心疼的,肝都颤了……
为了避免跟卢二接触,我主动揽下家里的活儿。
由于是两兄弟同时狃来,这尴尬的身份,时常会被村里人调侃。
这天我从河边打了两桶水,正用扁担挑着回去时,有一个男人冲我喊道:
“是老大功夫好,还是老二功夫好啊?”
“啊,哈哈哈啊,哈哈……”
他的话引来其他男人的大笑。
我气急败坏道:“滚到山外问你娘去吧,有娘生没娘教的。”
卢二因为那天晚上没得手,于是每天都对我虎视眈眈的。
那眼神里的饥渴,像是要把人活生生吞下去。
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洗头,然后趁机对我动手动脚。
好在卢大及时发现,替我解了围。
“卢二,时间不早了,该走了。”
连着两次没能得手,卢二眼里的欲火更旺了。
那股子邪念像野草似的疯长,这晚我正在洗澡,谁知他竟然直接闯了进来。
“卢二,你不是去守夜了吗,咋突然回来了?”我说着赶忙捞了件衣服穿上。
“担心你一个人在家害怕,我就回来了”
他说着,就对我动起手来,我大喊着“不要啊!”
他却无动于衷,我编了个幌子说,俗话说“大月伤娘,小月伤郎,你快放开我!”
但是卢二根本刹不住,还是卢大听到了动静,赶过来制止了卢二。
我这次的借口和老大的制止又一次打断了卢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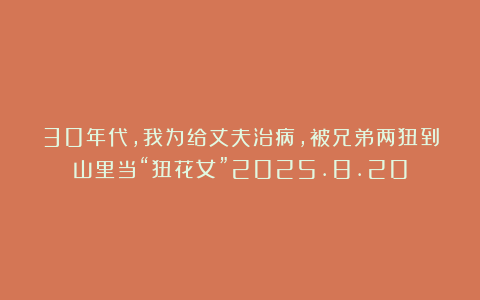
屡次被拒绝的卢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当晚他将卢大叫到院子里谈话,
他说道:
“哥,我难受,这女人太乖了,天天在我面前晃悠,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说这男人,就这么一点事儿,我怎么我就忍不住呢?
哥,我知道你喜欢她,我不介意,反正你是我哥,但是,今天我就想让你帮我一个忙,把我的根给我断了……”
没想到,卢二为断掉自己的念想,竟然决定把自己给阉了。
说着他还把裤子褪到了脚脖子处,然后把刀子扔给卢大。
这疯狂的举动,让卢大感到无比愧疚,他默默的帮卢二提上了裤子。
我知道此刻他内心很矛盾,他一方面喜欢我,不想我被卢二占有,一方面又不忍心看着弟弟每天被欲火折磨……
日子一天天过去,眼看我怀不上孩子,狃子客担心自己拿不到中介钱,于是找到卢二,
“婉儿怀上了没有啊?”
“不急。”
“屁话,狃花的规矩,婉儿怀不上我就拿不到那一半钱,婉儿也拿不到……”
可一段时间过后,我的肚子始终还是没有个动静,狃子客坐不住了,他着急的找到卢大,
“我给你们提个醒,人家是借母生子的,不是来做堂客的哟,”
(堂客,意思是,明媒正娶的媳妇)
“这我知道,会让她尽早狃花结果的。”
卢大知道卢二对我的心思,为了成全卢二,也为了尽早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他决定和同村的春狃下德州挣钱,好留给我单独和卢二相处的空间。
隔天天刚亮,他连声招呼都没打,就准备悄悄离开,我得知后连忙带着包袱追了上去,
“你就带我下德州吧,等回来的时机,我肚子里说不定就有你的种了,你回来再用下德州挣的钱,给老二狃个新的,他就没话说了。”
在我的强烈请求下,卢大终于松了口,同意带我去德州,可就在这时,山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俩不用想都知道,这肯定是卢二在宣泄心中的怒火,思索片刻后,卢大认为就这么将我带走,势必会伤害兄弟情分,随后他把我又送回了家。
“婉儿,老儿他真的喜欢你”卢大意味深长的告诉我道,
“可是……”
“你就听我的吧,”卢大说完就转身离去,离开了借母溪。
“早点回来。”我默念道。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卢大刚出发不久,天就变了脸,狂风卷着暴雨砸下来,河里浪头猛烈翻涌,卢大的竹筏就这么被猛烈掀翻,人也不知所踪。
卢二听到消息时,整个人像疯了一般,他觉得卢大就是为成全他,才会去德州,才会出事。
我得知此事后,浑身的力气像是被一下子抽干,魂魄仿佛飘到了半空,我跪在河边,望着卢大离去的方向,眼泪混着河水淌了一整夜。
还没等我整理好情绪,隔天狃子客就跑来提醒我,让我别忘了正事,
“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就没有留下来的理由,还要退钱,先前我就嘱咐过你的,你全忘记了,你是个有家有夫有儿的人,莫要由着你自己的性子,早结果早回家,这才是正道。”
是啊,既然我做了狃花女,我逃不掉的,替人传宗接代是我最主要的任务。
那天晚上,我硬着头皮本打算应了卢二,可当他靠近我时,我还是本能的感到排斥,怎么也跨不过去心里的那道坎儿,于是又借口来了月事,卢二见状也没再强求我,只好商议改日再战。
然而由于来了几个月还没怀上孩子,这件事已经在村子传开,一群小孩子跑来我家院子外喊着:
“白虎屁,扫把星,生不出孩子,克男人…”
“去去去!”我气得挥手赶走他们。
孩子们的嘲笑声像针扎般刺痛着我的心,而我只能默默忍受。
随后我去村子里干活,同村的村民见我孤身一人,便想占我便宜,
“卢大没了,听说卢二也没给你种上,要不让我扭你吧!”一个小伙子拽着我说。
我转身要走,他又拦着我。
“哎,妹子,你这是何苦呢?你出来做狃花女就是为了赚钱,谁狃你不都一样吗?”
男人轻蔑的话语让我倍感屈辱,虽然我是别人花钱请来的狃花女,但狃花也有狃花的规矩,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乱来的,我快步回到家,没想到这个小伙子竟悄悄的跟着我来到了家里,二话不说就想强行将我占有,
“好妹子,趁他俩不在,今天我就给你种下,你又有钱赚又快活,一举两得……”
就在对方即将得逞时,没想到卢大竟死而复生回来了。
卢大告诉我们,那天出事后,他被大浪冲到了岸边,刚好被路过的红军救下。
看着卢大平安归来,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随后扑进他的怀里痛哭流涕。
卢大被红军救下后,也加入了他们。
卢大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明白了借母溪世世代代狃女人的习俗,实在愚昧的可怕,这既是对女人的不尊重,也是男人无能的表现。
所以卢大和卢二商量,想让我回去。
“哥想给婉儿拿些钱,
让她回去好好过日子去。”
深夜,卢大对卢二说道。
可一直没得到我的卢二显然有些不甘心,
“我喜欢她,我不想让她走……”
“喜欢她也不行,
人家是有家有男人的……”
卢大劝解道。
“以后要娶堂客,
咱得堂堂正正的娶,
以后不能再狃女人了,
你喜欢婉儿,
可婉儿的男人,
还指望着她拿钱回去治病呢。
她也怪可怜的,
才十七八岁,
咱不能让她再遭罪了。
小时候你也是天天,
哭着闹着要找娘,想娘。
咱不能让咱的崽儿以后也见不到娘啊。”
原来卢大卢二的母亲当初也是个扭花女,在生下他们之后,她就离开了,自小没娘的滋味,他俩比谁都清楚。
卢二思考过后。
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样的命运,于是同意了,放我回去。
因为没完成任务,所以狃子客拿不到中介费,他找到卢二,想讨个说法。
没想到被卢二骂了一顿,狃子客咽不下这口气,随后竟跑到镇上去举报卢家私藏红匪。
没过几天,反动组织将卢家包围,为帮红军打掩护,卢大、卢二操起猎枪和他们对抗。
随后,卢二为了给红军争取时间转移,他故意往山上跑,把追兵引了过去。
可没过多久,他就不幸中弹了。
等我找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我抱起他的头,说,“你别死啊,我以后还要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呢!”
我还没说完,卢二就咽了气,顿时,无尽的懊悔和自责如潮水般将我淹没。
若不是我一直不肯接纳他,他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
卢二去世后,卢大跟着红军离开了借母溪。
“我走了。”他走前给我留下了这三个字。
“卢大,我是借母溪的媳妇儿,我会等你回来的”,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喊道。
卢大离开后,我并没有回家,不是我不想回,而是家里如今早已是物是人非。
那天在卢二送我回家的路上遇见了三叔,我才得知,几天以前,我的男人因痨病而死,日夜思念的胖仔也因饥饿离开人世,我已无家可归。
当初我做扭花女,本是为了给病床上的丈夫挣医药费,让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改善家里生活,可如今他们却一个病死,一个饿死。
如果当初我早点接受卢二怀上孩子,是不是早就回去和他们团聚了?
他们是不是也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了?
我终究成了罪人。
后来几十年过去,卢大始终没有回来,而我只能带着孤独过完余生。
我的遭遇不过是那个时代无数悲惨女性的缩影,她赤裸裸的展现出封建礼。
叫对人性的扼杀,传宗接代被捧上神坛,女人的尊严却被踩进泥里,扭花女的故事都是一部部无声的血泪史。
狃花的习俗在清末民初的湘西尤为盛行,那时山高谷深,交通闭塞。
加上战乱灾荒频发,当地男性普遍贫困,无力娶妻,而宗族观念中传宗接代的执念又让他们对延续。
狃花的习俗应运而生。
这种习俗本质上是底层男性在生存压力下对女性的工具化。
女性被剥离了妻子的身份,仅作为生育载体存在,其个人情感与尊严被完全漠视。
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红军进入湘西,带领劳苦大众推翻封建陋习,狃花这一封建落后的习俗也随之逐渐消亡。
而我也是借母溪的最后一个狃花女。
回望狃花女的历史,并不是为了沉溺于苦难,而是为了记住人最珍贵的权利是被当作“人”来对待,有选择的自由,有被爱的资格,有不被任何标签定义的尊严。
这份记忆是对当下的提醒,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愿每一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舒展,不必在阴影中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