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历史文化中掬一捧清芬
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
1
易安的酒
市四中 八(18)班 陈昕玥
易安,你这一杯酒,盛满了九百年的月光。
世人说你如清泉石上流,清澈照人。可他们只见你映出的松间明月,却不见你深处奔涌的暗流与力量。
那是一个连醉酒都专属男子的时代。太白举杯是仙气,曹植宴饮是风流。而你,易安,你端起酒杯,便是劈开了一片寂静的、只属于女子的天空。你不是浅酌,你是“煮酒笺花”,是把诗情与醉意一同投进生命的炉火里淬炼。于是,隔着泛黄的书卷,我们仍能看见那个在黄昏篱畔执杯的身影,衣袂飘然,眼神清亮——那不是“酒鬼”,那是未被规训的、鲜活不屈的灵魂。
你活得如此磅礴。爱时,敢写“徒要教郎比并看”,娇憨里透着平等的傲气;闲时,与夫君“赌书泼茶”,才智交锋的乐趣远胜于举案齐眉的恭顺。你从不甘做池中静水,你要做一条有方向、能奔腾的河。
然而命运最苦的酒,终究斟给了你。
建炎年间的颠沛,带走了你的安宁,也带走了明诚。那杯中的滋味,从此浸透了“寻寻觅觅”的寒气与孤寂。但你连沉沦都带着棱角。五十岁那年,你亲手将第二任丈夫告上公堂,哪怕被斥“不知廉耻”,哪怕法律森严,妻告夫要入狱两年。那不是冲动,是宁为玉碎的决绝——你知道清流若想涤荡污浊,有时必须以身为刃,哪怕撞上最坚硬的石头。
醉,是你看世间的眼;醒,是你对命运的回答。
醉时,你是“九万里风鹏正举”的逍遥客;醒时,你是痛失山河、收藏散尽,却仍挺直脊梁的未亡人。你醉过北宋最后的晚霞,也醒在南渡后最深的夜里。这一醉一醒之间,是一个朝代的剪影,更是一个女子将破碎人生重铸成词的壮举。
易安,你杯中的酒,从未真正空过。
初时斟的是青梅天真的甜,后来满的是离乱沉郁的苦,最终沉淀下的,却是穿越时光、依旧灼烫的——风骨。
千年已过,我们仍在传唱你的词句,仿佛想接住你当年洒入江海的那一杯。那不是哀悼,是致敬:致敬那泓不肯停滞的清流,致敬那副敢醉敢醒、敢爱敢恨的肝胆。
东篱依旧,人已千秋。但每当我们不愿随波逐流时,仿佛总能看见,你提着一壶酒,从历史深处走来,身影清瘦,目光如炬。
2
冬宜密雪,三春之冠
市四中 八(17)班 郑可歆
漫天风雪迷一人,世间已无张居正。
——题记
葭月方至,苍叶别霜,檐下皎皎雾淞如疏银,青竹赴宴作琼枝,缀上盈盈玉梨花。
他在漫漫历史中留下的实在是太浅淡——张敬修。他是否已沉进了老人的记忆里,成为被时代吹过的一粒尘埃?而提其父,张居正,却是无人不知。
张敬修,正是这位首辅的长子。
冬水煎雪,直至麓川鼎沸,熬得涟漪沆砀。于是这个名字被完全覆盖在父亲的盛名之下,将其一生只能借日而亮,不见自己独属的圆缺,也永远无法照亮那一片“灯下黑”。青史浩浩,他唯一一次被推上历史的舞台,也是替父偿罪。仿佛这个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去担下这个时代的罪责。而后,他也只是被历史的巨手一把拍落,像是掸去历史长卷上的一粒灰尘那般无情。
借父之耀,替父受过。于是张敬修人生的一切悲欢离合全被折叠进这八个字里,寥寥几笔,来去从容。
至此,史官搁笔,风过无痕。
无意轻卷历史长卷,来到万历年间。那个万历八年庚辰,他与弟弟懋修共登进士。有风乍作,琼枝瑟瑟地抖落半阕珠箔,在窗牖绽开霜花。而窗外岁寒霜重,山川将磅礴的情绪压抑进纷扬的絮雪,为他们饯行。紫陌花深,琼林宴罢,父柄国而子联翩,全矣!
可命运却只给他数五年的时间而矣……
万历十年,张居正骤逝。
大元古都废墟上的青草与野黍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根深而茎壮,埋在草丛中开裂的陶器早已流尽最后一滴汁液。破碎古都,宛如机关算尽,暗示了张家最后的结局。
张居正那位隐忍一生的学生,终在先生棺落之际,重露真面目。十年蒙尘,他把蜷缩成一团的自己舒展了,重新亮出了刀刃。
而接下这致命一击的,是张家,是那位长子张敬修。
在那个幽囚诏狱里,风雨萧条,青草鸣蛙。一纸状书,凡千余书,字字泣血,句句剜心。
先叙父功:“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再道己冤:“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次嘱亲人:“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惟六岁孤儿重辉,望诸公哀怜,存此一线。以死明志:“故告天地之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
他死的那一年,仅三十一岁。距他金榜题名,仅三个春天。一脉忠魂,终于回到了祖父与父亲并肩而立的墙头。
今日,江陵城外,张居正墓前石碑岿然。偶有人过,览碑上“明太师张文忠公之墓”。更远处,是否有一座更小,更旧的土坟。若有风雨摩挲过的石碑,我猜,上面当有“张礼部君平之墓”。
雪宴隆冬,允我歇灯归晓,允你昂扬向春。
冬宜密雪,有碎玉声。
密雪抚我荒芜贫瘠,一声祈你岁岁平安。
3
荔胄:苏轼的三重天
市四中 八(18)班 蒋以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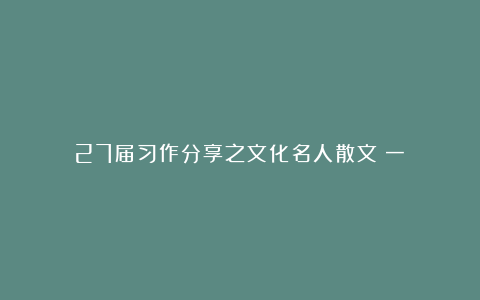
所有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它的苦涩与回甘。
岭南的荔枝红了,燎原之火般的,将山野都映出三分血性。伫立树下,看那累累垂垂的果实,披着粗粝的鳞甲。摘下一颗,轻轻摩沙。恍惚间,化作一枚藏着时光奥秘的琥珀,折射出藏匿着的伟岸的三重灵魂……
第一重,是壳。 指甲嵌入粗粝的缝隙,用力刺入,听得一声脆响。好像元丰二年御史台监狱沉重的关门声。“乌台诗案”,苏东坡从名动京华的苏学士,坠为了阶下囚。无尽诋毁如利刃,扎得他高傲的心,千疮百孔。贬谪的诏书一道比一道严酷,黄州、惠州、儋州……路越走越荒,命却越走越硬。这层坚韧的壳,便是世界最初赠予苏轼的礼物——命运多舛的惊悚,与“魂飞汤火”的淬炼。他未曾被击碎,只是将这一切冷硬,默默吸纳为骨骼的一部分。
第二重的膜,微涩如转化之茧。 剥开硬壳,指尖触及白衣,微涩,泛着清苦。黄州的东坡,从向苍天问寻,到俯身向大地讨要哲学。他垦荒,造屋,研究红烧肉的“火候”,在“长江绕郭知鱼美”的寻常里,咂摸出生命原初的滋味。这层薄膜,便是他与苦难谈判、和解的现场。林语堂说他“一生是载歌载舞的”, 那歌舞并非空穴来风,正是这层韧膜,将外部的苦涩过滤、酝酿,悄然滋养着内里的生机。
待到白衣褪尽,那枚莹如冰雪、凝若羊脂的果肉,才豁然呈现——这便是第三重,心,澄明而炙热。 含入口中,一股清冽磅礴的甜,如山洪般席卷一切。那甜,不带一丝烟火浊气,纯粹得如同他晚年的笔墨。那是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天真贪欢,是儋州“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辽阔认领,更是穿越所有劫波后,那声淡然的自问自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所有的苦痛,仿佛都只是为了成就这最后的“清欢”。这已不是口腹之欲,而是精神的结晶,是苦难在伟大心灵中反复蒸馏后,滴落的一滴纯粹露珠。
暮色将荔林染成一片恢宏的紫金。偶见有人评“为何千年而下,我们仍需一遍遍怀念苏轼?”于是笑着敲下:也许是因为他并非未遭风雨,而是为我们演示了灵魂可能抵达的韧性、广度与高度。
是他,接过命运最粗粝最苦涩的壳,以人生的微火耐心煨烤,终使我们尝到那枚最澄澈、最甘甜、最本真的心。
4
从嘉的江南 李煜的汴京
市四中 八(17)班 盛夏
风雨飘摇,困于汴京小楼,词中日月长。
他们给了你很多名字:重光,钟隐,从嘉……最后是那个染尽岁月鲜血的“违命侯”。李煜,南唐这一繁华的梦在你手中破碎,你的内心何止是心酸?
回望你的来时路,那是一场过于漫长而雍贵的梦。
梦里,你曾在晨曦间,拂过柳枝,惊动昨夜未干的雨露,衣袖间,是青草裹挟着泥土的清甜。你的眼眸里,映的是宫墙上的金碧辉煌,是宫宴后的烛烟袅袅,是庭中疏条交错间的月牙,是枝头盛放的石榴花。美,是你世界里最坚固的城墙。
那时候,他们叫你“从嘉”。从嘉,从嘉,是生活的美好,亦是人民的安定,更是盛世的延续。
可是,谁是从嘉呢?
你的记忆被蒙上一层灰,渐渐地,模糊了——
兄长的相继离开,只留你一人在世间。他们推着你坐上冰冷的龙椅。你像个孩子,笨拙地用稚嫩的双手,搭建一个华美的海市蜃楼,编制一个“完美”的梦,在帝国的废墟之上。他们喊你官家,叫你君主,而你心中的是“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的画卷罢了。
“嗒嗒嗒——”
来自北方的马蹄声,击碎了这幻梦。
那个叫赵匡胤的,改天换地,建立了宋。再后来,宋军直逼城下。
你看着宋军拥入城池,心中暗自冷笑:多讽刺!昨日的君王,今日的俘虏。你永远记着离开金陵的那一天,江水是浑黄的,像哭脏了的脸。那“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城,混着嘴角的咸涩,在梦中坠落。
到了汴京,那里的人叫你“李煜”,叫你“违命侯”。那个四面无窗的“府邸”里,望不见属于你的——属于从嘉的江南。
愁,不再是闲愁。它变成了实体,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它有了生命,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它终汇成了江河,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汴京的风比江南的要冷得多啊,梧桐深院锁住了春秋,也锁住了你。故国的雕栏在记忆里化成灰烬,一切成空,一切徒然。汴梁的阶梯太冷,秋雨太寒,你裹紧了衣衫,却裹不住一颗日渐凛冽的心。你终从梦的温室里走出来,伸手拥住了这凄凉的寒风,一点点筑成你笔下的脊骨,坚韧而挺拔:写下“春花秋月何时了”的凄凉,写下“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痛。可你深知,一首首以“李煜”为名的诗词终不敌那个江南的“从嘉”。
李煜李煜,是故国之君,汴京之囚;从嘉从嘉,游于金陵城,守望着这片江南。
在生命的尽头,温酒还有着余热。你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你:“李煜!李煜!”想必,是那个江南的从嘉来接你回去了吧!
从嘉,别回头。
身后不是江南,是汴京的秋。
5
红梅·傲雪·淡然
市四中 八(18)班 元婧晗
真正的淡然,是看清生活后还能热爱生活。
——题记
红梅沐雪而立,傲立寒霜,在生活的风雪中绽放,恰似苏轼的一生,在风雪中淡然摇曳。
初绽,不惧风雪
年少,苏轼,如寒梅初绽,便遇风雪,欲折枝,恰披上红衣。仍不失鲜艳。乌台诗案的推搡,如同大风,暴雪,把这一朵刚披上红裳的红梅吹得凌乱无章。而他,扎根枝头,不惧,不惧,怎受风波?躬耕东坡,一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一粟”为红梅尚未绽开的霓裳,点上了不惧为色彩的璎珞。这些风雪如一叶轻舟,溅起点点水花,卷附在红梅的霓裳上。“不惧”,初显淡然。
盛放,傲立寒冬
往后,贬途漫漫。“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句话,是红梅盛放,是傲视风雪。苏轼轻描淡写,他的影子中,这株红梅摇曳着绯红的衣裳,在一片白茫茫中绽出了赤红,正如苏轼,在傲视风雪的同时,依旧怀着赤红的心:开堂讲课于蛮荒之地。他留下了红梅的种子。“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他看清了生活,仍然爱生活,恰如红梅盛放在杳无人烟的寒冬,依旧盛放自己的热烈与傲挑。
“傲立”,尽显淡然。
永绽,传以风骨
暮年,淡视一切。“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雨中独行,眼中盛满淡漠。这株红梅将永立于枝头,高也罢,低也好,都是一种赞叹!红梅在尽头,面对结束,轰轰烈烈地,用尽力气,绽出生命的最后一章。红,是花瓣的颜色,亦是苏轼眼中的一生,点缀了璎珞的霓裳舞上一曲,在枝头留下不可磨灭的脚步。丝丝茎脉,编织出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亦是淡然。“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啊,也无风雨也无晴,有的,便是那一枝红梅,绽开红裳,酝酿下淡然的清香。
红梅朝朝暮暮,永立在枝头,赤红的花蕊,绯红的衣裳,以及,他绽出的淡然,风雨也好,霜雪也罢,苏轼这一枝红梅,将会永立在淡然的顶峰。红,将成为他的代言。
回首,向来萧瑟,红梅傲立,绽出淡然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