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自我反照在平凡之物上
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
1
枫
市四中 八18班 林琮竣
那道血痕般的红,劈开雾气撞入眼帘。
在一座后山,石板路被夜雨浸透,滑腻如青鱼脊背,寒气裹着腐叶的土腥钻进领口,我抱紧双肩,只剩机械抬腿的力气。
幸运的是,我看见了它。不是一棵,是一片,就在断崖边缘,从岩缝里挣出来,筋骨盘虬的枫。最奇的是叶色,并非明艳的黄桔红,而是沉郁的绛,像淤血,又似将熄的炭。两丝击打其上,蒸腾起白色雾霭,整片枫林在灰白背景里沉默地燃烧,静默到有重量,压得雾都流速迟缓。这不合时宜的浓烈,近乎悲壮。
我鬼使神差走过去。树下秋叶厚软,踏上去悄无声息。抬头,拔干交错如铁画银钩,分割着低垂的天幕。雨并不直接落在我身上,先经过层层枫叶的拦截,汇聚成更大的水滴,再沉重地砸下,带着枫叶特有的,微微的气息。我靠着最粗壮的一棵生下,树皮粗粝,寒意隔着衣料渗入脊骨。
“它们在这多久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我惊得一颤,侧头见是一位山民打扮的老者,蓑衣斗笠,肩上扛着短锄,不知何时出现的。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枫林:“没人晓得。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它们就在这儿了,”他卸下锄头,坐在不远处一块青石上,“这地方,土薄,石头硬,一年里大半年裹着雾,见不着几天太阳。别的树,长不高,也活不长。”他顿了顿,“就它们,肯能下扎,根比树冠还深,专找石缝钻。你看那颜色,”他指了指头顶深郁的红,“不是晒出来的,是熬出来的。雾里浸,雨里沤,风里摇,硬沤出这一身红。 ”
我怔怔地望着。雨丝更密,但林下的空间却奇异地静谧。老者的话像钥匙,打开了我的眼睛。我开始看清那些狰狞枝干上雷劈的旧疤,看清岩缝里暴突如鹰爪的树根,看清无数红叶边缘被虫噬风啃的残缺。它们不美,甚至算得上丑陋,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挣扎。可也正是这挣扎,让那抹红脱离了轻浮的艳丽,沉淀成一种有分量的存在。它们不是来点缀秋山的,它们就是秋山本身,是这色瘠壁凝出的血珠,是缄默与严酷共同酷造的酒。
老者起身,拍了拍蓑衣上的水珠:“人哪,有时候就得学学这枫。不一定非得长在沃土平川,见着日光就灿烂,能在不见光的地方把自己活成一种颜色,一种脾气,就算没白来这山上走一遭。”他走入雾中身影渐淡,声音却清晰传来,“一路往东,再上一段坡,就有灯火了。”
我没有立刻动身,又在树下坐了许久。我伸出手,接住一片旋转飘落的枫叶,它并不轻盈,边缘微卷,色泽沉暗,叶脉在掌心纹路中显得格外粗砺坚实,我忽然懂得了它的重量,那是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用全部的生命力来对抗贫瘠、潮湿与遗忘,最终凝结成一小块燃烧的证明。
它落在我肩上的很轻,却压在了整个漂泊的秋天。
2
演一出生存的悲喜剧
市四中 八18班 朱奕煊
树丛深处,与它相逢。
阴雨迷蒙,万物失色。我独自漫步,见此“淫雨霏霏”之景,秋日的凉意早已散尽,独余下凛冬的寒风。
偶然间,我在道边瞟见了它。
雨下大了,我不禁加快脚步。为何从来都未见过它?门前的草木本都是熟识的,有些虽四季常青,至今还是绿意盎然,但却因过于标致,经过岁月沉淀,反倒黯然失色,令人心生厌倦了。
我的脚步终究移到了它面前——一抹亮丽蓦然在我眼前划开。雨点无声地敲打在它身上,荒草肆无忌惮地在它周围蔓延,试图掠夺那本就微渺的养分。它确实是在这里,倔强地生长着。
但面对苦难,它坦然而笑。阴雨是它最好的帷幕,雨点是它最佳的舞伴。狂风袭来,独属他的演出便开始了。他将根紧紧地埋在泥泞之下,微微展开他的叶瓣。雨水自上而下淌过它的每层肌肤,滑过叶尖儿,翻涌成细小的水雾。他接受着,默默地旋转着,带动这残缺的躯体,跳跃、欢欣,甚至带着酒醉般的激动在颤抖。
但他的悲剧,无人观看。
他舞得愈激烈,观众便纷纷离去,他愈是欢欣,便愈被众人唾弃。不得不说,多肉,这株不起眼的,可怜的植物,在群芳之中,早已沦为了笑柄。
没有花朵,只有光秃的叶瓣与狭长的根茎,但这便是它的全部。他生来仿佛便是一个悲剧,注定要在荒草间虚度终生。我怜惜地拨弄它的叶瓣,为何已知是悲剧,还要立身其中?我诘问着。
他叹息着,继续他的舞蹈。他已不再拘束,和着雨点,他仰起叶瓣。自中心向四周,层层叠叠,没有错综,逐次过渡。紫红的内部渲染出外环的奇幻,外环的粉红映衬出内部的迷离。他抬起头,仰望苍天,无畏地给予了礼貌的笑意……
或许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悲剧,天下少有完人,挫折不可避免。悲剧,是魏晋名士早已参悟到的宿命,但因悲剧丢弃生活,绝非真理。他面对悲剧,坚决地拒绝。他失去了花应有的尊严,丢失了自然应有的馈赠。一时间,他似乎失去许多,但又什么也未失去。
他将秃叶当作彩衣,他将风雨视为福音。这又何尝不是生的希望,于他而言,悲剧,只不过一尘土。
低落之时,不妨吟诵尼采的“无法将我置之死地的,令我更坚强”。于我心中,悲剧便为光明所向。
天晴,树丛深处,他正微笑着向我告别……
3
潮涌,潮涌
市四中 八17班 童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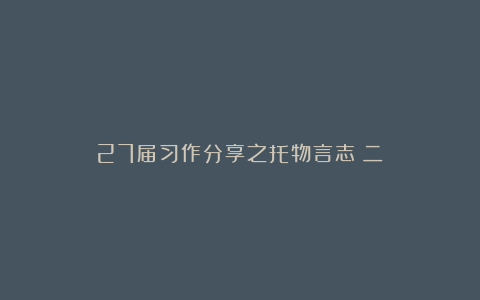
非因逐浪随波去。
印象里的潮,总是飘忽不定。
钱塘江大潮,在夕阳中斑驳。拾级而上,屹立在你眼前的,是近似悬壁似的礁岩。正值日暮时分,浮光跃金,渔舟灯盏,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进行分割,湛蓝与黄金都纯净得毫无斑驳。日夜的风,将峭岸和水脊塑成波浪。
终于到了顶,我侧栏而望,大潮开始涌动无限能量。晚露如缟素轻笼钱塘江口,咸涩的风掠眉而过,将远江揉作一片濛濛烟水。未及凝神,地底已漾起隐隐雷动——那不是天地的私语,是潮在深海之下孕蓄的势能,是勇毅之志欲破混沌的前奏。倏忽间,天际线处裂出一道银白锋刀,初如素练垂江,转瞬便化作万马奔腾的阵列,携着崩山裂石的磅礴,向着岸堤奔涌而来,目光所及,正是那片横亘江中,棱角峥嵘的礁岩。
潮之涌,是破障前行的磅礴动力,在与礁岩的碰撞中尽显锋芒。它摒弃溪水潺潺的试探,远离湖水涟漪的安逸,以千万吨江水凝聚的合力,完成一场挣脱束缚的野性冲突。先是前锋浪涛呼啸而至,带着雷霆之势狠狠撞向礁岩。浪花瞬间崩裂,化作漫天玉屑,迷蒙了半片江面。但这并非终结,后浪立即衔枚疾进,卷着未散的水珠,顺着礁岩棱角攀爬,冲撞,噬咬,将磐石的冷峻彻底吞没在汹涌的碧色中。这奔涌绝非无序的蛮干,而是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冲破时代的桎梏。
潮之勇,是直面硬核的坚韧坚守,在与礁岩的抗衡中沉淀风骨。他从非一时的激情宣泄,而是千万年与礁石相拥的生命坚守。潮声里,藏着秦汉烽火的余温,载着魏晋风骨的清响,却从未因礁岩的阻隔而放缓奔涌的步履。它明知礁石坚硬,撞之必碎,却仍以血肉之躯赴险。礁岩试图以棱角划破潮的锋芒,潮便以持续奔涌的势能磨平岩的顽固——这是勇的高阶形态,不是逞一时之强的冲撞,而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勇的坚韧,是包容险阻,化阻力为动力的通透。
站在潮声轰鸣的岸堤,看潮与礁岩千百次交锋。潮的奔涌与勇毅,早已超越自然景观的范畴,成为一种精神图腾。
浪花拍岸,潮声渐烈。
那股裹挟着天地之气的勇毅,顺着血脉渗入心底,化为前行的不竭动力:生命的真谛不在于平顺无波,而在于逆旅中奔涌,在困境中坚守,人生的价值不在于随波逐流,而在于以勇为刃,划破天幕,以涌为势,踏平前行的荆棘。
怒涛卷地破苍冥,勇携长浪赴长风。千回奔涌初心在,伴潮直上碧霄中。
4
风的形状,芦的答案
市四中 八18班 陈钰绮
风是芦苇唯一的语言。
校门前,在湖水与岸的交界处收藏着一排排芦苇,晚饭归来,坐在窗旁,目光不经意掠过那片芦苇。
正巧赶上日落时分。夕日熔金,光影筛过半边芦苇,像细浪般向天际摊去。当金粉簌簌落水面上,正巧一阵风掠过,这时它们便开始展现风姿。不是一整片的伏倒,它们次第地,慵懒地倾斜,那一簇正弯腰迎风,另一簇便直起柔软的身姿,错落有致,缠绵地倾泻着,道出风的缓与轻。一阵风走了,一阵风来,轻风中,它们保持着自己被风所抚摸过的形态与弧度。偶尔有雪白的芦花迎着风散漫地飞舞,落在水中如浮动的星光,挂在芦叶上,似那颤抖的泪。
暮色渐深,却嚣张了风的气焰。
风渐大,愈发凶猛。我担忧地望向那片芦苇丛,担心它们在大风中真的会伏倒于湖中,化作永恒的寂静。然而它们的柔逐渐在狂风中化作了韧与逆。
你看那每一根芦苇,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画着抗争的弧线。风推着它们向东,他们便借势压弯些,但穗子依旧倔强地指着那东方的天际,风欲让他们俯倒,它们便化作一道弓,以柔韧的极限,逐渐消解着风的呼啸。它们没有一株折断,有一株真正屈服。风呼啸声伴着芦苇摇摆的密语,在夕日中唱出了芦苇的气骨。
风渐小,塑造了芦苇的弧度,温柔而不屈。等到夕阳终于远山的天际线后,风终于停止了。
芦苇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两道弧度,一道柔而顺,一道却劲而刚,在我的心中低语:
风大时,要表现出逆的风骨;风小时,要表现出顺的悠然。与风的顽强对抗,写出了它的顽强不屈;随风的悠然摆动,绘出了万物融洽的诗卷。
你看那芦苇,注释了对抗境遇的两种智慧。风从东方来时,它便向西方弯腰,将苇絮洒向天际,将希望的种子播向远方。当狂风企图将他撕裂时,他在俯仰之间将毁灭之力散作无形,以牢固的根御风,以中空的茎秆谱写生命之韧。或许风平浪静过后大树折断了枝干,芦苇依旧在湖岸交汇处巍然挺立,在每个晨昏交界展现其智慧:风只是过客,大地才是永远的归宿。
人生当如芦苇:顺风时俯身着势,逆风时韧性生长 。而心之所向如穗尖,永远指向远方的天空。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永不弯曲,而在于每一次弯曲后都更接近天空。
5
破岩劲竹
市四中 八17班 李意平
青竹,不屈地生长着。
若是走在竹林里,四周如墨水般浓郁的绿色会淹没你的眼睛。微风拂过,掀起的沙沙声则轻柔又调皮地按摩着你的耳膜。几颗晶莹的晨露,凝结在修长的竹叶上,透着绿,似要清洗这本就一尘不染的绿叶。竹干,竹枝,细细长长,光光滑滑,没有一丝风雨留下的划痕。整片竹林,皆是这浓郁的绿,雍容华贵,千篇一律。
若是往外围走几步,走出这片“生机勃发”,原本绵软的土地变成了粗糙的砂石,甚至是顽劣的岩石。你会发现这里仍然有竹子,却截然不同。道道伤痕,是风雨和泥点制成勋章,牢牢地贴在上面。叶子随叶脉分开,边缘干枯,景象有点破败,竹干却格外粗壮。没有了水的滋润,却仍然坚挺向上。这风尘仆仆的景象下,却藏不住春日的生机,夏日的浓郁,秋日的挺立和冬日的孤寂。竹子根部,坚实的岩石微微松动,隐隐的裂缝是对生机的坚持?还是对命运的反击?
或许会有一场足够大的雨,让里面占尽地理优势的竹子们从从容容品鉴,也让外围的那些落寞的竹子们能够沾得一些上苍的雨露。不求雨露均沾,只是竭尽全力吸收生的希望。雨很大,风也很大,在那风雨里,外围的竹子左摇右晃,身影单薄,却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喜怒无常。
竹子好像总是以成片的壮观来震撼人们,却鲜有人关注到那些身处边缘却奋力向上的竹子,他们立根破岩,却以他们独有的方式展示着生命的另一种勃勃生机。地理的劣势,使得他们遭遇的风雨会更强大,但一时的风雨所带来的累累伤痕,却是下次,下下次迎接风雨的珍贵经验。待到阳光再次普照,那些勋章是如此闪耀。
阳光会温暖每一片竹叶,抚慰每一个竹节,在每一个竹子精灵的耳边温柔地细语。生机勃勃从来都不只是形容那些养尊处优的华美,生命的不屈与坚持,哪怕粗粝异常,也值得歌颂赞美。竹叶上的露珠不是,叶上的斑驳才是。
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光鲜亮丽只是外包装而已。娇柔,终是昙花一现,在时间的冲击下,终究会磨灭。而不屈的意志,将会挺立人间,一次的倒下,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站起。就像竹子一样,向下深深地扎根,汲取养分,向上直直地昂扬,展示生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