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
1
回忆外婆
——一株君子兰
18班 王宣迪
晨曦未至,四五点的天色,如同霜一样的白,阳光没有覆盖阳台,洗手池边那株君子兰,半黑半银,望着在池上洗衣的外婆。她是很劳累的,一大早起来洗衣,浇花。此时的她,正提着一件从水中泡出的白衣,左手托着衣角,不让水漏下把房间弄脏。
君子兰是外婆养了十几年的。听说我出生那天,君子兰刚好一夜开花,外婆在医院照顾我母亲后回来给君子兰浇水,添肥。那时君子兰没有。长出很结实的老叶,好像连风都能把它吹倒,外婆看着弱小的君子兰,又想到了我,在看过了花与家务后做了好吸收的粥去医院照看母亲。她两头都要顾,是个大忙人。
君子兰长得很快,在我五岁时,我去看君子兰,而外婆正在为它浇水,不知怎的,我突然提议:“天放晴了,我们去晒太阳吧!”外婆如同鹅蛋般白而圆的脸上出现一抹笑,她拉着我坐到阳台上,让我抱着花盆,说是让花也晒晒,放在房间里闷着也不舒服。
她同样也如君子一样直率。
大约是七岁,我到了努力学习的年纪,我在小心翼翼地做着作业本,外婆突然站过来,盯着作业本,开口:“这里这里都错了,做作业的时候要仔细,像君子兰那样扎根时选对土缝,这样才不至于少水分少空气活不下去。”我明白她说的话,也照做了。
2023年1月5日,她离开了,君子兰的厚叶也一点一点枯萎。当母亲告诉我外婆不行了,我仿佛看到她在离开前仍勤劳的做着事情,炒着我爱吃的美食,冻在了冰箱里,是让我不要忘记她的厨艺,我明白她的用意并祈祷着发生转机,可悲的是奇迹并没有发生,君子兰最后叶落,与世辞!
她是那株君子兰,是勤劳的生活者,是直率的导师,也是过去时间的凝视者,凝视着我的心。虽然她只活在那一张相片里,但我不能忘记!
2
唠叨的外婆
18班 陈昕玥
外婆的唠叨是从清晨五点半开始的,但总是裹着笑意。
“囡囡,被子要叠四角方正——”她推开我的房门,话说到一半,自己先笑起来,“哎呀,你这被子卷得像春卷!”眼角的皱纹瞬间聚成两把欢快的小扇子。她一边抖着棉被,声音穿过薄薄的木门板,带着哼歌般的轻快。
她的唠叨是有形的,却总被笑容软化。追着我穿秋裤时,她举着裤子满屋转,自己先笑弯了腰:“小祖宗,你跑得比兔子还快!”硬塞苹果给我时,眼睛眯成两道弯月:“上午十点一定要吃,你看这苹果红扑扑的,多像你小时候的脸蛋!”每晚递来牛奶,必定配上皱鼻子的俏皮表情:“喝干净哟,杯底剩一口,明天就少一朵笑容!”我感冒时,那唠叨会变成夜里三次摸我额头的手,和凌晨厨房熬着的梨汤咕嘟声,抚着我的心。
其实我知道——她那带着笑意的唠叨,是怕人生太苦,非要撒上糖霜。爱在她那里,化作千千万万句含笑的话,像阳光穿过窗棂,把所有的叮嘱都晒得暖烘烘的。
3
外婆的笑
18班 柯亭伊
笑容是她脸上最耀眼的色彩。
外婆脸上是常常带着笑的,明媚的阳光总盖不住她淡淡的笑意。
外婆小时候家里穷,没钱读书。到现在大字还不识几个,每当我到她家时,她总会从枕头下拿出一本佛经,翻到做好标记的那一页,让我一字一字教她念,再用铅笔歪歪扭扭地注上拼音,还笑着打趣自己:“外婆可真是什么都不认识!”
在我印象里,外婆总是很忙,要照顾牙牙学语的小表弟,还得顾着洗车的生意,常常一手抱着小表弟,一手将泡沫洒在车上,在太阳底下忙碌着。天蒙蒙亮时,全家人还在睡梦里,她已经起床准备早饭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尽管这么忙,她还是能挤出一丝一毫的时间打理她的小菜园,每当我去的时候,小菜园总是生机盎然,也许是翠绿的葱,也许是冒头的小青菜,也可能是一株株待采摘的大白菜。外婆常常笑着摘下菜园里的瓜果蔬菜,自豪地跟我说:“喏,带回去,外婆种的,没有农药,干净!”那时的她,笑容里透着光。
外婆的脸上总挂着绚烂耀眼的笑容,仿佛明媚春光。
4
窗边的外公
17班 廖燚晨
外公总爱抱着小小的我上街。他的身子骨很硬朗,走起路来像一阵风,呼呼地就掠过了大街,穿过了人群,新建的游乐园一下子就到了。
外公还爱抽烟。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清早醒来,总能看见他立在窗边。朝阳是金色的,软软地照进来,外公就仰着脸,对着光,一口一口地吐着烟圈。他整个人一动不动,膝盖抵着窗台,背靠着玻璃,只有夹着烟的手指和嘴唇偶尔动一下。从背后看过去,真像一尊旧旧的雕塑。也不知是不是从前当海军养成的习惯,他能这样站上两三个钟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头上的火星明明灭灭的,像他沉默的心事。
等到太阳完全爬上天了,外婆在厨房里喊:“吃早饭啦——”他这才慢吞吞地把烟头摁熄,收进一个小铁盒里,转身朝我们走过来,脸上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笑。
外公最盼着见我。三年级那年,我从箬山转学去了温岭,不能常常见到外公外婆了。每次打电话过去,外公一听我们要来,就在那头高兴得话也说不清楚:“要走来啊!我帮你们把床铺好了……”其实他是想说“床铺好了”。我就在这头纠正他,爸爸妈妈在旁边低声笑。外公也不争,只是嘿嘿地笑着,像个做错事又开心的小孩。
去外婆家要经过一座小山。我们的车刚停稳,就能望见外公站在山顶上朝我们挥手。他赶紧把烟从嘴里拿下来,不知喊着什么,然后就一步一步、有点蹒跚地走下来接我们。等他走近了,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就全笑开了,手里还总拎着一个红塑料袋——那是他特意给我留的水果,洗得亮晶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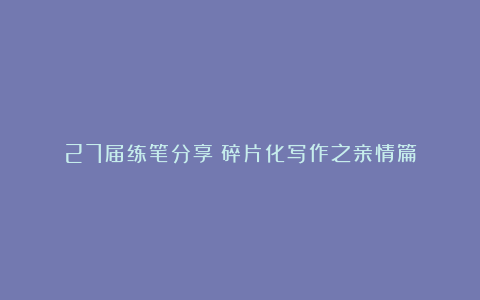
后来外婆家搬进了小区,不用爬坡了。可每次我们去,外公还是早早地等在小区门口,远远地就朝我们招手。他花白的头发顶上,依旧飘着一缕淡淡的青烟。
第二天我们要回去了。衣服都被外公洗好晾干了,行李也收拾得整整齐齐。阳光斜斜地照进阳台,外公还站在那个窗边。只是这一回,我忽然发现,他的背好像比上次更驼了些,等他转过身来,脸上的皱纹,也深得更明显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笑了笑。
5
外祖父二三事
18班 陈歆恬
外祖父的屋子总是乱糟糟的,各种鱼竿、鱼线、过季的衣服堆在一起也不理。随意在哪一抹,就能抹出厚厚的一层灰来。最令人忍受不了的,是大扫除时,从他床头发现的一窝逃窜的蟑螂。
外祖父很少出门,即使在家也很少走动。他唯一出门的动力便是钓鱼。曾有段时间,只要不下雨,外祖父就骑着电瓶车,拎着个水桶和板凳,带上渔具,在桥下找个阴凉处钓鱼。我也跟他去过,可在挂鱼饵、放线之后便无事可做,就盯着水面磨着时光。往往是日上三竿,阳光挪着步子过来了,我们又往旁边挪。外祖父总是不厌其烦地重挂鱼饵,重摆鱼竿。放鱼饵的袋子空了,怎么就钓不上呢?他对此毫不在意,静静地望着水面,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带着神力吸引他似的。
一般是坐了整天也没成果,可偶尔也能钓上几条小鲫鱼。他就很高兴一般,打电话来兴冲冲告诉我:“又钓上啦!给你们送来煮汤喝。”我笑了。总觉得外祖父送来的鲫鱼,熬的汤要比买的鲜。
外祖父少出门还有一大原因——他很少买菜。一个人在家,他懒得烧菜。倒一碗酒,大白米饭,拌点咸菜,便是一日三餐。“吃那么麻烦干什么?平时随便吃饱就好了。”他说。他喝酒也不醉,一杯杯下肚却仍清醒。他甚至在我儿时常怂恿我喝点酒,吓得母亲赶紧将我拉开。
到了逢年过节,亲戚好友都聚来了,外祖父才大展厨艺烧满桌子的菜。最后一道菜上齐了,他才坐下吃,没吃几口又忙着不知干什么去了。厨房里又响起一阵锅碗瓢盆的奏乐。
自从给外祖父换了手机安了宽带,他又少去钓鱼了。母亲说,他整天就坐在床上捧着手机。一天晚上,跟外祖父视频通话。他那黝黑的脸呈现在屏幕上,眼睛紧贴屏幕细细地看,直到认出我们才皱纹一扭一扭地笑起来。“……要多出去走走。”母亲劝他,“总盯着手机眼睛不好。”外祖父不听:“一把年纪了,眼睛坏了没关系。”母亲无奈摇摇头。耳朵又不好,眼睛坏了怎么行?
他的视力确实差了,精神差了,整日不知所为,越频繁地发呆、出神。
怎么回事呢?外祖父老了。
6
外婆印象
18班 吴彤
外婆是个慈祥的老人,面上总带着微笑,说话温声细语,从不发怒。
我敲响了外婆家的家门,才抬手敲几下,门就“咔嚓”一下打开,外婆站在门边,身上带着刚从厨房出来的热气,双手擦了擦沾了斑斑油迹的白布围裙,一边唤着我的小名,一边拉着我的手进门,说着“囡都长这么大了”,皱纹舒展成了一朵花。
外婆是擀麦饼皮的一把好手,外婆一手拿擀面杖,一手拿一团翠绿的面团,“啪啪”拍几下,又将面团揉捏、伸展开,擀面杖使着巧劲,一只手旋转饼皮,另一只手灵活地擀面皮。没过多久,一张大小适宜,均匀平整的麦饼皮就诞生了。
外婆又坐在沙发上,捏着一枚细针,缝补孩子们的衣物。外婆眼神不好,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总要眯着眼,伏着头,才看得清针脚,一针一线地密密缝补。
临走时,外婆总一个劲向我手中塞着零食或蔬果,问我是不是很忙?什么时候再来……
7
晨曦,锄头
17班 陈奕璇
爷爷总爱抚那锄头。
清晨,乡下,公鸡打鸣,爷爷便起床了,扛着锄头,穿好靴子,就到地里去。我在窗口望着,晨曦渐起,日光慵懒洒在他身上,四周喧嚣声未起,烟火味亦未浓,气息中只余泥土芬芳。爷爷带着锄头,让锄头亲切问候他的小菜苗们,问问他们是否营养不够,问问他们杂草是不是又欺负它们跟它们争地盘了,接收了信息,爷爷便拿着锄头,对准泥土,刨出杂草来,也一并挖出土来。埋藏其下的泥土被翻出来,泛着水汽,似乎朦胧中刚睡醒。爷爷挥动手臂,略弯着腰,一下将锄头落下,在往后一带,一拖,杂草便被连根铲除。
那是小时候。后来,时间一长,那锄头纵使再被呵护,也爬上了岁月的箴言。每每下午,爷爷总爱搬张竹椅,坐于门前,旁边竖放倚着锄头。他抚着它,看着木头中深深浅浅的泥土,卡在裂纹中,喃喃自语,却又像与多年的老伙计对话——这老伙计见证了几十年来晨曦微光中的菜苗,也见证了丰收世界紧紧挨在地下的土豆,见证了无数最终受我们全家夸赞的蔬菜。爷爷与锄头,无需多言,爷爷心血来潮想种玉米,它便答应,陪伴着爷爷见过每一滴露珠。
不知为何,总觉得爷爷中的菜尤其鲜甜,每每奶奶端上菜,他总要一个劲往我碗中夹菜:“囡,快尝尝,这新品种嘞!”盛情难却,勉强夹一筷子,却总让我这不爱吃菜的人忍不住想吃光这盘菜。家中其他人也同我感同身受,这盘菜成了饭桌上最抢手的,每逢这时,爷爷总摆摆手:“我是业余的,不会种,那锄头才是专业的嘞!”于是,就这样,四季轮转,却总有那一盘菜。
后来,老家拆迁,新房门前没有地,那把锄头也未扔,在屋口,回忆着数十载来晨曦中,回忆着爷爷种下的一株株菜,回忆着家人在饭桌上的欢声笑语,承载着爷爷掌心的深纹,承载着岁月。
8
家有“顽童”
18班 郭敏熙
我的妈妈好像比我还幼稚。
这天,暮色渐浓,窗外的夕阳泛出蓝紫的霞光,可我对这丝毫提不起兴趣,无味地扒完几口饭,起身离开餐桌,提起笔开始进入这全无硝烟的战场,似乎是察觉到了我心中的压抑与负面心理,妈妈悄无声息地起身,蹑手蹑脚走到我身旁,在我耳边说着:“坐这么久了多累,站起来走走吧!不如这样,我们比金鸡独立,谁站得久谁赢。”说罢,也不等我回应,连拉带提地扶我起身,自己摇身一晃,开始单脚立着,我心中生出些滑稽,玩玩罢了,也抬起一只脚。半晌,妈妈晃了晃,似是要倒了,她赶忙展开双臂,像一只笨拙学飞的小鸡崽,憨憨一笑:“听说这样立得更久。”我见她摆动的样子,伸手一扶,自己却不慎落了地,“哈哈哈,你输了!”妈妈撩撩额前碎发,露出一双弯弯的眉眼,“你怎么这样!”说完这话,我自己都禁不住被逗笑了。冰冷的书桌前,是独属于二人的暖阳。
夜里。我支着头愣怔地对面前的墙壁发呆,手机屏幕却突然一亮,是妈妈打来的视频通话,一接通,就是一双满眼皆是我的笑眼,“怎么了?”“给你看个特别神奇的画面!”妈妈调转镜头,对向漆黑的夜空。“你仔细看这个云。”她用手指指,又对着那片云捏了捏,似是要把它摘下送我,我眯眯眼定睛瞧去,只见薄薄的云雾似为黑夜女神蒙上的一层轻纱,若隐若现的月色似云朵上潺潺的清泉,可这时,几个素白的身影从云层中掠过,似鸟又若风,如梦如幻不知其究是何物,它们好似扇动羽翼,围成一圈,不停地盘旋,徘徊,果真若正举行着什么盛大的仪式,“它们好像在循环诶!这会不会是外星鸟,不会把我抓走吧!”听着她故弄玄虚,哄小孩一般的语言,我噗嗤一声笑了:“这么幼稚。”可还是给她看了好一会儿的夜空,“好了好了,是不是很神奇,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呦!”言罢,还亲昵地把头偏了偏,我笑着摇摇头,看着她发来的“晚安”儿童表情包,心中若填了满罐的蜜糖。
妈妈是我家的“顽童”,每一刻都试图以自己的“顽”换来我放松的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