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新春的步伐红已在倒计时中缓缓来临,一组集字春联却让时光有了褶皱——纸上没有俗常的热闹笔触,反倒晕着元代赵孟頫笔墨特有的温润光泽。这不是赵氏为马年亲笔所书的新作,却是一场跨越七百余年的“笔墨对话”:每一个字都从《胆巴碑》《洛神赋》等传世碑帖中精挑细选,经@见自己逐字校准、拼合成章,最终让赵孟頫的秀雅风骨,与马年新春的喜庆意趣撞了个满怀,墨香里全是藏不住的千年雅趣。
这组春联的妙,先在“字”的选择里藏着巧思。赵孟頫的书法素来以“温润如玉”著称,楷书端庄而不板滞,行书灵动而不跳脱,恰好避开了传统春联常见的浓艳与粗犷,让新春的喜庆多了几分书卷气。就像“龙腾辞旧岁,马跃启新程”一联,“龙”字取自《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笔笔中锋稳实,竖弯钩处带着含蓄的弧度,似龙尾轻摆的灵动;“马”字则从《闲居赋》中撷取,横画轻起,竖笔劲挺,四点如马蹄踏地,虽无动态,却藏着跃然欲动的气势。更难得的是字与字的呼应:“腾”字的舒展与“跃”字的紧凑相映,“辞”字的婉转与“启”字的刚健相衬,哪怕是“岁”“程”这类笔画繁简不一的字,也通过间距的微调,让整联疏密有致——仿佛赵孟頫当年挥毫时,早已将马年的意趣融进了笔锋,每一个字都不是孤立的碑帖片段,而是为春联量身定制的“活字”。
比字的选择更见匠心的,是“联”的意境与赵氏笔墨的契合。马年春联常离不开“跃马”“奔腾”的意象,若用过于刚猛的书风,易失雅致;若过于柔媚,又难显马的劲健。而赵孟頫的书法恰好有“刚柔并济”的特质,能将喜庆与清雅揉得恰到好处。比如“春风送暖驰千里马,旭日东升照万重山”一联,“驰”字笔势连贯,走之底的捺画如骏马扬蹄后的惯性,带着向前的冲劲;“照”字的四点底温润饱满,似旭日洒下的柔光,中和了“驰”字的动感。整联读来,既有“千里马”的豪迈,又有“春风暖”“旭日升”的温情,而赵孟頫的笔墨就像一根丝线,将这份豪迈与温情串得妥帖——笔画的粗细变化里,藏着春风的轻软;结字的开合间,见得山势的开阔;连墨色的浓淡都似有讲究,“马”“山”等字墨色略重,似画面的焦点,“风”“日”等字墨色稍淡,似背景的晕染,让春联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像一幅笔墨淡远的山水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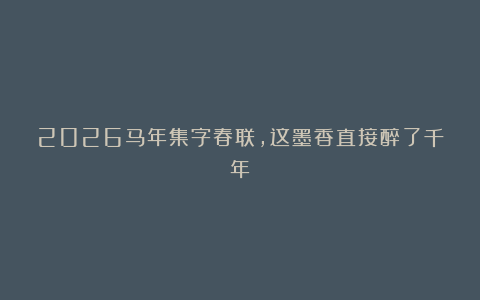
最动人的,还是这组春联里的“穿越感”——它让现代人在贴春联的瞬间,与元代的赵孟頫有了一次隔空对话。我们想象着,当年赵氏在案前挥毫时,或许也曾为新春写过联语,只是那些墨迹早已湮没在时光里;而如今,网名@见自己,从浩如烟海的碑帖中,将那些散落的“字”重新拾起,拼合成马年的祝福,就像把散落在历史里的星光,重新聚成了一盏灯。当我们把这组春联贴在门上,红笺上的“赵体”不再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展品,而是能触摸到的温度:晨起时,阳光照在“马跃”二字上,似能看见笔锋划过纸页的痕迹;傍晚时,灯光映着“春风”二字,似能闻见墨汁晾干后的清香。这种“触摸历史”的感觉,是寻常春联给不了的——它让新春的仪式感,多了一层文化的厚度,让我们在庆祝马年的同时,也与千年的笔墨传统撞了个满怀。
有人说,集字春联不过是“剪剪贴贴”,算不得真正的创作。可只有懂行的人才知道,要从数十种碑帖里找出能组成春联的字,既要匹配字形、字势,又要贴合联意、年味,难度不亚于重新写一副春联。@见自己在逐字校准时,要考虑“马”字的结体是否与“龙”字协调,“驰”字的笔势是否能与“跃”字呼应,甚至连每个字的大小、倾斜角度都要反复调整,只为让整联看起来“宛若天成”,没有一丝拼接的痕迹。这种“于细节处见真章”的匠心,恰是对赵孟頫笔墨精神的传承——赵氏一生追求“古法”,讲究“用笔千古不易”,而这组集字春联,正是以现代的方式,延续了这份对笔墨的敬畏与执着。
当2026年的鞭炮声响起,这组赵孟頫集字马年春联,会在千家万户的门上绽放墨香。它不是最热闹的,却是最雅致的;它不是最张扬的,却是最有故事的。每一个字都藏着元代的月光,每一联都裹着马年的春风,在红笺与墨色的碰撞里,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副春联,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让古老的笔墨,在新的时代里,依旧能开出雅趣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