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一统志》(光绪年间印本)
方志学
清代“大一统”理念抵边中的方志编纂实践
——基于云南边境府州志的考察
方天建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5年第2期】
摘 要:方志编纂,为清代“大一统”工程的重要体现形式,彰显着一统天下的王朝意志。历史上被称为徼外僻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在清之前,几无官修志书备考,然自康熙朝始,随着方志编纂工程的推进,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部正式性方志纷纷呈现,如嘉庆《广南府志》、乾隆《开化府志》、雍正《临安府志》、康熙《元江府志》、道光《普洱府志》、康熙《永昌府志》和乾隆《腾越州志》等,成效显著,成为推广“ 大一统” 理念的重要载体,透视清王朝文化统边、治边的重要实践方式。再则,边境方志通过序言与统一性的体例编纂形式,彰显文献编纂“润物无声”的“大一统”理念融入与宣传功能,成为考述“大一统” 理念推及边地的重要文献证据。
关键词:清代;云南边境;方志编纂;“大一统”
“大一统”,作为清朝康雍乾时期在历史文献(《清实录》《大清一统志》和相关地方志)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不仅成为清王朝统一疆域的重要思想助推器,还是其推动政治和文化一统的重要指导思想。因之,有关“大一统”理念的研究,也成了近年来学术界关注清史的热门课题,并产出了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诚然,正如“大一统”理念所透视的核心主旨一样,需要形成疆域、政治、文化和观念等方面的天下一统,因之清王朝围绕其开展的相关举措亦是由大到小,由宏观到具体,进而使得国内有关“大一统”研究的学术脉络亦遵从该基本规律。再则,就康熙年间编纂地方志的思想主线而言,无疑是将“大一统”理念传播天下,进而形成从清王朝中央统编《大清一统志》到各省级单位编纂通志,再到各府、州、县编纂府志、州志和县志的层层递进关系。然而,就当前国内学界有关清代“大一统”理念的研究现状可见,从宏观层面的中央到中观层面的省级地方,均有研究成果体现,但具体到“一统到边”的边境府、州、县层面,相关研究则较薄弱。因此,有必要从清代边境方志编纂层面,专门审视大“大一统”理念抵边的形式、特征与价值问题。在此前提下,本研究专门以清代云南边境方志编纂中的“大一统”理念融入问题为切入口,深入考察“大一统”理念“一统到边”的形式及其特征,进而就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文化统边、治边价值展开必要论述。
一、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形式
考察“大一统”理念融入方志的编纂形式,需要明确清代云南边境的地理行政区划。就行政版图而言,据《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全图》显示,清代云南桥接国外的主要边境府、厅,由东向西,主要有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元江军民府、普洱府、顺宁府、永昌府、腾越厅。然而,在乾隆朝之前,当下云南省临沧市所辖的边三县(沧源、耿马和镇康)地区,均归永昌府辖制,而非顺宁府管理,因此有关该地区的边境属性,特别是相关“大一统”理念的实践考述,还需回归到康熙《永昌府志》和乾隆《永昌府志》的记载中找寻证据,而非《顺宁府志》。
(一)“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方志编纂的由来
无论是明朝还是清代,“大一统”理念直接或者间接地呈现于方志编纂中,其本质乃是为编纂《大明一统志》或《大清一统志》提供地方志书支撑,进而亦顺推了“大一统”理念在地方的实践与宣传。正如《大明一统志》所言:
盖自唐虞三代,下及汉唐以来,一统之盛,蔑以加矣。故惟覆载之内,古今已然之迹,精粗巨细,皆所当知。虽历代地志具存可考,然其间简或脱略,详或冗复,甚至得此失彼,舛讹淆杂,往往不能无遗憾也。肆我太宗文皇帝,慨然有志,于是遂遣使编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惜乎。
至于明代“大一统”理念是否融入云南地方志编纂,由于明代云南方志史料记录阙如,未知其详,仅能从明代万历年间云南按察使徐拭在隆庆云南《澂江府志》序言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云南镇宁州知州尹绍皋在万历《蒙自县志》序言中,初略管窥。如,隆庆云南《澂江府志》序言提及:“我朝平定之后,改澂江路为府,一统志及云南通志则概及之,而专志罔备,莫可睹记”。再如,万历云南《蒙自县志》序言强调,“蒙自故无专志。万历癸卯(1603,万历三十一年),前抚军育台陈公,既平东西逆彝,欲修滇之全志。檄下所属,各修邑志,以报时邑”。上述序言未直接提及明代“大一统”理念进入方志编纂,仅提及一统志与云南通志,难为实证。不过,明万历三十一年云南官员打算纂修全省通志,并要求云南省所属各地修志之事实,当为可信,亦可理解为云南单方面推动方志编纂之行为。然则,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地方志,则有据可考,当为编纂《大清一统志》之客观需求。就此,《嘉庆重修一统志》序言中有精辟总结,“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今二百年”,继而“圣祖仁皇帝始命纂修一统志,世宗宪皇帝重加编辑,至高宗纯皇帝御极之八年,甫获竣事”,后来还因“开拓西域地二万余里。因于四十有九年,续有成书”。
总之,为满足数次纂修《大清一统志》之需求,彰显清代“大一统”盛况,包括云南省府在内的省、府、州乃至到县,亦纷纷编纂方志,致使云南边境府县志从无到有,进而形成有志可考,有志备考的方志编纂高峰期。
就《嘉庆重修一统志》序言可知,《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始于康熙朝,成于乾隆朝。具体始于康熙朝何年,目前所见之中央与地方文献表述略有出入。据康熙二十五年(1696)对《一统志》总裁勒德洪等所作上谕载:
朕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览万方。因天文以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贡五服,职方九州,纪于典书,千载可睹。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钜典,名曰《大清一统志》。特命卿等为总裁官,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
就《圣祖实录》所见,《大清一统志》确定名称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该时间点在康熙《云南通志》的序言中亦有确证。云贵总督范承勋强调“讵可忽诸臣于二十五年,钦奉命来制”,因而“我皇上特命儒臣纂修大清一统志,诏天下各进省志”。云南巡抚王继文则直接说明了编纂《大清一统志》与编纂《云南通志》之间的内在关系,即“圣天子当久道化成之,会兼礼明乐备之休,特命儒臣弘开史馆,取十五国之成书,编大一统典训批图,搜籍规制精详,是省志也者”。
需要注意的是,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编纂省志,彰显清代“大一统”的时间,或者说康熙朝酝酿编纂《大清一统志》的具体时间,应该向前推移。就此,在宣统《蒙自县志》和道光《澂江府志》的康熙朝旧序中,大体能够验证。据康熙十二年(1673)蒙自知县王元弼在《蒙自县志跋》中可知,康熙时期推进《大清一统志》编纂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康熙十一年(1672)。王元弼在《蒙自县志跋》中明言:“壬子(1672)之秋,弼在都下,始闻卫相君疏请纂修《一统志》。制曰’可’。乃通行天下郡邑省会,各修其志”。
《圣祖实录》
另,康熙二十二年(1683)赐进士第中议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前铨曹掌选典试赵士麟为康熙《澂江府志》所作序言可知,“今上御极之十年,命天下修十五省之志,所以大一统也”,已在编纂省志中,不自觉彰显“大一统”的理念。
再,通过编纂省志,以显清代“大一统”理念,在康熙三十年纂成的《云南通志》中,亦有体现。云贵总督范承勋在《题名续纂云南通志疏》中提到,编纂《云南通志》,仍为服务《大清一统志》之所需,即“云南通志,先于康熙二十三年内,经前督臣蔡毓荣于会典正在纂修事,案内纂成大清一统志渐次告成,若独云南一省前迹未确未备,所系不止一隅,而实关乎全壁”,还是彰显康熙治世的必然体现,“且自二十三年至今,又越六七载。其间皇恩之叠沛,政教之日新,凡有裨于遐荒,悉犁然而具举,不加叙述,非所以仰佐圣治,共启文明也”。因此,需要对清王朝的强盛加以宣扬:
自本朝戡定以来,我皇上轸念遐荒,恩纶叠下,山川日益奠丽,彝汉日益安帖,沟洫日益疏濬,土田日益开垦,熙皞耕凿者,民风弦诵诗书者,士习休息而蕃衍者,户口输将而恐后者,贡赋虽山泽鱼盐之利,不敌中州而树畜稼穑之勤,渐臻乐利。抚今追昔,未有如我国家之声灵遐畅远迈千古也。
然而,康熙治世之下,云南则面临“当此之时,使滇志犹然阙略,其何以扬太平之盛治,昭大一统之弘规也”。因之,“滇志犹然阙略”的困局,云南省加快了编纂志书的步伐,使得康熙朝,成为云南各地编纂志书,特别是边境府县编纂志书彰显“大一统之弘规”的由来。这也开启了清代云南边境府、州、县,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乃至光绪年间的间断性百年地方志编纂历程。
(二)边境府厅志序言中的“大一统”理念
清代云南地方志的编纂,缘于康熙要求编纂《大清一统志》所需。因此,如何在方志编纂中彰显一统志需求和“大一统”理念,不仅是康熙《云南通志》编纂的使命,亦是云南各地方志编纂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此背景下,作为边徼之地的云南边境地区,始于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编纂的府志或者州志中,落实一统志需求,彰显“大一统”理念痕迹明显,为清代“大一统”理念在云南层面,实现“一统到边”实践的重要文化工程体现。
其一,滇东南边境府志中的“大一统”理念融入。滇东南边境地区,清代主要涉及广南府开化府,所涉及的府志主要有嘉庆《广南府志》、道光《广南府志》、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开化府志》。这其中,从嘉庆《广南府志》序言可知,广南府地区曾于康熙年间由知府茹仪凤初略辑录了一部广南郡志。茹仪凤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序言中明言:“广南一郡,自赵宋分道已入疆域,元明设府。历代服从,非苍山洱海、金齿叶榆,或顺或梗,何以延至今日,尚无郡志可稽,诚不可解也”。因之,其为了“兹当报政,期满如叨,恩命量移他,所以致夙愿,终虚生难释勉”,进而“采通志内列于广南条下数语,再参以己之所见、所及、所传闻者,草创是编”。又,乾隆年间,广南府知府单国光深感广南地区缺乏地方志的遗憾,难以彰显清朝盛世,即:
恭惟本朝定鼎以来,声教四讫,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我皇上践祚之年,添设附郭,宝宁县经画周详,以致边徼夷疆,输诚向化。一切城池、官廨库仓储,学宫坛庙,莫不釐然具备。而独志乘未修,洵阙典也。
基于彰显清朝盛名和大一统之需,单国光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强调,有必要纂修《广南府志略》,不然无以在“幸值风云日启之时,使任其志典,如将何以风斯民而宣圣化用,不自揣勉,为纂修似创也”。在上述背景下,嘉庆《广南府志》应运产生,并在序言中或多或少彰显着清代盛华边地的理念,正如该志编纂者何愚在道光五年(1825)的序言中认为:“虽然广南百数十年来,涵濡圣泽,声名文物科目迭兴。予又守此日久,使郡志依然缺如”。可见,透视边地的涵濡问题与皇清盛泽,特别是声名文物兴旺,成为广南府编纂《广南府志》的重要缘由。该缘由,道光《广南府志》编纂者李熙龄的序言则更为直观,其言广南府“虽为边地,而涵儒圣化已二百余年,文物声明几与中土等,不其盛欤”,然遗憾的是“惟广南旧无志书”。
此外,就清代滇东南地区另一边境重镇开化府而言,其修志的脉络较为清晰,主要涉及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开化府志》两种。无论是在乾隆《开化府志》序言中,还是在道光《开化府志》新旧序言里,融入或者彰显清代“大一统”理念,成为了重要的核心思想。尤为明显的是,乾隆《开化府志》编纂者汤大宾在序言中即看门见山地强调,“今天下车书一统,凡雕题凿齿之伦、兽居鸟语之域,罔不绘图以进,使四邮险塞如几席之近者然”。云南巡抚刘藻强调“仰赖圣天子德教洋溢,遐方绝域,罔敢不共,而交人尤修职贡惟谨”的声教显扬。云南粮道罗源浩强调,开化府地区“百年来,生聚教训,煦育益深,几于家弦诵而户诗书矣”,然“惟是地处山隅,纪载无闻,志乘未有成书,盖亦阙典也”,无法彰显清代“我国家肇造,区宇九囿久式,于康熙四年(1665年)始设郡治,易髻跣为冠裳,泽蛮僰以礼乐,谓非千载一时,变草昧而文明者欤”的一统盛世光景,因之“夫志之在边徼,视中土为尤亟”。而《开化府志》的编纂,被云南布政使傅靖认为是“可以镜往昔,即以诏来今,询有合于外史之遗意,而足以导扬美盛,昭国家一统无外之鸿模矣”的大事,被云南学政叶观国认为是“开郡文学既骎骎日盛,又得太守以文教治其郡,多士将益泽于诗书,于以鼓吹休明,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虽边地何难与中区匹体哉”的重要文教工作。
再则,虽然乾隆《开化府志》未明确提及其编纂的缘由,即为编纂《大清一统志》或者《云南通志》所服务,但其中或多或少彰显的“一统”理念和清朝声教问题,已经间接透视了其对“大一统”理念的实践。另,道光《开化府志》承袭乾隆《开化府志》,其编纂理念和指导思想几乎缘于乾隆《开化府志》序言,没有过多新的序言强调“大一统”意识或者理念,但其却强调了续修《开化府志》,其实是为纂修云南省省志提供证实所需。其编纂者周炳在其序言中明言,“道光乙酉岁(1825年),大府纂修省志,来取事实”。
其二,滇南边境府志中的“大一统”理念融入。就清代滇南而言,具体地理范畴主要指代临安府、康熙元江军民府和雍正年间新设的普洱府所辖之地,为清代云南南部典型的边境之地。因之,滇南地区所涉及的边境府志,主要有雍正《临安府志》、康熙《阿迷州志》、雍正《阿迷州志》、嘉庆《临安府志》、康熙《元江府志》和道光《普洱府志》。
在几部清代滇南边境方志中,雍正九年(1731),《临安府志》的编纂者张无咎在编纂序言中明确提出,该志的编纂是为服务国家编纂《一统志》所需,“恭逢天子勅命儒臣修一统志,制府少保鄂公、大中丞张公奉修滇南省志,遍檄滇属郡邑,俱各修志,以备采择”。此类表述,嘉庆《临安府志》编纂者江濬源在序言亦强调,“国朝一统志及云南通志,裒集而续编之门类,无嫌于相洽体裁,间附以鄙见”。此外,作为临安府所辖之阿迷州,其州志中,亦明确了方志编纂的国家需求和“大一统”理念。如,康熙《阿迷州志》编纂者阿迷州知州王民皞强调,“圣君贤相隆治化于一统,纂志书于千祀,甚盛举也”。再如,雍正《阿迷州志》编纂者阿迷州州牧陈权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序言中强调:“圣天子御极以来,开辟前古未有之土地,化千古未有之民人。令近臣鼓吹休明,修大一统志,转饬各省志互为证订,诚千古未遇之盛典。爰是宪檄下各府州县,重修乘志”。
另,就“大一统”理念,特别是为编纂《大清一统志》服务,云南巡抚吴存礼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元江府志》的序言中明言,编纂方志的目的为服务纂修一统志,彰显清朝盛世,即“皇清御宇,版图式廓,梯山航海,重译来朝。皇帝命在廷诸臣纂修一统志,垂宇宙壮山河,何其盛也”。 道光普洱府志的编纂者之一郑绍谦强调,普洱地区在道光之前,由于“不有志乘纪之”,致使无法彰显“其何以备一方掌故上昭,圣天子揆文、奋武、声教、四讫之郅治乎” I2的清代盛况。于是,郑绍谦等人通过“综览方册,搜括远近,证以汉唐元明诸史,并旁摭先儒记注及滇中杂记各遗编”,进而“撮其要于简而能该仿照《大清一统志》及《云南通志》,裒为是集”。可知,道光《普洱府志》的编纂,亦深受大清“一统”思想的影响,因为其相关编纂原则,为仿照《大清一统志》和《云南通志》使然。
总之,清代滇南地区的几部边境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均或多或少透视着“大一统”指导思想的痕迹,深受清代《一统志》编纂思维的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地将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到方志编纂中,进而将“大一统”理念通过文化工程编纂的形式,推及滇南边境。
其三,滇西边境府州志中的“大一统”理念融入。由于滇西和滇西南边境地带,清代大部分时段归属永昌府和腾越州辖制,因之该部分集中讨论永昌府所编纂地方志中的“大一统”理念,主要涉及康熙《永昌府志》、乾隆《永昌府志》、道光《永昌府志》、光绪《永昌府志》和乾隆《腾越州志》。这其中,就康熙《永昌府志》的“大一统”理念实践而言,康熙四十一年(1702),《永昌府志》编纂者永昌府同知李文渊认为,既是服务国家编纂《一统志》之所需,亦是增补永昌府旧志残缺之要求:
然窃思我皇上敏政勤民,博采风俗,纂修《一统志》。于是各省咸有省志进呈御览,天下风土情形,靡不周悉。所以斟酌时宜,动无不善,圣治之休隆,真前古所未有也。但省志本于郡志,宁有有省志而无郡志者乎? 且旧志既已残缺,此而不修,其后不可问矣。绝续之机,正在此时。
另,就康熙四十一年编纂《永昌府志》的意义,特别是彰显清代强盛和“大一统”意义,亦得到了时任云南学政王之枢的积极认可。其认为,永昌府虽是“西南徼外地,置郡自汉始,迨有明欲化导诸彝,率以金陵人戍其地”,然其“故人物语言彬彬然有江左之风,实西南徼外一都会矣”。不过遗憾的是,“我朝定鼎以来,武功远振,文德广敷,所以登之衽席,陶之学校者已久,而独郡之旧志残缺弗备”。因之,康熙《永昌府志》的编纂,“足以艳羡后世”。
再,就《永昌府志》中所彰显的“一统”盛况,特别是在永昌府辖区的体现,道光《永昌府志》的编纂者永昌府知府陈廷焴在道光六年(1826)的序言中明言:
自我朝定鼎以来,天威遐畅,罔有不庭,而又得前之贤人君子,能宣朝廷德意,化及荒服。是以内而孟定各土司无不恭顺爱戴,俗易风移;外而缅甸诸彝亦莫不向风慕义,纳赋输诚。数十年间钲销鼓息,斥堠无惊。猗欤休哉! 历代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最后,永昌府辖区,除了康熙朝积极编纂府志,以因应康熙帝编纂《大清一统志》上谕要求外,乾隆时,该府所辖战略要地——腾越地方官员,也积极编纂《腾越州志》,进一步彰显边地官员实践清代“大一统”理念的积极之心。乾隆《腾越州志》编纂者屠述濂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序言中,明确强调了“大一统” 思维,即“且夫一统无外者,圣代之隆规也,筹边必备者,守臣之专责
也”。
二、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特征
清代“大一统”理念,主要通过省府官员和边境官员序言的形式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因之,形式透视特征,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亦体现着省府官员宣传推介和边境官员实践作为的显著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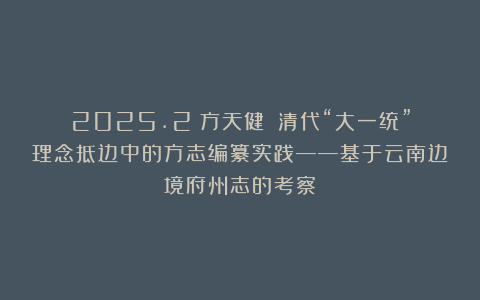
(一)省府官员宣传推介
在目前所存的清代云南边境府州县志中,通过省府部门官员序言的形式,加以宣传清代盛况与文教抵边行为,为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直观体现。这其中,按照编纂时间顺序,涉及省府官员作序的清代云南边境方志主要有康熙《永昌府志》、康熙《元江府志》、乾隆《永昌府志》、乾隆《开化府志》和道光《普洱府志》。就地域而言,涉及云南清代早期边境五府中的三府,仅广南府和临安府方志中未载省府官员序言。
在上述几部方志中,所涉及的省府官员主要有:为康熙《永昌府志》作序的云南学政王之枢,为康熙《元江府志》作序的云南巡抚吴存礼,为乾隆《永昌府志》作序的云南布政使费淳,为道光《普洱府志》作序的云南按察使梁星源。另,尤为特殊的是,为乾隆《开化府志》作序的省府官员较多,人员达5人,应与该时期的“安南勘界案”尾声影响有关。他们分别是云南巡抚刘藻、云南学政叶观国、滇藩使者傅靖、云南粮道罗源浩,以及云南东巡使廖瑛。这些省府官员亦分别在其序言中,或多或少强调了清朝盛世与“大一统”理念。
如,云南学政王之枢在康熙《永昌府志》序言中强调了永昌府“武功远振,文德广敷,所以登之衽席,陶之学校者已久”的“一统”武功文德理念。云南布政使费淳在乾隆《永昌府志》序言中,则通过明言永昌府久入中国版图的方式,以强调永昌府在国家一统中的藩篱作用,“永昌自西汉通中国,属益州,其隶版图也久”,因之其若“边境有事,其忧不止一郡”。云南巡抚吴存礼在康熙《元江府志》序言中,不仅强调了康熙皇帝“命在廷诸臣纂修一统志,垂宇宙壮山河,何其盛也”的清朝“大一统”由来,还就“一统”盛况惠及元江地区的成就加以宣传,即作为滇之西南“于地为最僻”的元江府,因“前之抚滇者,惧其扰而难驯也,爰以极边之四郡,拣选贤能,奏请调补以资弹压,而元江府首列”,而在吴存礼等人“因势利导,上慰九重南顾之虞,岂不亦光盛世而尽臣职也哉”之下,最终形成“圣朝涵濡教养,沐浴膏泽者,既深且久,于是乎烈焰遐荒,不复作羌髳”的盛世局面。
另如,云南巡抚刘藻在乾隆《开化府志》序言中,则强调了“仰赖圣天子德教洋溢,遐方绝域,罔敢不共,而交人尤修职贡惟谨”的中外一统观。云南学政叶观国认为,《开化府志》的编纂,使得开化地区“多士将益泽于诗书,于以鼓吹休明,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虽边地何难与中区匹体哉”。滇藩使傅靖认为,《开化府志》的编纂,“足以导扬美盛,昭国家一统无外之鸿模矣”。云南东巡使廖瑛认为,《开化府志》纂成,是“统一代之制度为史,列九有之陈迹为志” 的体现。再如,就《普洱府志》的纂成,云南按察使梁星源在其序言中,明确强调其所体现的一统作用,即“初始开辟,入版图,属元江,以通判治之,后专设郡,隶以宁洱、思茅、威远、他郎,于是夷俗渐革而文教兴焉” 。
(二)边境官员实践作为
相较之省府官员通过序言宣传推介“大一统”理念方式,边境官员则积极通过编纂方志,来加以实践和倡导清代盛世抵边的“大一统”需求。如,乾隆《广南府志略》编纂者单国光强调,编纂方志具有宣传教化斯民的重要性,“当文教昌明之日,幸值风云日启之时,使任其志典,如将何以风斯民而宣圣化”。嘉庆《广南府志》编纂者何愚明言,编纂方志,其实是为了彰显“广南百数年来,涵濡圣泽,声名文物科目迭兴”的盛况。
嘉庆年间清代疆域
又如,雍正《临安府志》府志编纂者张无咎认为,纂修临安府志,不仅是为了“恭逢天子勅命儒臣修一统志,制府少保鄂公、大中丞张公奉修滇南省志,遍檄滇属郡邑,俱各修志,以备采择”的需求,还是补正曾经临安旧志“凡疆域之广狭,风俗之贞淫,田赋之损益,城池之修废,学校人才之盛衰,文章政事之得失,忠孝节义之显晦,以及隐逸流寓、灾祥、寒暑、土司彝种之属无”的现实需求。另,雍正《临安府志》主要编纂者之一的建水州知州夏志源则明言编纂《临安府志》,主要还是彰显清朝“大一统”之盛,亦是推动临安府地区的“教养斯民之道”,即“各上宪承宣,朝廷德意方将,合二十余郡之风尚,著为成书,以彰’大一统’之盛。而临志一? 实际其会当亦载笔者所不遗,而于教养斯民之道,不无少补云”。又,元江府知府宁祝宏在其所撰的雍正《临安府志》序言中,明确表示了该志编纂的“大一统”理念实践:
各州县志采十之五,搜博考才十之二,荟萃成帙,纲张目举,条分缕晰。详而有要,简而能该。诚足昭东迤大观,补百年遗事。而后之莅兹土者,展卷了如,当无忧其缺略也。方今圣天子文德武功,远及六合。两台大宪,经纶事业,彪炳西南,非复昔年封域。正欲汇纂通志,献于当宁。俾信今传后,以此帙察一郡之形势,可备一得之采乎。
再,嘉庆《临安府志》编纂者江濬源认为,方志的编纂,“其义归于扶树教道,提摄人心,垂之方来,用资观省而已”,置之临安府再次续修《临安府志》,则因之前方志“凡耇老之所尝见闻,风韵盛采之尚能仿佛者,历时寑久,纂述蔑如盛美之迹,无以传政教之流,莫之继守土者憾焉”。
另如,康熙《元江府志》编纂者履成人认为,元江府“虽要荒远在万里,民尽彝猓沐化已深,倘一旦采风者辱临兹土,无一郡志以表明其疆域、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风俗、户口、政论,亦守土者之羞”。可见,康熙《元江府志》的编纂,亦是为了服务国家或者省府编纂“一统志”或者“通志”所需,希望通过疆域、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风俗、户口和政论等“一统志”编纂体例要求,来实践和倡导清代文化工程推进中的“大一统”理念。另,道光《普洱府志》编纂者之一的郑绍谦认为,该志的编纂,不仅是对道光六年(1826)“修云南通志,奉檄采访郡人,所集四属志稿,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究不足为善本”缺憾的完备,还是撮其要“而能该仿照《大清一统志》及《云南通志》”,进而实现“补此百年缺典,勒为一郡成书”的幸事。而道光《普洱府志》编纂仿照《大清一统志》和《云南通志》体例的做法,无疑也是在不自觉地彰显清代的“大一统”理念。
再如,康熙《永昌府志》编纂者之一的罗纶,虽未明确强调“大一统”理念,但其在序言中,亦表述了康熙朝的“天威遐畅”盛况。其认为,“麓川内列三宣,缅甸亦系羁縻,以及车里、老挝、木邦、孟艮之属,熙然宁帖,无敢稍有蠢动”,缘由“皆赖我皇上天威遐畅,故悉宴安如此” 。因之,“则官斯土者,幸际太平之世,即举斯土之事宜而熟习焉、胪列焉,缕悉条张,无微不备”,方能实现“俾后乎此者,不事阅历,不烦搜采,一览而洞若指掌。未求其治之之法,先得其治之之迹,盖亦斯土之要务,尤为官斯土者之明鉴也”。另,康熙《永昌府志》编纂者之一的李文渊,则强调了该志编纂与“大一统”理念之间的直接关系。其认为,编纂该志,不仅是为了服务“然窃思我皇上敏政勤民,博采风俗,纂修《一统志》。于是各省咸有省志进呈御览,天下风土情形,靡不周悉”的现实需求,而且是彰显“所以斟酌时宜,动无不善,圣治之休隆,真前古所未有也”的“绝续之机”。因此,该志的编纂,“条例悉遵《通志》”,强调对“大一统”理念规范性实践的经典版本。
三、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价值
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的形式和特征透视,文献典籍缺失,边境治理无典可考,无法彰显清代“大一统”背景下的文治武功盛况,为当时主政云南边境地区官员所面临的相同困境。而在响应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文功背景下,作为边徼的云南边境地区,方志编纂工作相继开展,纷纷进入有志可考和有典可循的时代。因此,在“大一统”理念助推下的清代云南边境方志编纂工作,一方面彰显着“文献抵边”,弥补边境地区方志缺失遗憾的文献价值;另一方面透视着“思想到边”,衍生边境地区文教护边的积极思想价值。
《新纂云南通志》
(一)“文献抵边”,弥补边境地区方志缺失遗憾
在清代云南边境地区数部地方志的编纂序言中,编纂者均强调边徼地区缺乏方志的遗憾。因之,在清代“大一统”编纂方志的推动下,使得没有方志的边境府地区,纷纷出现方志编纂热潮,可谓是“文献抵边”的聚焦体现,亦是体现“大一统”助推云南边境府地区实现“方志抵边”的关键举措,更是为系统考察清代“大一统”理念在云南边境地区编纂方志的实践,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资料层面的历史活态证据,彰显了积极的“文献抵边”价值。
其一,清代滇东南地区方志编纂中的“文献抵边”价值。如,嘉庆《广南府志》未编纂之前,广南府地区的地方官员遗憾地强调,“其地之荒僻,事之掣肘,又为四郡之最,未免智勇交困,但念已蒙简拔”,因之虽然广南一郡“自赵宋分道已入疆域,元明设府。历代服从,非苍山洱海、金齿叶榆,或顺或梗,何以延至今日,尚无郡志可稽,诚不可解也”。嘉庆《广南府志》编纂者何愚认为,“广南边徼地,仕途畏为烟瘴之区也,明代土司自治之府。自我朝康熙十八年始,隶版图,设官吏,建学校,置弟子员,前乎此者,士大夫游览所不到记,咏所不及也”。道光《广南府志》编纂者李熙龄则认为,广南“虽为边地,而涵儒圣化已二百余年,文物声明几与中土等,不其盛欤”,然遗憾的是“惟广南旧无志书,有之自茹公仪凤始,继修于单公光国,再修于何公愚,自天文以至文艺规模亦稍备矣,而其中缺略甚多”。因此,清代两种《广南府志》的编纂,不仅弥补了广南府地区没有方志的缺憾,还是清代编纂《大清一统志》,彰显“大一统”理念中的“文献抵边”重要实践活动。就此,广南府本地人代表王佩璋、雷万钦、龚思醇、戴清、李如珠、胡万龄、胡庆元、严为琛、丁生聪等人在嘉庆《广南府志》编纂后的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广南夙隶沙侬,杂居苗猓,元明之代,既乏传人,边徼之区,讫无作者。今沐圣朝,菁莪之化党,庠序肇其规,又蒙大吏经籍之颁,法令典章宣其教。艾男叶女,咸知孝弟力田,摆子僰丁,渐识诗书。虽名儒硕彦继起者,未之或知,而音孤行伏处者,有可颇采。幸逢何太守纂修郡志,欲为我荒陬彰表乡贤。综千里之幅员遗逸必备,开百年之风气,盛事须传。
又如,乾隆《开化府志》中的云南巡抚刘藻序言认为,开化地区于清代改土设流,至乾隆时期“将及百年,建置沿革,已非其旧,而山川风物,以及典章制度、学校人文,复日新月异,咸馄耀于光明”,然遗憾的是“顾志乘阙略,无以备轩之采,君子少之”。因之开化府知府汤大宾等人,在“公务之暇,取郡中版籍文献之可征者,属辞比事,汇为十卷,俾千百年方隅事迹,原委条贯,瞭然在目。自兹阿僰诸部,悉得与中土文物抗衡,未可侪诸边幅之末矣”。云南学政叶观国认为,开化地区“外距交冈,内杂僰倮,实滇省东南之边隘”,但“郡旧无《志》”,难免使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产生“国有史,郡有志。盖文献之攸存,古今得失之林,岂吾开而独阙如何也”的“喟然叹兴”之憾。叶观国认为,乾隆《开化府志》的编纂,乃“今太守乃能于政理余暇,探求掌故,勒成志乘。观其纲举目张,不支不漏,其力可谓勤、其功可谓伟矣”。云南布政使傅靖认为,开化府“古西南徼外,僻处滇之东偏,壤逼交藩”,虽然“迨圣朝声教覃敷,八荒在宥,改土设流,遂为严疆重镇,涵濡德化者,百年于兹。迩来户诵家弦,风会骎骎益上”,但遗憾的是“顾文明日启,而志乘阙如,览古者不无文献无征之虑焉”。傅靖认为乾隆《开化府志》的编纂,具有“然创始较纂述为难,而创修于新辟之地为尤难”的“知与西华盘龙之胜竞秀标奇,以互相辉映”的文献创始之功。云南粮储等道罗源浩认为,“滇居天末,而开化一郡,尤僻在边幅,三面界安南,为卉服鸟言之地”,虽然“百年来,生聚教训,煦育益深,几于家弦诵而户诗书矣”,但遗憾的是“惟是地处山隅,纪载无闻,志乘未有成书,盖亦阙典也”。因此,其认为乾隆《开化府志》的编纂,实为是对“夫志之在边徼,视中土为尤亟”的补充。云南迤东道廖瑛认为,“去内陆而边省,去边省而荒徼,文物未开,声明未著,一摇笔而抚驭机宜咸属焉,又难之难者也”,而且具有“滇之开化,本三长官司地,我朝改流设府,控制交国,百年来恭顺无比,此亦开化无外之验也”的重要战略性,但遗憾的是“至今记载缺如,仅于省志中窥其大略”。因之,其认为乾隆《开化府志》的编纂,实为“其他法制典则,淑行偏才,靡不毕具,可谓宣扬德教能其官者矣”的重要体现。乾隆《开化府志》编纂者汤大宾认为,开化府“以九牛六诏之边,二台八戛之地,抚驭亦非易事。况幅员千里,僻在边隅,外控交冈,内蔽临广”,同时其“山川风物,记载无闻,即《通志》亦间有称述,多约略言之,究未勒有成书,诚缺典也”,于是其“爰于修建学宫之余,合僚属诸君,裒集成书”。
其二,清代滇南地区方志编纂中的“文献抵边”价值。就此,云南巡抚吴存礼在康熙《元江府志》的序言明言,“元江古惠笼甸界在滇之西南,于地为最僻,历代阻声教”,导致“前之抚滇者,惧其扰而难驯也,爰以极边之四郡,拣选贤能,奏请调补以资弹压,而元江府首列焉”,同时遗憾的是“元江向无郡志,间载通志者,略而不详”。因此,其认为,康熙《元江府志》的编纂,“然则是编也,不但便于展卷、披图、按籍索览,使天时地利,物曲人官莫不璧合珠联、星罗棋布,以之鼓吹休明,黼黻至治,于是编深有赖焉,余益叹章君之留心郡务,而非兢兢于簿书期会之所可及”。康熙《元江府志》编纂者章履成认为,“元江于古为荒服,不入版图”,虽然清朝“改设文武流官而以普洱等处附焉”,然而“因地极边,荒山古硗瘠编额无几”,致使“所历山川险恶,彝猓错杂,而瘴疠为虐,询诸父老,咸称证敛无常,而吏缘为奸,学校芜残,而教化未广,习俗犷陋而彝性叵测,道路迂危,而商
贾不前”,同时还“考滇省全志,元江一郡寥寥数语,略而未备,盖其地由圣朝新辟,即欲悉因革制度,而文献无证”。因此,其认为编纂该志,具有“创始之难不同于别郡,可以按籍而考稽,因时而删定者也”的特殊文献价值。
另,雍正《临安府志》编纂者张无咎认为,“临郡辖四州五县九土司,幅员之广,周环二千五百里许。田赋人民甲于两迤,且土彝种类繁多,哀牢瘴疠之乡,悉在境内。官斯土者,颇称难治”,同时“考旧闻得前守程公应熊所辑郡志,皆抄本,且残缺者十之三四,盖惜乎,其为备也”。因此,在为了“恭逢天子勅命儒臣修一统志,制府少保鄂公、大中丞张公奉修滇南省志,遍檄滇属郡邑,俱各修志,以备采择”的需求,其认为该版《临安府志》的编纂,具有“不博搜而备载焉,以是知诸公之补缺正误。事该文直信而有徵也,爰付剞劂用志弁言讵云,名山之业,足垂不朽哉”的文献价值。
再,云南按察使梁星源在道光《普洱府志》的序言中认为,“考云南为天下之边,而普洱尤为云南之极边矣”,虽然“百数十年来,风俗人情居然中土而其朴素纯良,似犹过之”,但在志书编纂方面,“前太守郑公创撰志稿,残缺太多,存者亦未确,后任皆为日暂,未能补其缺略”,因之其认为,“庚戌志成,问叙于予,予时乘臬是邦,仅两月旋奉命作藩于鄂,予愧是邦之风土人情,尚未洞悉得是书,而边境之情形了如指掌矣”。道光《普洱府志》编纂者之一的郑绍谦认为,普洱“窃以兹郡素称边要繁剧,非可猝理恒兢兢滋虑焉”,进而形成“肇造以来,纵僻处南陲,抑亦守土者,所可藉手报最也”的局面,遗憾的是“不有志乘纪之,其何以备一方掌故上昭,圣天子揆文、奋武、声教、四讫之郅治乎”。因之,其认为该志的编纂,具有“就正补此百年缺典,勒为一郡成书,岂非幸欤”的文献补正价值。
其三,清代滇西地区方志编纂中的“文献抵边”价值。康熙《永昌府志》编纂者之一罗纶认为,“且吾永地处极边,去京师万余里,以天下论之,滇为最远。以滇论之,永昌又为最远”,因而“幸际太平之世,即举斯土之事宜而熟习焉、胪列焉,缕悉条张,无微不备”,但遗憾的是“至于溯治乱之遗踪,吊往昔之故迹,抚今思古,考物辩务,非阙逸无稽,即简略不备”。由此,其不由感叹到“吾永无志久矣,此一方之典故,倘任其废失无征,吾之责,亦子之责也”。而该志书的编纂,其认为是“永昌无志而有志矣”的大事,并能起到“俾后乎此者,不事阅历,不烦搜采,一览而洞若指掌。未求其治之之法,先得其治之之迹,盖亦斯土之要务,尤为官斯土者之明鉴也”的积极文献参考价值。康熙《永昌府志》编纂者之一的李文渊认为,“云南为中国边地,永昌又在其极西,郡之远者,莫是过矣”,虽然永昌地区“山川、风土、人才、物产,未尝不与中州等,殆骎骎乎其日盛也”,不过遗憾的是“然皆略而未详,览者每有未尽之叹,是《府志》之修何可少也”。因此,其认为康熙《永昌府志》的编纂,具有“俾后乎此者,于以俯筹民生而仰赞圣治,取诸此而已足矣! 则永昌亦何远之有”的积极“文献抵边”功能。
清代云南地区简明图
另,乾隆《腾越州志》编纂者腾越州知州屠述濂认为,作为“守土边臣”,他到访腾越边地,直达阿瓦地区,“于山川之险易,关隘之周防,夷情之顽顺,已足亲履之,目亲睹之矣。而犹谦让未遑,缺所记述,其何以扬休命而答前贤”。然而腾越州“自万历之末,以迨于今百六十七年,不但续修无闻,即求原志亦不可得,文献之缺,何其甚哉”。因此,屠述濂“故取原稿,加以身所亲见闻者而正续之,重为排纂,务使体例必归于一”,正式纂成乾隆《腾越州志》。而就乾隆《腾越州志》的“抵边文献”价值,光绪二十三年(1897),刑部主事寸开泰在《重刻腾越旧志序》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也。现值新定界,不无出入,吾尤愿镜方舆核掌故者,奉此为绳准,则不泥于今,自有以合乎古。率旧章而订新约,巩数千里之边防,重亿万年之图籍,庶不召今日刻志之盛意,与前人作志之苦心。
(二)“思想到边”,衍生边境地区文教护边理念
清代“大一统”理念,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悄然融入到云南边境方志的编纂过程中,成为清代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重要指导思想,彰显着清廷编纂《大清一统志》的“统一性”目标,正如乾隆皇帝对该志的御制序文所言:
圣祖仁皇帝、特合纂辑全书,以昭大一统之盛。卷帙繁重,久而未成。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重加编纂,阅今十有余载,次第告竣。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寄……书成、凡三百五十余卷。夫肇十有二州见于虞典,禹贡一篇,备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贡赋、物产,实为方志之权舆。
同时,乾隆皇帝所昭示的“大一统”思想,也随着云南边境地区方志编纂工程的推进而成功抵边,实现“大一统”理念到边的文化实践。而且,在“思想到边”的背景下,亦使得清代边境地区方志的编纂过程中,衍生出了“文教一统”“思想一统”和“领土一统”等重要稳边、固边、护边思想。
就清代云南边境方志编纂中的“一统”护边思想,相关方志序言中或多或少均有所体现。如嘉庆《广南府志》提及,“郡志创自前守茹公,至单公则纂为志略,足见苦心采辑,不鄙薄边夷之意”,主要因为“恭惟本朝定鼎以来,声教四讫,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我皇上践祚之年,添设附郭,宝宁县经画周祥,以致边徼夷疆,输诚向化”,进而体现“当文教昌明之日,幸值风云日启之时,使任其志典,如将何以风斯民而宣圣化”的文教化边思想。
又如,乾隆《开化府志》云南巡抚刘藻序言强调了该志编纂的护边价值,“诘奸慝、敉边圉,守土之责不可不殚厥心力也。《志》于边防、师旅及加恩交中事,言之尤详,大夫亦早见及此乎”。云南学者叶观国高度赞扬了编纂该志的文教护边、统边价值,“又得太守以文教治其郡,多士将益泽于诗书,于以鼓吹休明,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虽边地何难与中区匹体哉”。云南粮储等道罗源浩则强调地方志对于边徼地区的重要性及其文教价值,“夫志之在边徼,视中土为尤亟”。而作为边徼地区的开化府,由于方志的编纂,使得“然非躬逢景运,遘光华复旦之期,而有人以襄其盛,岂能使密箐幽谷一变而为声明文物之域也哉? 渐摩愈久,则风会愈新,孰谓荒陬僻壤,不可臻于一道同风之盛也”。云南迤东道廖瑛的序言也强调了《开化府志》编纂对于护边的重要价值:
夫非以边衅既开,难乎为继耶?览斯《志》者,务在保境息民,无贪奇功,无贻后患,无争赌咒河原议,睦邻禁奸,使彼为屏为藩,何尝不可以塞外属国耶? 然则,交连粤黔,惟滇之开化抗其喉,而镇静安和,悉于是《志》焉。
另如,康熙《元江府志》编纂者强调了文教治边的重要性,即“因地极边,荒山古硗瘠编额无几,而吴逆横证邀功,逐于原编之外,将彝民所奉土官各项据微定额,报入全书,至使民不胜役,地日凋残”,因之其“择彝汉子弟立诵其中,以广宣文教”,进而实现“予因思地,虽要荒远在万里,民尽彝猓沐化已深”的文教治边目的。再则,道光《普洱府志》在疆域中,强调了治边的重要性和彰显清代天子安边理念,即“普洱为滇省边陲扼要,山川土宇界连外域,而郡守所统一县三厅之中,各有土司归其管辖要。其绣壤交错,唇齿相依,判疆里之悬殊,极形势之险隘,抚兹土者能不悉心规画,以慰胜天子安边之意欤”。
再如,康熙《永昌府志》编纂者之一的罗纶强调该志的编纂,具有积极的护边价值。其认为,“若而人者,抚之则为藩篱,扰之则皆仇敌。滇彝固多,而永则尤多,三面环彝,独以东面临滇,永实诸彝要隘之区,全滇咽喉之地也。余每于簿书之暇,考旧典于残编,征往事于故老。如思氏屡勤征伐,莽氏数烦剿抚,渺尔番酋,揭竿挺刃,皆足为国家患”。因之,其强调了治边的重要性:
治之者诚能控制之、抚安之,而彝尚有不辑不廷者哉? 是守令之贤否,边疆之治乱系焉。况今麓川内列三宣,缅甸亦系羁縻,以及车里、老挝、木邦、孟艮之属,熙然宁帖,无敢稍有蠢动,是皆赖我皇上天威遐畅,故悉宴安如此。
另,康熙《永昌府志》编纂者之一李文渊,强调了方志编纂与文教治理边地永昌的关系,其曰:
我国家仁敷化洽,无远不逮,且悯兹土之数困于兵革,尤为加意抚绥之、振兴之、教养之,潜移默化,日登于衣冠文物之俗焉,则今日之永亦安能若此其盛也? 夫以永地之远若此,其风气之开又最后若此,而今日之盛遂若此,则前乎此与时乎此者,沿革必有所由焉,兴衰必有其迹焉,诏敕疏奏必有其文焉,守令官师必有其人焉。
四、结语
清代“大一统”理念为疆域一统后的产物,是清代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大一统”理念融入方志编纂实践的直接助推器,也是清代统一文化工程深入边疆的具体体现。因之,清代云南边境第一部方志的编纂过程中,云南省各级官员序言或多或少主推“大一统”理念,统一式的编纂体例透视格调,成为了主流的编纂实践形式。
清代“大一统”理念,其融入云南边境方志编纂的过程,虽然清廷中央和云南省府层面的动为主力,但云南边境地区府、州、县官员的作用,亦不可忽视。不过,就“大一统”理念入云南边境方志的形式可知,云南边境地区缺乏志剩文献,无法彰显清朝“大一统”盛况的缺憾,是云南边境地区方志编纂者一再强调的理由,亦是云南边境官员落实为清廷中央编纂《大清一统志》,为云南省府编纂《云南通志》,提供方志材料“互为证订”的客观要求。正如此,才使得清代“大一统”理念,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方志编纂过程中融入了云南边境方志,进而也使得“大一统”理念在云南边境方志编纂中的融入问题,具有明显的省级官员序言宣传推介和边境官员实践作为的契合性特征。
再则,清代云南几个边境府,大多在清之前未留下编纂方志的明确记录。直至清代,特别是康熙朝开启纂修《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省府单位,纷纷编纂省属通志,以便编纂《大清一统志》采纳所需。而云南边境地区府、州、县为了服务云南省府编纂《云南通志》之客观要求,其主政官员纷纷响应,编纂各级方志,以备采用。在此背景下,集中体现清代“大一统”理念的《大清一统志》编纂指导思想、体例和要求,顺之成为云南省编纂《云南通志》,以及云南边境府、州、县地区编纂各类方志的统一规范,成为承载清代“大一统”理念在文化工程方面的集中体现形式之一。
总之,清代“大一统”理念融入云南边境府州志编纂,不仅透视着“一统到边”的文化实践,助推了作为僻远性特征浓厚的云南边境地区,纷纷进入有志可循和有典可查的文献抵边时代,更是将“大一统”理念推及边地,成为维护国家“一统性”,特别是边境府州县主政官员和本土乡绅人士,产生“文教一统”“思想一统”和“领土一统”重要稳边、固边、护边思想的自觉成功实践。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网络
排版: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