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2日,南京秦淮河·夫子庙景区
跨进那扇门,便像是跨进了一条时间的河流里去了。门是寻常的,并不如何轩昂,但两旁的一副楹联,却先就将人镇了一镇:“归燕几番来作客;鸣筝何处伴随云”。字是行草,带着些飘然的姿态,仿佛那燕影与筝声,都化在了墨痕里,要随风散入巷口的斜阳中去。我立在那里,心里便幽幽地响起了一千多年前刘禹锡那苍凉的调子: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诗,是刻在门内的影壁上的,用了篆、魏碑、隶、行草四种书体,像四重不同的嗓音,在唱着同一首古老的歌谣。篆书是古拙的叹息,魏碑是嶙峋的风骨,隶书是沉静的叙述,行草便是那飞入百姓家的燕子,带着一抹潇洒而又怅然的尾音。还未见着馆内的珍藏,单是这进门的一瞥,六朝的风烟,便已扑面而来了。
燕影拂花
院子不大,却曲折有致。另一副楹联挂在院门,写的是:“因随燕影追唐韵;便拂花光溯晋风”。这联写得实在是好,轻巧而又深沉。“燕影”是刘禹锡诗里来的,是历史的信使;“花光”是眼前秦淮河畔的,是现实的明媚。只这一“追”一“溯”,便将唐人怀古的诗韵与晋人风流的气度,轻轻地挽在了一起,像一只无形的手,为我推开了那扇通往魏晋的、虚掩着的门。
GO TRAVEL
往里走,便是“来燕堂”。这名字起得真好。堂前的檐柱上,又是一联:
水绕城柳萦堤摇曳六朝烟雨旧;
人名世文述志承传一脉法仪新。
我默默地念着,上联是景,是梦。仿佛能看见那秦淮河的水,绕着建康城,绿柳拂着长堤,在迷蒙的烟雨里,摇曳着一千六百年前的旧影。那“旧”字里,有王导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的赫赫权势,也有谢安在淝水之战前,与人围棋赌墅,谈笑间令强虏灰飞烟灭的从容气度。而下联,则是魂,是根。“法仪”二字,并非冷冰冰的礼法教条,而是王、谢这般世家大族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气韵——是治国的智慧,是艺术的创造,是人格的独立与风雅。这“新”字,便点明了这纪念馆存在的意义:那旧日的燕子虽已飞入寻常之家,但那风骨与文脉,却如地下的潜流,至今仍在我们的血脉里,汩汩地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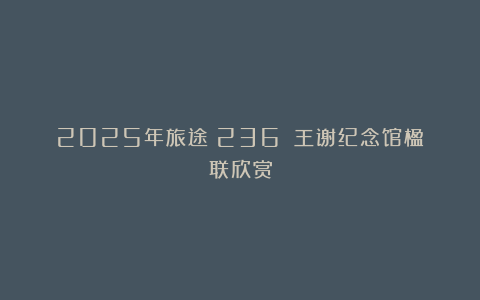
史家何必嗤六朝
堂中端坐着王羲之的塑像,神情萧散冲和,目光却似乎穿透了时空。他左右的楹联,口气更是斩钉截铁:
文物自堪诧千古;
史家何必嗤六朝。
这像是一声骄傲的宣告,又是一句不平的反诘。是啊,何须那些抱着“正统”史观的先生们来嗤笑六朝的偏安与短祚呢?单是王右军那一纸《兰亭集序》,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字迹,那“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自信,便足以让千载之后的人们,为之惊叹屏息了。六朝的政治或许混乱,但它的文化,它的艺术,那时世人对于精神自由的追寻与对于美的创造,却达到了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这塑像,这楹联,静静地立在这里,便是一种最有力的文化自信。
我的脚步,最后停在了那方“曲水流觞”的模型前。
一条蜿蜒的石渠,仿佛还有清澈的水在流动。我似乎看见,永和九年的那个三月三,在会稽的兰亭,以王羲之、谢安为首的四十二位名士,列坐水旁,羽觞随波逐流,停在谁的面前,谁便要饮酒赋诗。那是何等的风雅,何等的快意!政治的风云在远方翻卷,而他们却在此地,与山水融为一体,将生命沉浸在艺术与哲思的欢愉里。“羽觞随波泛”,王逸少的诗句轻轻滑过心头,眼前这微缩的景致,霎时间便充满了流水声、吟诵声与朗朗的笑语。
馆内还有淝水之战的半景画,有六朝的石刻与砖画,有古朴的罗汉床与雅致的文人书房。这一切,都像一块块拼图,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东晋。它不只是一个朝代的代号,它是一种气息,一种风度,一种被后世文人不断追想、摹仿,却再也无法全然复制的文化典范。
从纪念馆里出来,夕阳正真真切切地斜挂在乌衣巷口,给青瓦粉墙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巷子里游人如织,笑语喧阗,确是“寻常百姓家”的热闹气象了。我回头又望了一眼那扇门,心里却不再有初来时那种物是人非的苍凉。那“堂前燕”确是飞走了,但它在飞过一千多年的时间长河时,却将一些东西遗落在了这里——是那些刻在木头上的楹联,是那些写在书卷里的风骨,是那种对于美与自由永不磨灭的向往。它们不曾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这人烟阜盛之地,静静地,等着下一个有心人的来访。
GO TRAVEL
自由,是选择的无限可能
在这里
自由就是拥有选择
如何度过每一刻的权利
#版权说明#
图文|张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