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
XIUMI HOTEL
新月与蔷薇
—— 伊朗文明的千年经纬 ——
突然,在墙上看到这句话:“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令我大吃一惊,谁啊,谁啊?说出这样的话!
哲拉鲁丁·穆罕默德·鲁米(1207-1273)波斯苏菲派诗人、哲学家,代表作《玛斯纳维》被尊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
01
四行诗选
亚当子孙皆兄弟
译自《蔷薇园》
萨迪
亚当子孙皆兄弟
兄弟犹如手足
造物之初本一体
一肢罹病染全身
为人不恤他人苦
不配世上枉称人
博物馆里布置成这样的门户,异域风格抢眼得很。
XIUM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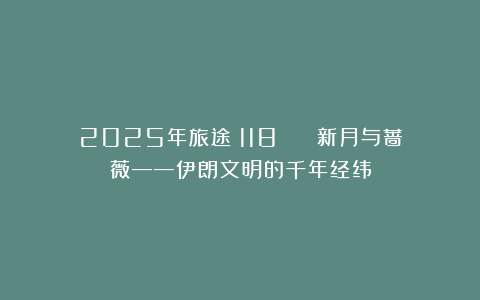
我仿佛能看见那些头缠白巾、身着长袍的达尔维什们,在沙漠的星空下,用萨迪的诗句抚慰旅人的灵魂。“亚当子孙皆兄弟”——这穿越七个世纪的声音,此刻在南京博物院的“新月与蔷薇”展厅里回响,与彩釉瓷砖上蔓生的藤纹一同生长,直抵云霄。
02
贴金钢盔,蔷薇园
设拉子的《蔷薇园》早已凋谢在历史的尘埃里,但萨迪的诗句却如不死鸟,在每一代波斯人的血脉中重生。我凝视着南京博物院里那幅细密画,波提乏王端坐中央,金质城垛纹饰将他环绕,侍从们华美的衣袍上,每一道褶皱都藏着《列王纪》的传奇。最奇妙的是背景里若隐若现的狩猎场景——猛兽追逐着逃命的羚羊,星空与几何图案交织,仿佛整个宇宙的秩序都浓缩在这方寸之间。这是波斯人独有的智慧:在绝对的规整中容纳最狂野的想象,就像鲁米的诗句:“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
蔷薇园
03
细密画前随想
在内沙布尔的陶器前,我久久驻足。那些九世纪的陶碗上,库法体的阿拉伯文蜿蜒如藤,既是经文,又是图案。一个红色的陶盘上,白色的釉料书写着“仁慈的主”,每个字母的末端都化作一片棕榈叶。我忽然明白了:在这里,神谕从不以训诫的面目出现,它化作装饰,化作韵律,化作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就连道德教化,也要披上艺术的外衣才肯降临人间。这让我想起萨迪的另一句话:“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枉称人。”原来人道主义的关怀,早在十三世纪就已镶嵌在波斯诗歌的韵律里,烧制在日常器皿的纹饰中。
在帖木儿时期的细密画前,我发现了另一种震撼。哈迪·塔吉维迪笔下的巴赫拉姆国王宫廷,乐师弹奏着塔尔琴,侍女手捧石榴,园丁在左侧的庭院里修剪玫瑰。门楣上刻着“尊贵的苏丹”,而扉页上却是哈菲兹的诗句:“风景的露台,是我的眼睛,是你的领地。”这是何等的自信——帝王将相与诗人的抒情诗可以共享同一个空间,权力必须向美低头。
我忽然想起欧玛尔·海亚姆那充满怀疑精神的四行诗:“我们来去匆匆的世界如同圆轮/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位数学家诗人,在十二世纪就用诗歌探讨宇宙的虚无,而他的诗句,竟能穿越时空,与萨迪的人道主义、鲁米的神秘主义、哈菲兹的享乐主义并置在同一文化谱系中,互不否定,各自生辉。
亚当子孙 皆兄弟
我仿佛站在三十三孔桥上看夕阳。桥洞下的水影荡漾,仿佛倒映着千年的文明层叠:塞尔柱的砖艺、伊利汗的穹顶、萨法维的彩釉……所有这些王朝都如海亚姆所说的圆轮,滚滚向前,但艺术却如河床下的宝石,越磨越亮。
蒙古铁骑曾经踏平城池,帖木儿的战刀染过鲜血,但最终留在历史记忆里的,是完者都汗陵墓上那八角形的穹顶,是撒马尔罕清真寺里将砖艺推向极致的彩釉。残暴的帝王往往以赞助艺术来赎罪,而时间这个最公正的法官,总是选择留下美,遗忘血腥。
当我要离开伊朗文明展馆时,再回首,张鸿年的译笔依然鲜活:“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我忽然明白,让我惊叹的不仅是那些看得见的艺术,更是这种贯穿千年、将所有人联结在一起的精神。就像细密画中那些金色的藤蔓,看似装饰,实则是骨架——是美,让破碎的世界依然完整。
END
微信号 : gszyb1990
【版权说明】
图文 | 张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