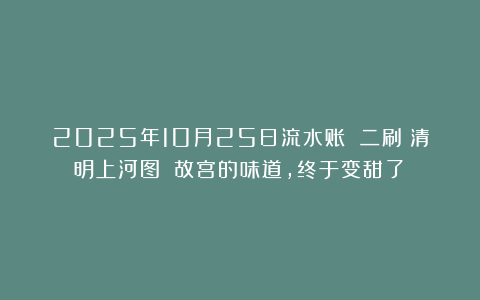|
今年的年票终于派上了用场,但约展览还是需要定闹钟,拼网速,讲人品。
我们几个人组的小队伍,还真是有意思,每次都有一个人指定能进去小程序里,所以我们最后总能约到一起。
你别问,为什么11点了还在刷票,其实我们已经约上了周三的票,但是kelly约在了下午,我们都在上午,于是她守在11点没睡,偏偏我那天也没睡,在刷剧呢,于是就都赶上了。
去之前,战战兢兢,担心像那天一样,要天黑回来,这次可不能天黑就回来,因为娃要上课,必须要有人送,晚上还有双安商场夜校的启动仪式,这都是不能错过的。
因此那天我连家都没回,送完樱桃,把车停在地铁上,早饭也没吃,就坐上了10号线,8点33就出了金鱼胡同,快快地往东华门走去,又急匆匆走到午门,第一份欣喜来了,人非常少,8个排队口,只有三四个口有人,我且没有看到大量旅游团。
于是我也顾不上等另外两个小伙伴,就先跑进去取午门特展的号,我拿到的已经10-11点的号段。
景仁宫是一个关于文物捐赠的小展,类似于故宫的答谢仪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以人为要素的捐赠的脉络。
看到了郑振铎和沈从文的捐赠,还是小小激动了一下。
有一秒我们都觉得,如果我拥有其中任何一项宝贝,我大概都想留给自己不停把玩和欣赏,不舍得捐出去。
不过下一秒也明白,首先,我们不舍得是因为我们还不曾拥有。
其次,最好的爱是保全。
这些曾经的拥有者们,肯定知道这些宝贝最好的归处应该是哪里。
我想,真的有一些东西,只能属于全人类。
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太小了,难以承载其重。
从景仁宫出来,我们感觉肚子饿了,就去了不远处的甜品店,点了咖啡,鸡腿,把午饭解决。
等到午门排队时,时间是11点半,过了我们的时段,不过却意外地直接找工作人员,不排队就进去了。
没搞明白这个逻辑,大概是因为没办法把我们这些过号的小伙伴,压到下一个时段。
所以这次的体验不要太好。
上了午门之后,重磅的2展厅是按照色号来排队的,刚上去,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发一张带颜色的小纸条,然后你就可以开心地去1展厅和3展厅闲逛了,因为每个展厅都会有工作人员喊号。
比如,我拿完票,刚进去3展厅看了几个物件,就听到工作人员喊“红色排队啦”
每一个色号50个人,我当时拿的43号,大概排了20多分钟,中间我还掏出了刚买的彩虹凳,不过很快就收起来,进去了。
《清明上河图》这次足足看了5分多钟,应该是这次的平均值,每个人看得都特别认真,因为细节太多了。
这次看清明上河图,因为有上次的打底,回来也看了一些电子图,有了大概的结构概念,也能看到一些细节,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
其实这张图不仅仅是构图和绘画的造诣,我看着那些一寸寸展开,一寸寸进入画面的芸芸众生,他们有的负重,有的清闲,有的慵懒,有的卖力,有时拥挤,有时荒阔。
我无论站在西山鬼笑石,还是站在景山公园万春亭,我都看不清北京城里的一切。
沈周《富春山居图》的“不忍”
与那个雕塑一般不动的观众
《富春山居图》,我之前没有见过,沈周的这幅背临之作,也实在是震撼。
想想我学书法也有几年,却至今也无法背临一幅完整的字帖,这当中还不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更是对自己的确定感,始终做不到“对自己的绝对信任。”也是因为你越懂得一幅字的了不起,你看到的细节越多,你越是不敢造次的感觉。
沈周为什么会背临这幅画,因为他原本收藏的原画,请一个朋友写题跋,却被朋友的儿子据为己有,而且后来还拿去售卖,沈周没钱买回,但又实在念念不忘,便自己动手画了一幅。
“”馀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於思耳!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成化丁未中秋日,长洲沈周识。
景泰六年(1455年),沈周担任粮长一职,当时天灾人祸不断,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百姓大多无力缴纳田赋。沈周不忍强征,而知县却要求沈周赔偿田赋差额。沈周因此家中积蓄全无,连妻子的首饰都典当出去。然而还差500石,沈周于是入狱。后来,同乡郭琮帮他补了这500石,沈周才被释放。
观展时,跟我们相隔10个人的阿姨,我被她的心理素质震撼了,她愣是在五牛图里赵孟頫一段文字里看了10分钟,在清明上河图的地方,工作人员几张嘴巴凑在她耳边,喊她往前走,她就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也不回复,也不言语,我感觉这真的像冷暴力,我当时在旁边都有一种冲动,要上去拉她一把,给她清场出去。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有素质的,估计已经快被憋出内伤来了。
工作人员当中的一位老大姐,我路过的时候冲她笑了笑,她还是愁眉不展。
如果我们千山万水来看这些作品,难道不是也应该看看这些作者本人?哪怕被他们熏染一星半点做人的选择吗?
终究,艺术作品要走向人们的内心,可能还不仅仅需要一个展厅,一次大展。
人对于时间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尽管2展厅还是慢慢地在推进,可这次却并不着急,整个展厅也没有嘈杂和慌乱。
更重要的是,其实生活中你真的很难重复做一件事,重复走一条路,我们都还是喜欢变化和迭代。
买了个纪念文创包,价格100,小东西挺多,金边笔记本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