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总爱说,一年到头没啥新鲜事,大概能记住的,也就是谁家添了新丁、哪户口角闹得大些。可2014年那场子午饭后的闲散,不知怎的,竟从田间的轻松扯闲,演到后来让全村人心里一阵阵发毛。人家说,遇上野兔算运气,可那一下午,沁阳市这个偏僻小村落,把“意外”两个字给撞了个正着。
那天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撒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头一边嚼着烟锅,一边聊着自家种的菜。这时候,有人半开玩笑地嚷了一句:“不如咱们去弄两只野兔,今儿晚上给大伙加个菜!”大伙听得兴起,回屋拿了陷阱竹竿,有的拎把锈镰,有的就提根柴棍,零零碎碎,热热闹闹沿着小路钻进山。
刚进山林,还只当是赶场游戏,一帮头发花白的人,蹑手蹑脚地猫着腰,东张西望。说起来,山里的野物也精,好动静一响就迷了踪。但那会儿是天公作美,一只没长大的兔崽子,被惊得嗖嗖跑,几个人一边踩着落叶,一边忍不住乐得咧嘴,想着回家怎么分这顿野味。
可你说命运这事吧,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正追得高兴时,走在前头的王老汉,突然一脚踩进石缝,身子一晃,差点没栽倒。可没等别人扶他起来,他低头想拔脚时,脸色就变了。
那一瞬,空气像凝住了。旁边的李婆赶过来一看,先是瞪大了眼,再一口气倒吸到嗓子眼——那石缝里竟鼓着几片灰白的布料,还有几块惨白骨头。可最叫人胆寒的,是那骨头姿势跟人静止在某个动作里似的——一只手就那样横在前面,勾着,像还在死死扣着扳机。鬼知道这人究竟是怎么死的,谁又会以这种诡异的姿态被埋到几十年后?
几个老头老太当场腿都软了,山林里的鸟叫也像被吓跑了。没人敢多看一眼,匆匆收拾下山。一路上七嘴八舌,有人悄声念叨着:是不是日本兵?是不是当年跑山的土匪?也有人干脆不理会,说天意莫测。这么大动静,捂是捂不住的,没多久,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大家合计着报警。
警察一接电话,哪里还敢怠慢?派出所把装备一收拾,几名警官就沿着山路颠了老半天,总算到了事发地。村民也都等在山脚,有的看热闹,有的悄悄搓着手,说是怕见不干净的物事。
警察带着点紧张、带着点好奇。有人绕着石缝小心查看,确认四周没眼下的危险,才让法医和技术员去勘查。说来也怪,那尸骨不仅保存得还算完整,连老旧的军帽角扣都还搭着。村里有的是从“抗战”边角日子熬过来的老人,瞅两眼却又不敢认:这究竟是咱自己人,还是天南地北的流落英雄?
警官们考虑再三,没敢轻易动。毕竟这不是寻常冲突,不清不楚乱动一通,谁也担不起那个责。于是,专业队一拨接一拨上山,有法医忙着现场测量,有考古学家蹲在泥地里翻捡弹壳,也有人组队到档案馆查那几年失踪的士兵名字。
巧在这点破小山村,风一吹就能传半里地,那天晚上就有人听说,除了警察,还有市里两个领导专程来了。为首那位,叫李建国,说是市里的老区促进会副秘书长。平日里很少露面,可这回,是头一回来得这么急。听说消息的村干部还打趣:“建国同志眼睛里头全是事儿,估计是来了真英雄。”
李建国赶到,第一件事不是抢抓新闻,也不是抹几滴眼泪,而是盯着村民和记者说:谁也别靠近,多带条警戒带护着!有年轻民警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可他翻脸道:要是破坏了现场,这人,估计连名字都找不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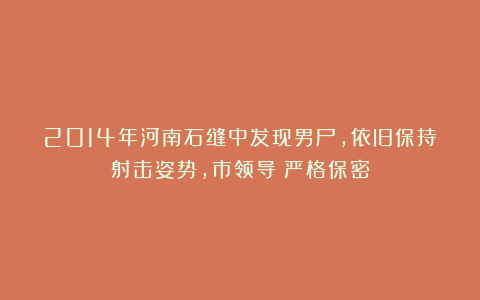
其实,保护的不光是死人那点骨头,还是活着这帮人回忆里的一口气。常平阻击战的老故事,老一辈听得多了,说过去多惨烈,可真没哪个后人摸到过先祖的遗骨。警戒线拉起来,有老师下课带着娃娃偷偷探头,也有老人拄着拐杖,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想找点熟悉的乡愁。
现场的法医折腾了一夜,X光一照,没见大伤小孔,弹片都嵌在泥里。看得出来,这是战时冻死或殉职——不是刑事案。考古组翻出几枚老式步枪弹头,还捡到一片洗得发亮却没有号码的军号牌。荒山野岭,能留下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种解释。
接下来,就是那一套繁琐却温情的对照——地方志、老战士名单、战场日记;还有村里老太太回忆谁家的二儿子一夜未归,谁的哥哥在1940几年丢了消息。档案筛来筛去,越看越心酸——抗战时跑出来的这点骨头,十有八九无人认领。可这一回不知为什么,调查竟跟一名失踪牺牲士兵搭上了线。
李建国盯着档案看了又看,夜里两三点还在村干部小楼下,点着灯和几位家属喝糖水。偶尔有老太太红了眼眶,说也许这回咱再不用给先人招魂了。
确认身份那天,天阴着,队伍走到山头,李建国递了三支黄菊。不讲究礼节,就是实在。有村干部劝他歇一歇,他低头一笑:“人死不能复生,可英雄不能没人认。”
这不是句大话。有人还真记得,常平县前几年闹过一次事,三百多座烈士坟被人扒了,现场惨不忍睹。那事传出去,气得当地老人连饭都不想吃,干脆天天守着坟地。也许李建国心里,比谁都拧巴——他怕不仅“骨头”没人认,将来连记忆都被风刮没了。
后续就顺理成章:报告一递,纪念馆的批文也下来了。设计的人有点意思,说建筑要半开放,要让所有来的人既能看见展柜,又得能呼吸到山风。陵园则一律种着百合和松柏,说是让烈士“睡得安稳”。墓碑上一块块,有名字的,铭字精致,无名的,就一块素碑,刻着“无名忠魂”。
孩子们从那以后也常去实地上课,不光拍照,老师还让他们用手摸摸纪念石,说:“看看,这就是历史,不是只写进课本的那种。”外地来的大学生更有个性,住帐篷拍纪录片,不信邪地连夜守桥头,说想拍到“星空下的英雄村”。
说到这儿,我们忍不住要想——这些埋在泥土深处的故事,最后到底归谁所有?这一通风风火火地找回名字、修个墓、置一座馆,当然有仪式感。但真正让人难舍的,不就是几年一遇,山林里那些说不清的、带着烟火气的发现吗?
谁晓得下一回挖出野物的时候,是不是又有某段历史在等待“被撞见”?或者说,其实每条埋藏在泥里的命运——本就值得我们再三回头张望。
只是,终于有人能去祭拜、有人能开口叫一声“回家”。剩下的空白,谁来添?谁又在那静静的山岭之下,等着下一个春天,把风里遗落的名字,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