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古代历史上,真正能以诗名留世的女性并不多。中国有李清照、鱼玄机等,她们的诗作至今仍被传诵;但与众多男性诗人相比,女性诗人始终是寥寥数人。在欧洲亦然,俄罗斯的诗坛更是由普希金、莱蒙托夫、布洛克等男性主导。
然而,到了20世纪,这个历经了2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俄罗斯却出现了一位非凡的女诗人——她的诗如火般炽烈,像铁般坚韧,她用文字对抗命运,用灵魂拥抱苦难。
她才华横溢,却脾气古怪,她不喜欢“正人君子”,却喜欢怪人圈子,她的朋友里有狂放不羁的诗人,也有内心阴郁的哲学家,她的爱情来得猛烈,去得无声。她就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那么,这个才华与悲剧并存的女人,为何偏偏只信任那些“不合群”的灵魂?
茨维塔耶娃出生于1892年的莫斯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后来创建了著名的“亚历山大三世艺术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母亲是一位有名的钢琴家,追求完美、情感强烈。母亲希望她成为音乐家,而她却偏偏迷上诗歌——她说:“钢琴是别人的语言,诗才是我的声音。”
她七岁开始写诗,十五岁出版诗集《黄昏的专辑》,以纯净的语言和深刻的情感让俄国诗坛惊讶。她写的爱情诗不是柔情蜜意,而是带着火焰的冲突与孤独。评论家称她“像火焰一样写诗,像暴风一样生活”。
茨维塔耶娃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人。她曾在信中直言:“我厌倦那些自以为高尚的’正人君子’,他们的灵魂没有裂缝,没有激情。”她更愿意与那些“不完美”的人相处——他们可能贫穷、偏执、孤僻,却都在生活的边缘燃烧。她说:“怪人是自由的,他们不向现实低头。”
这种性格,使她在诗人圈中既受人敬仰,也常被误解。她会在聚会上与人辩论文学,毫不留情地驳斥对方的观点;也会在孤独时一个人坐在窗前写诗,写到手指冰冷。朋友形容她“像刀锋一样敏锐,又像火焰一样温热”。
1912年,她嫁给了谢尔盖·埃夫龙,一个出身贵族的青年。他温和、沉静,与她炽烈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婚后,他们有过短暂的甜蜜,但很快被时代打碎。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谢尔盖参加白军作战,茨维塔耶娃则带着两个孩子留在莫斯科。
那时的生活极其艰难。街上没有面包,房间里没有取暖的煤。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她把家里的衣物、书籍都拿去换粮食。她的日记中写着:“我用诗换面包,用灵魂换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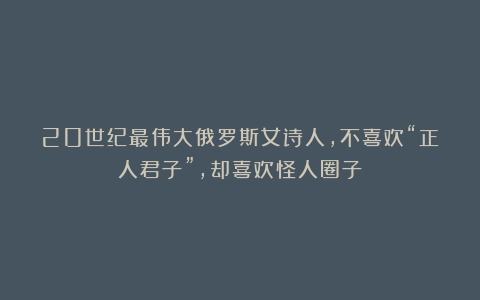
可即便如此,饥饿仍夺走了她的小女儿伊琳娜。三岁的孩子死在孤儿院,她得知消息后整整一天没有出声,只在夜里默默把那件小衣服叠好放进箱子。
1919年之后,她开始写那些著名的“流亡诗篇”,语言尖锐、节奏紧促。她在诗中写道:“我不属于胜利者,也不属于失败者,我只属于文字。”这种孤傲,使她在俄国文坛显得格外孤立。
1922年,她辗转逃到布拉格,与丈夫团聚。那是她生命中最平静的几年。她在布拉格结识了许多流亡作家——有人崇尚自由,有人醉心酒精,有人整日争论政治。茨维塔耶娃喜欢这种混乱的氛围,她说:“我喜欢疯子的圈子,因为他们的眼睛还亮着。”
她的朋友们后来回忆,那时的她总是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面前一杯冷茶,笔下却飞快地写。有人说她像一座火山,安静时让人不敢靠近,爆发时又震撼人心。
然而,流亡生活的贫困仍让她疲惫。1930年代初,她随丈夫迁到巴黎。巴黎是诗人的城市,却没有给她带来安宁。那时她的丈夫开始被苏联情报机关吸收,从事秘密活动;她的女儿阿丽亚逐渐卷入政治旋涡,而她自己则继续生活在文学与现实的缝隙中。
她在信中写道:“巴黎的灯光那么亮,却照不进我的心。”她不合群,不去上流社交场合,也拒绝讨好出版商。她仍然与那些贫穷、落魄的诗人做朋友——那群被社会视为“怪人”的人。在他们的聚会上,她朗诵诗,声音清亮坚定:“世界在崩塌,而我仍要写诗。”
1939年,她听从丈夫的劝说,带着女儿回到苏联。她以为那是重回祖国的归宿,却没想到那是一条不归路。苏联正处在肃反运动的高峰期,外来者被怀疑是间谍。丈夫被捕,女儿也被关押,她被迫流落到鞑靼的小镇叶拉布加。
那个冬天,她的生活陷入彻底的绝望。她几乎没有食物,也没有朋友。她到处求职,希望能做翻译或抄写员,却屡遭拒绝。她写信给朋友:“我连呼吸都要小心,怕浪费空气。”
1941年8月31日,她在租住的小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49岁。
她的死,没有惊动多少人。战争正在燃烧,没人有余力去悼念一个诗人。直到多年后,她的诗被重新发现,人们才意识到,这个被时代遗忘的女人,曾用全部生命书写了自由与孤独的意义。
帕斯捷尔纳克在得知她的消息后写道:“她不是死于饥饿,也不是死于绝望,她死于一个不懂诗的时代。”这句话,成了后人对她命运最深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