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柚子 素材/张向阳
声明:作者柚子在头条用第一人称写故事,非纪实,情节虚构处理,请理性阅读!
01
我叫张向阳,今年整五十。这会儿坐在县城中学的教师宿舍里,窗台上还摆着二舅打的樟木箱。摸着箱盖上那道陈年刻痕,四十二年前的往事哗啦啦往外冒。
1983年霜降那天,我娘赵秀兰咽了气。她得的是急性肝腹水,从发病到走才七天。那年我八岁,爹张永福在县农机站当修理工,一个月回不来两趟。
记得那天日头刚偏西,娘攥着我的手往窗外指。院里那棵老槐树扑簌簌掉黄叶子,有几片飘进窗棂落在她青灰的脸上。后来大舅总念叨:”你娘是怕树叶掉光了,没人给你絮棉袄。”
爹第七天就娶了后娘。那天晌午大舅赵建国开着拖拉机冲进院,车斗里化肥袋子还鼓着。他把我从灶台边拎起来,军大衣一裹就往外走。新后娘追到院门口骂街:”养不熟的白眼狼!”
拖拉机突突往北开,我缩在大舅胳肢窝里,闻着他领口柴油味混着汗酸味。天黑透到了二十里外的大舅家,土炕上的芦苇席子扎得我脸生疼。后半夜被尿憋醒,看见大舅蹲院里磨柴刀,月光照得刀刃雪亮。
02
二舅是第二天晌午来的。他骑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车把上挂着半袋富强粉。三舅傍晚才到,呢子大衣上沾着火车座的煤灰,公文包鼓鼓囊囊的。
“让娃跟我过。”大舅蹲在门槛上卷烟,火星子溅到补丁摞补丁的裤腿上,”我天天出车,晌午让王婶给送饭。”
二舅一巴掌拍在掉漆的炕桌上:”你当养狗呢?我家媳妇刚生完娃,正好可以一起养。”他棉袄袖口还沾着刨花,那是给公社小学打新课桌时沾的。
三舅从搪瓷缸里挑出片茶叶嚼着,忽然掏出手绢给我擦鼻涕:”省城子弟小学要考试,明天就带他去报名。”他手腕上戴的上海牌手表反着光,照得我眯起眼。
三个舅舅的唾沫星子在煤油灯底下乱飞。大舅突然撕了记账本,黄草纸裁成三条:”抓阄,抓着啥算啥。”二舅抢着抓了个纸团,就着灯影念出声:”二!”
二十年后上坟我才知道,那三个纸团写的全是”二”。
03
最终我跟了二舅。二舅妈李桂枝刚生完表弟,见我进门就把奶娃子塞给婆婆,连夜用蓝布头给我拼了床被褥。头天夜里我尿了炕,臊得躲在柴火垛后头不敢见人。
“多大点事!”二舅从木料堆里翻出几块松木板,”给你打张带护栏的床,保准滚不下去。”他咬着竹尺量尺寸,木屑落在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
开春后二舅在院里支起凉棚,给公社修理课桌椅。我趴在小马扎上写作业,总被他吆喝去捡钉子:”仔细着点,钉子能换盐哩!”他裤兜里总揣着炒黄豆,我每捡十颗钉子就给一粒。
最盼着三舅的包裹。每月初八邮差在门口摇铃铛,牛皮纸包着的《儿童时代》里总夹着大白兔奶糖。有回还寄来个铁皮铅笔盒,盖子上天安门城楼的金漆晃人眼。
04
大舅每月初一来送粮。五十斤玉米面用化肥袋子装着,底下总埋着惊喜。有时是供销社处理的碎饼干,有时是沾着油星的报纸包——打开是两片卤猪肝。
那年腊月特别冷,二舅手上的冻疮裂得渗血。大舅把军大衣往炕上一扔:”改改给娃穿。”二舅连夜拆了重缝,我穿着能拖到脚背的棉袄上学,同学都笑我是唱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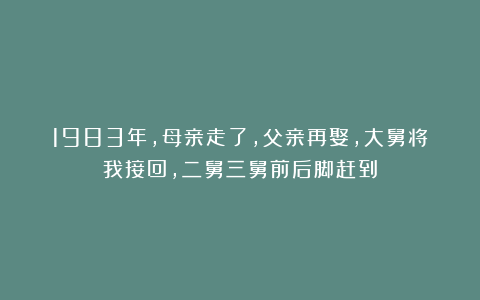
直到在县城上初中,我才发现大衣内衬缝着暗兜。里面塞着张卷烟纸,上头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建国给娃买鞋钱——叁元整”。那字迹被汗渍晕开了,像朵墨色梅花。
05
初二那年,三舅突然从省城回来。他翻开我的作业本,眼镜片直反光:”这应用题解法不对。”说着掏出英雄钢笔,在草稿纸上画满我看不懂的图形。
那天晚上,三舅和二舅蹲在门槛上抽烟。”娃得去县中。”三舅的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我联系了刘校长,能住教师宿舍。”二舅闷头抽完三根烟,最后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摔:”中!”
临走那天下着雨,大舅开着拖拉机来送行李。二舅妈往我书包里塞了十个煮鸡蛋,用红毛线织的网兜装着。三舅的新皮鞋踩在泥地里,咯吱咯吱响。
06
高考放榜那天,三个舅舅挤在镇邮局等电话。大舅的解放鞋沾满泥,二舅的工作服还别着木工凿,三舅的白衬衫被汗浸透。当听说我考上师范大学时,二舅突然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三舅掏出手绢擦眼镜:”好,好,当老师好。”大舅转身往外走,说是去供销社买挂鞭。后来二舅妈告诉我,大舅在供销社门口蹲着抽了半包烟,烟盒上写的运输单都让他攥成了纸团。
07
二舅肺癌住院时,我从学校赶回来。他枕边放着个铁皮饼干盒,里头装满泛黄的纸片:有85年的化肥袋发货单,90年代邮局汇款存根,还有我历年成绩单的复印件。
“当年你三舅出主意,说纸团都写二…”二舅的氧气面罩蒙着白雾,”你大舅连夜改运输路线,就为每月初八能赶回来对账…”监护仪的滴滴声里,他攥着我的手渐渐松了。
08
去年清明给娘扫墓,我带着三个搪瓷缸子摆在坟前。大舅前年走了,二舅肺癌去了有十年,三舅老年痴呆住进疗养院。我给每个缸子倒上散装老白干,酒气混着烧纸的烟往天上飘。
“娘,您给评评理。”我掏出个铁皮盒,里头装着发脆的账本纸,”大舅85年运化肥的运费单,二舅给学校修桌椅的工分本,三舅汇款的邮局存根,他们都烧给您了对不?”
风把纸灰卷成旋儿,像三个舅舅又蹲在茅房后头对账。那年抓阄的真相,是二舅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破的。
09
如今我在镇中学教数学,教室里还摆着二舅打的课桌椅。去年教师节有个女生送我盒麦乳精,说是她爹让捎的。那汉子挠着头笑:”张老师,我爹是赵建国运输队的老王头。”
前些天去省城看三舅,他连亲儿子都不认得了,却摸出个铁皮文具盒往我手里塞。护工说老头成天攥着这盒子,谁来抢就跟谁急。
窗外的老槐树又黄了叶子,我把三个搪瓷缸并排摆在讲台上。粉笔灰纷纷扬扬落在缸口,恍惚间看见三个身影蹲在房檐下:
大舅正用改锥敲着生锈的扳手,二舅拿砂纸打磨课桌毛刺,三舅把教科书包上崭新的挂历纸。他们额头的汗珠在秋阳下亮晶晶的,像当年连夜拆改军大衣时落的棉絮。
“舅,今儿讲勾股定理。”我敲敲黑板,”当年三舅说的,数学是世上最准的秤…”
教室里沙沙的笔记声漫过山梁,我知道三十八年前那三个纸团,终究是称出了比山还重的情分。
10
三个搪瓷缸如今摆在我家五斗柜上,分别印着”先进生产者””模范教师”和”优秀党员”。这些他们生前最看重的奖杯,被拿来当了半辈子茶缸。缸身上的珐琅彩早磨花了,却照得见人间最干净的念想。
去年修缮老宅时,在门框后发现三排身高刻痕。最上面用铅笔写着”阳阳八岁”,中间是”阳阳考取县中”,最底下那道新鲜刻痕齐我耳尖,标注日期是”2023清明”。
我知道,那是三个舅舅弯着腰,在时光里继续为我丈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