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象征着中美关系从长期对峙走向接触与沟通,标志两国外交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彼时的北京会谈紧凑而审慎,双方在诸多原则问题上互探底线、寻找交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周恩来总理讨论建交相关议题时,尼克松还提出了一个颇为具体的人道关切:希望中方释放两名被拘押的美国人,一名叫约翰·唐奈(又译唐奈),另一名是理查德·费克图。
为此,尼克松放下身段,先正面承认两人在华确有违法行为,态度上强调尊重中国法律。他随即转入情感层面的劝说:唐奈有位年事已高的母亲,七十有六,期盼在有生之年再见儿子一面;费克图身患疾病,家属焦灼挂念,希望他能够尽早回到家庭。言辞间既有政治考量,也包含人道诉求,力图为两人争取宽大处理。
周恩来在认真听取美方陈述后,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时也为体现中美改善关系的诚意,原则上同意酌情从轻处理,并指示相关部门依法审查、区别对待。随后两人依据罪行轻重先后获释。尼克松获知消息后十分振奋,连声称赞周恩来是“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这也成为会谈气氛缓和的一个注脚。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又犯下何种罪行,以至于要由美国总统亲自出面交涉?故事要回溯到二十年前的一起大案。
新中国初建之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破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不愿看到新政权的稳步发展。彼时我国反间保密体系尚在起步阶段,台湾与美国方面多次派遣特务渗透内陆,肃反斗争频仍。1952年,公安机关在东北地区侦破一起重大的美国间谍案件,成为当年保卫战线的关键战果之一。
案件起因是中央公安部电令东北方面:在长白山一带捕捉到来源不明的电波,疑似对外发报。地方随即展开排查,评估该地是否存在移动电台与特务据点。长白山地广林深、气候严酷,积雪封山的环境为隐蔽活动提供了天然屏障。再加上美方小型电台技术先进,侦测难度陡增。然若不能尽快查明并拔除该秘密电台,我国在抗美援朝的关键阶段就可能遭遇军事与情报上的严重风险。
随着侦查深入,情报逐步汇拢:有人两度听见夜半飞机轰鸣;猎人于密林中发现印有外文的罐头盒;还有五名身穿志愿军军装的男子搜购山民物资。这些线索互相印证,显示敌特已潜入该区,而且试图伪装成志愿军行动。在当时,能以空投方式将特务投放至此者,除与志愿军交战的美军外别无他选,敌情基本明朗。
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东北军区公安部负责人谭友林部署反特行动:以发现异物区域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寻,在通往山地的要道设卡盘查,形成内紧外堵的围剿态势。一方面向敌暗示“行动已暴露”,迫使其消耗与失误;另一方面利用其物资有限的弱点,切断补给、困而歼之。策略很快见效,一名身着志愿军军装、配戴手枪的男子前往当地公安机关自首,自称李军英,代号5774,隶属美国驻日情报机关。
经详审,案情轮廓逐渐清晰:李军英与另一支五人小队在“文世杰”(化名)的带领下空投入境,另有同类小队在相邻区域潜伏。他们自架电台,直接与驻日美方间谍机关联络,任务是于东北构建“游击基地”,长期刺探军政情报,并在必要时破坏机场等军事设施。值得强调的是,这批人员多为台湾方面的中国人。鉴于美国人易被辨识,CIA倾向吸收原国民党系统人员充当眼线与破坏力量。
按计划,特务在完成情报搜集后需择路赴日复命,预设了三条撤离通道:其一以“空取器”对接运输机离境;其二经上海海空口岸;其三由香港出海。上述供述一旦核实,将为全盘摧毁网络提供“钥匙”。谭友林遂令反复校核口供,筹划围歼与堵截路线,强调尽量活捉,以便获取更上层线索。
多部门协同推进下,两支小队相继瓦解。除两名顽抗者就地击毙外,其余悉数被擒。复核审讯表明,各人证词与李军英供述基本吻合。与此同时,化名“文世杰”的张载文提供关键情报:六天前与驻日美方机构有过电联,按规定每七日需复电一次,眼下仅剩最后一天。指挥部立即决策“放长线,钓大鱼”——借敌对我全歼不知情之隙,诱使美机进入预设空域,伺机将其击落。
第七日,俘获特务牛松林以张载文名义用台复电,按指示编发“合逻辑”的战果与困难。美方未觉异样,催促其“速返”汇报。牛松林旋即回电称:东南沿海戒严,无法经上海与香港撤离,申请美方派机实施“空取”。驻日机构迅速应允。东北反特联合指挥部择定伏击空域与简易起落点,诱使对方按“预报坐标”进入杀伤圈。
严寒中,部队完成对空火力展开与伪装。先至的是一架美军运输机,在目标上空盘旋后投下大包裹与两份命令即离去。第一份为嘉奖文书,意义有限;第二份详述“空取”流程:先试飞,后实施。可见对方警觉性甚高。谭友林权衡战机,决定试飞阶段即行击落,避免生变。其后敌机第二次返场,投下照明弹并由北向南俯冲,至距场约二百米高度时,我方高射炮、重轻机枪同时开火,将其击中。飞机撞树后解体坠落,四人中两死两生,还未来得及销毁证物,现场即被控制。
起初,两名幸存者坚称自己是民航公司雇员,执行赴朝鲜接运飞行员的任务,因迷航误入中国。然而,随着此前被捕特务的指认与证据链完善,谎言难以为继。一人供述自己为约翰·唐奈,年仅二十二岁、耶鲁高材生,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此次渗透行动的策划与主导者,“文队”亦由其亲定。另一人理查德·费克图,波士顿大学应届毕业生,同为CIA遴选成员,在行动中扮演从犯。
我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唐奈以首犯论处,判处无期徒刑;费克图以情节较轻,判二十年徒刑。案件通过国际媒体公布后,美国政府却公开否认两人与CIA的关系,宣称他们为驻日陆军部的文职人员,且已于1952年某次飞行中“牺牲”。这种“硬拗”不仅推诿责任,亦试图将问题引向中方“非法囚禁”。但在证据确凿与口供完整的现实面前,该说辞难以自圆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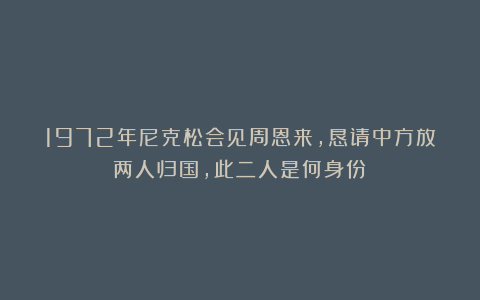
美国舆论压力与外交攻势并举,甚至一度将此案与朝鲜战俘问题强行捆绑,扬言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周恩来明确表态:审判美国间谍乃中国内政,须依中国法律办事;对危害中国安全的外侨依法判刑,同时对改造表现好的个体可作区分对待。美国又转以联合国秘书长名义斡旋,要求“人道释放”。1955年,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坚持独立自主处理的原则,同时在主权与法律框架下表示允许间谍家属来华探视。
此举一石数鸟:既给了联合国方面必要体面,也以事实反击美国媒体对“中国虐囚”的抹黑。美方起初以各种借口阻挠家属来华,但拦不住当事家庭的意愿。其后,两人的亲属先后到访,见到被拘者接受文化与政治学习,有专人谈心疏导,起居有序,家属总体表示安心。与此同时,美军内部也曾构想以特种兵营救的极端方案,但因风险过高被终止。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多轮会谈中持续以“战俘”叙事施压,试图模糊两人与CIA的真实关系。周恩来直言,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战俘,而是特务,性质截然不同。由于理由不足,美方的外交攻势始终未获实质进展。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出现突破;结合两人家属困境与健康因素,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先后予以释放,成为推动双方关系解冻的具体举措之一。回国后,唐奈重返校园,于哈佛攻读法学博士,后在美国某州担任律师并晋任法官,专办青少年案件,生活步入正轨。1983年,他携妻子与孩子重访中国,受到礼遇,游历多座城市,颇具象征意义。费克图因罪责较轻,获释更早;返美后先任假释官,便于照拂双亲,继而回到母校波士顿大学出任体育事务副主任,人生轨迹也渐趋平稳。
回望此案,从长白山密林中的微弱电波,到严寒雪野里的伏击火网,再到国际舆论与多轮斡旋,它既是新中国早期反间斗争的缩影,也是大国博弈、人道议题与外交策略交织的生动案例。最终的处理,既守住了法律与主权底线,也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开启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