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土匪啊,你别说现在,放在上个世纪,想想都让人脊背发凉。可现实就这么反转:1998年,程莲珍咽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谁还记得,这个和街坊邻里乐呵呵唠嗑的老太太,几乎曾经搅动过贵阳半城风雨?有些人,年轻时风头无俩,老来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传奇转身,平平淡淡。
程莲珍出生的那个地方,说好听点是大山深处,说直白点,那真是进了冬天炊烟都看不大清。小村不大,倒真是盛产好看姑娘,布依女孩自小皮实可人,倔劲里透点灵气。程莲珍,美得又秀气又带点辣,小时候跟着家人下地干点活儿,一抬头总能惹来小伙子胆怯瞄一眼。这事儿传开可快了,媒人嘴皮子都磨破,说得谁家都不想把自家小子落在外头。
可程莲珍不着急。她心里头有点拧巴——她不甘心一辈子窝村里,做个柴米油盐的小妇人。每次有新鲜人进村,或者看到点外来人带的奇物,她总是驻足多看两眼。也许谁的心,没憋过“外边世界会不会比这儿大得多”的小念头?
美貌总是会惹事,尤其是在那种闭塞的小地方。没隔两年,贵阳有个风头正劲的大户,陈正明,亲自拎着礼盒上山。听说陈家是书香门第,陈正明自己还那会儿新式教育的大学生。这在程莲珍同龄姑娘里,妥妥的云端人物。更关键是,他瞅见程莲珍,脚都挪不动。人总爱冲着好看的去,陈正明,算是把“冲动”两个字诠释得明明白白。
两家鸡飞狗跳地折腾了小半年,最后陈正明高高兴兴娶回家,程莲珍也算是攀了高枝,穿金戴银,小日子一下子“豊”了起来。按理说,换了别人,这辈子差不多就对了。可你看命运,偏不讲道理。
新婚蜜月没熬多久,两口子恩爱得天知地知,可世事就是怕“意外”二字。大概结婚不过五年,家里突然天塌地陷——陈正明竟然病了。头疼发热,居然拖得人不人鬼不鬼地离了开。程莲珍真是哭断肠,从盈门福气到守寡,转手就是一夜。
关键是,陈正明一走,家里五间大屋、几亩好田地,都显得扎眼。明里暗里,亲戚们打小算盘,土狗流氓都闻着气味围上来,陈家大宅窗户夜里吱哇乱响。程莲珍守寡带娃,亲戚们那脸,翻得比贵州六月天还快,连枪都开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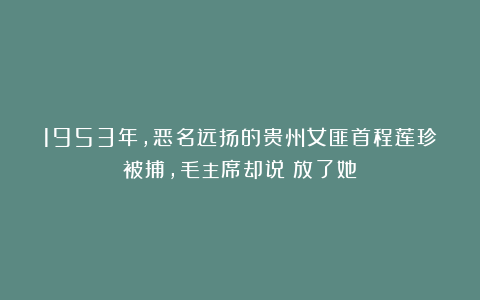
你说她能坐得住么?她还真就坐不住。一口气咽在心头,程莲珍豁出去了。她学会码枪上膛,骑马一身漂亮布衣,胯下马嘶、手带双枪,恍恍乎幼年女儿变成绿林女豪。第一次,有人悄摸着来捣乱,等不到天亮就被她端着枪赶回了老家。陈家门前再没人敢撒野——此时的程莲珍,贵阳几条街的浪子都要绕道走。
可再硬气的寡妇,也有软弱的时候。女人终究不铁,尤其是孩子饿了病了,夜里冷风灌得心发虚。程莲珍盘算着:“总不能就这么熬吧?总要找个靠山。”县城里有个军官,罗家兄弟,一个营长、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罗绍凡,其实早对程莲珍有心。消息灵通的人,总归会找到突破口。几个酒场饭局,人情世故推推搡搡,几句试探的闲话,风言风语架到一起,程莲珍也许就认了,却没想这一步,将来却……唉,一步走错,翻到难解的棋局里。
解放那年,贵阳城头变幻大王旗,程莲珍本也能金盆洗手。可惜罗家兄弟,尤其那个军官罗绍铨,心里还存着“国民党”残梦,怀着点不甘沉浮。解放军大军压境,蒋介石早坐船漂到台湾去了,可留在大陆的,都是放不下的命。
这段日子,程莲珍被裹挟着上山下乡,跟着罗氏兄弟做了“匪首”。讲是“保财保命”,其实也不过是别人权宜的棋子,好日子成了押宝。每次瞒天过海,每次想力挽狂澜,都像是鸡蛋碰石头。最后他们哪能斗得过洪水一样的大部队?一群残兵遁进深山老林,只剩稀稀落落百十来号人,连喝两口白水都难。
事情败露得快,程莲珍落网那年已经两鬓透白,显不出多少英气了。公安把她带走,究竟怎么处置?这边大伙儿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拍板。案牍堆成小山,谁都说她“罪大恶极”,可伤心人终究是人,有过辉煌,也有过绝望。
这事最后还惊动了毛主席。主席看得明白,他翻了翻材料,只说了一句话,“别杀,放了她。”理由?“古时候,诸葛亮能七擒孟获,我们也能学着点。”你说妙不妙?有些豪迈,有些慈悲。程莲珍这一劫,算是死里逃生。
人是心软的动物。一回头,程莲珍像换了个人。她低头思量,也许过去做错了什么,可国家给了一条出路。这几年,她挨家挨户地敲门,劝那些还在山里打游击的小头目:“世道都变了,何必再苦?”她不背枪了,只戴顶旧草帽,嗓门亮亮地讲“党和政府有多好”,孩子们围着她叫阿姨。半个月没过去,就劝下二十来号好汉,倒戈归降。剩下几位头铁的,也都没能再成气候。
到这里,这出“大女主剧”算是拍完了。程莲珍后来成了村里的老人,街口遇上,只是个慈眉善目的糟老太太。谁还能记得、谁还好意思提当年?
咱中国人讲究将错就错,也讲究回头是岸。人,谁一辈子不走点弯路?程莲珍倒霉也好,侥幸也罢,最后那些个风浪都做了旧梦。有人信命,有人认命;有人一辈子在命运里流转,兜兜转转,终归还是吹了灯,洗了手。
今天回头琢磨,她那时夜里失眠,会不会也悄悄问自己一句:“老天爷,这条道,到底是对是错?”我们旁人当然说不清。故事到这,也就差不多了。谁说传奇只能一边倒地风光到底?我看,平淡收场,也挺对得起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