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进京,这本该是件风光喜事。可郑洞国刚要带着一家老小收拾行李,家里却突然起了波澜——他身边的女人,陈碧莲,冷冷丢了一句:“你去你的吧,我就在上海不动。”就这么几个字,倒比当年枪林弹雨还让他心里拔凉。家里历来和和顺顺的陈碧莲,头一回这样摆明了跟他“赌性子”,郑洞国有点懵,也有点无奈。
其实,要说人生顺遂,大多数时候都绕不开曲曲折折——哪有都如意的事?陈碧莲不是一块任人搓圆捏扁的豆腐,她就是那种越是被劝越是要顶两句的性子。上海于她,不只是个落脚的城,更是熟悉的巷子、庙口晨市、窗外长街上摩肩擦踵的人声。郑洞国刚想了想“非她不行”的理由,却发现自己除了男人的自信,还真没别的压服她的把握。
他妥协了,留了陈碧莲在上海,自己孤身去了北京赴任。说出去是顾全家庭,其实也是心有一丝酸楚。可人世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往前走,家里的人却忽然不跟了。郑洞国大概也没料到,就这张不舍的离别票据,一年后会变成真正的诀别——陈碧莲写来一纸离婚信。
他盯着那封信,仿佛有一阵风横扫进了心口。陈碧莲从没说过缘由,就这么干脆地要断。他始终想不通,夫妻这些年下来好歹有份情分,哪怕有口气,怎么也不至于一句话就说散了。可人心如水,变了就是变了,连追问的力气也没了。郑洞国最后还是签了字,这一笔划下去,算是告别了自己两次婚姻的峥嵘起伏。
回头寻思,他郑洞国这一生,命里结总比解多。湖南人出了名地要强,小时候却一点自主都没有。父母早就替他定了娃娃亲,同村的覃腊娥大他好几岁,从没读过一天书。可老郑家觉得,年纪大能照顾人,识字不识字都无所谓。小郑还懵懂着,家里什么都作主,那年月女人本就是要守着厨房、织着麻线过一辈子的。
要说新旧交替,郑洞国也是早开眼的人,军校、革命、自由恋爱这些词不陌生。可是什么时候变呢?家里那种根深蒂固的安排,不是三言两语推得开的。他自忖不喜欢这桩包办婚姻,却说到底还是安安分分地对待覃腊娥。参军了也不在外头胡来,挂念着家里那口人,想着早晚要接乡下的亲人进城换个生活。
命运翻篇没有打招呼,他没等到团聚,等来得竟是噩耗。覃腊娥在他外头打仗的日子染上风寒,没能熬过。郑洞国那年正得意,脱下军服刚回家,跟大哥揣了满心好消息。可大哥反复地叼着烟,半天不开口——那烟灰敲打在桌上噼啪的响,好像一下一下打在他心口。等真捅破窗户纸,郑洞国眼前一黑,“砰”地栽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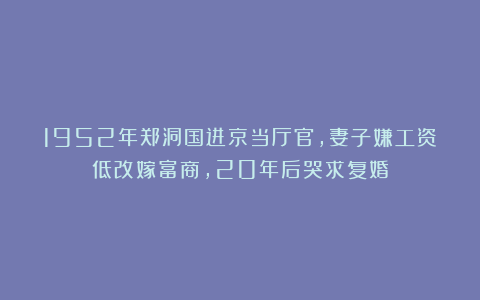
咬着牙把家事办完,他没想到,没出几个月,父亲又在回乡途中遇了贼人,命也丢了。从此,郑家老小就这样七零八落,他也把一腔温情倒进了部队。那几年他像是不要命的人,在枪火纷飞中混成了骨干。也不知是杜聿明看重他,还是命运补偿,郑洞国挺进了上层。
抗战那些年,他是硬骨头军官,有几次血战下来差点搭进去老命。偏偏命里还就有感情的牵绊,在最风光那会儿,门当户对的陈碧莲闯入了他的视野。她十七岁,身上那份不染尘埃的清气,郑洞国心知肚明,这和乡下女人不一样,带着新时代的样子。
两人最初见面也没啥轰轰烈烈,就是亲戚家的一场闲坐,陈碧莲笑起来小巧一捂嘴,郑洞国那点刚强顿时软了三分。周围是那么多老太太媒人瞅着捧着,都知道这小姑娘家世摆那,知书达理,却不任性作派。郑洞国头回感受那种“被人惦记”的味道——年轻就是不懂得轻重,几句问候便暖进心里。
好日子总是短。郑洞国前线打仗,陈碧莲常常赶火车千里来见,咬咬牙挤出几天团圆。她不像老一辈女人只知在家守着,跑到前线送棉衣,筹募受伤士兵的补贴——那股子劲头,连他都暗暗吃惊。这事很快传了开,军中的副官、连长们也被带动得捐款,弄得整个营区都说“郑团长娶了个心肠好的好女人”。
可夫妻间的考验,哪里是互相捧场那么简单?1943年要远征印度,军令一下,说走就走,对方却是天地茫茫。郑洞国习惯了离别,可那回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陈碧莲该流的泪倒没少,送行那天却咬紧牙关往他行李里塞东西:毛巾、家书、艾草,一样不落。等真要冲着雪山去的那一刻,他才明白,身后那道影子究竟多重。
战争过后,两人终于在上海安了家。说来也是运气,郑洞国战功在身,落了个副司令的清闲差事。陈碧莲喜欢上海,不全是因为舒适——更像是一种自己能主事的自信。这个城市,半数人都在做发财梦。陈碧莲起先很克制,见多了身边阔太们的张扬、争抢、排场,也渐渐动了心。女人嘛,谁还没几分虚荣?
但国民党局势说变就变。解放军来了,郑洞国退了下来,维持着一份规矩而不奢华的日子。陈碧莲却有点不高兴了——上海的生活开销大,老郑的工资在北京是厅官牌面,在魔都算不得什么。她重又见识那些身价万金的富商,有人追求,也自然有人承欢。这样的局面,到了1953年终于彻底撕开了裂口——她决定离婚,要换过别的生活。
说“工资不够花”,其实也未必全是钱的事。夫妻本就是两条平行轨道,彼此越来越看不懂,那就分开各自安好。郑洞国没挽留,干净利落。陈碧莲改嫁富商,摆脱了厅官夫人的身份,日子一时风光。可后来风水轮流转,富商进了监狱,家产查封,上海滩的繁华像转身就没听见的一场热闹。那时,郑洞国的生活却稳稳当当,波澜不惊。
日子一晃二十年。陈碧莲无路可走,哀哀求见前夫,要复婚。郑洞国这时候已另有新伴侣,早过惯了安分日子,他不再动摇。可这么多年夫妻旧情,终归斩不断羁绊。他资助陈碧莲些钱,还安排她找了个差事。孙子孙女见她,还喊她一声“上海奶奶”。有些恩怨,到最后不是仇人,也不是爱人,只剩下岁月赠的一点温情和和解。
到头来,这一段段婚姻翻来覆去,究竟是宿命,还是时代?人生许多道别,往往都没想象的那么“彻底”。陈碧莲那个夜晚,会不会后悔当初说不去北京?郑洞国有时也会想,如果咬咬牙带着她北上,生活是不是会不同?可惜故事就像老上海的雨,明明昨天淋得透湿,今日早晨又有新的太阳。人各有路,半生潮落潮起,谁也说不清,到底何为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