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网络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请悉知。
李克农那天进门的时候,没打招呼,也没寒暄,直截了当地看着粟裕问了句:“我儿子是不是死在前线了?”屋里顿时安静得能听见风吹窗棂的响声。
粟裕正低头喝水,杯子在手里顿了一下,刚想说话,李克农又跟了一句:“别绕弯子,我受得住。”
这不是试探,是一个父亲压了太久的情绪。
李伦,这个从小被他们一家当成希望来培养的儿子,自打去解放舟山群岛那边打仗,杳无音信。
李克农和赵瑛这段时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稳。
赵瑛一句话都不敢说出口,但眼圈天天红着。
李克农心里憋着火,可又不能乱问,直到听说粟裕回了北京,他才赶紧去找人。
说到李伦,这孩子命硬。1927年,赵瑛那会儿肚子里还怀着他,白色恐怖最凶的时候,李克农被通缉了,躲到小王庄。
赵瑛挺着肚子,天黑下雨也不管,雇了条船、踩着泥巴路,跑了四公里去报信。
结果赶得刚好,李克农他们提前转移,才没被抓。
李伦还没出生,就已经救了全家一命。
小时候李伦没啥特别的,唯一的事儿就是盼着父亲回家。
后来搬到延安,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他在延安大学附中的时候,学生们讨论问题,他想发言,结果他姐李宁插了句:“他还不是党员呢。”邓发那时候在旁边听见了,笑着说:“没事儿,让这个党外人士说两句。”这事儿传出去后,大家都拿李伦开玩笑,说李克农家出了个“党外人士”。
李克农听了,脸都拉下来了,马上找儿子谈话,说:“你是党的孩子,不能真把自己当圈外人。”
李伦没说啥,点头听着。
第二年,他就主动申请参军,去抗大报到。
那年,他才16岁。
训练累得不行,但他从不叫苦。
后来炮兵学校一成立,他就转过去学技术,成了咱们炮兵系统最早的一批人。
抗战胜利后,他分到晋绥野战军,干过榴弹炮团的副营长,还守过张家口车站。
打过孟良崮、石家庄,也见过不少生死场面。
可就是这样一个战场上的老兵,回到部队以后,居然没给家里写一封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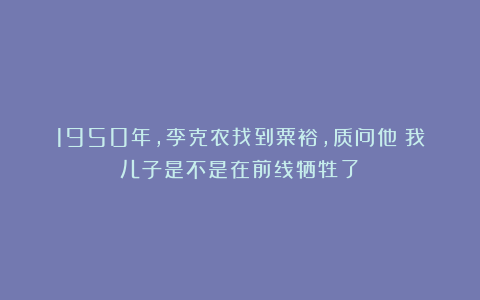
但他家人等得心焦。
赵瑛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跟李克农说:“你说他是不是出事了?”李克农没吭声,抽了一支烟,第二天就去找粟裕。
粟裕那边也懵了。
他知道李伦去了舟山,但前线情况他也不是事事都掌握。
被李克农问急了,他也不敢乱答,只说:“我让人查查,查到了第一时间告诉你。”后来消息来了,说李伦还在,只是一直在转战,实在抽不开身。
粟裕松了口气,马上找了陈锐霆,让他去把李伦叫过来,当场批评了他:“你再忙,也要给家里报个平安。”
李伦听了,脸都红了,赶紧写了封信回家。
那封信赵瑛收到了,哭了一场。
李克农没说话,把信折好放进抽屉,之后谁也没再提这事。
李伦后来又被派去了朝鲜,命令来得急,他媳妇刚生完孩子,他连孩子面都没摸一把,只隔着医院的玻璃窗看了一眼就走了。
等他回来,孩子都能跑了。
1955年,他被授予少校军衔,几十年后晋升为中将。
等到2018年住院的时候,91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医院里的人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这条命,是党给的。”
2019年夏天,他去世了。
火化那天,赵瑛已经走了几年,李克农也早就走了。
送他的人不多,熟悉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后来有人提起他,说这人一辈子没什么大新闻,就是老老实实干了几十年,打了不少仗,没留名。
他的女儿在悼念会上说了一句:“他走得安稳,这辈子他没欠谁。”
参考资料:
《李克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粟裕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解放战争纪实·华东篇》,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渡江战役卷》,军事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