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秋,湖南会同的枫木村,空气静悄悄的,夜里也并没什么声响,但屋里的人却彻夜未眠。十九岁的青年,屋外停着些许落叶,好像映着他的心情。他在书桌旁摇了摇头,写了些什么,留下几个梨子,一转身出了门,从此背起书包,消失在乡邻的记忆里。谁会想到,这一去连影子都没再回来过?故乡和亲人就这样被他丢在了身后,夜色遮不住那点点牵挂。
这日的决定显得毫不壮烈。母亲梁老太太还在屋里忙碌,不过豆大的泪却早已洒满了炕头。儿子没和她明讲,只是嘱咐了几句,就像去隔壁地里干活一样平常。也可能她压根没想到那声再见会这么漫长。
多年后,1949年的秋天,战事已定,南京的街巷还是一如既往地车水马龙。那天,梁老太太家门外来了几位解放军战士,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战士们兴冲冲地说:“大娘,粟司令让我们来接您去南京享福!”这话头极冲,稍微有点失控。她一愣,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那个没回过家的小儿子?当即跌坐屋檐下,哭得像个泪人。
情景多少有点让人心酸,那几个小伙子嘴角噙着笑,眼眶却发红。战士们递上包袱,说粟司令牵挂家里,说他念念不忘那一桌饭和旧木椅。他们不太会说客气话,话说得直白。母亲还是问了一句,儿子是怎么活下来的?这问题没人愿意多讲。死亡和别离,太多了。济济一堂都站着无数搬家、赴任和无名的别离。粟司令只是又一个漂泊游子的缩影,只不过他多了份大人物的荣光。
粟裕,这个名字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反复提及。但鲜有人会想到,在战争的巨大声浪之外,他最怕的,其实还是夜深人静时的思念。他参加革命后,整整二十三年没见母亲。二十三年,让人讲话都得喘口气。母亲把他好像看青蛙一样看着,想说话,哑口。儿子连话都说得结巴,唯恐那泪水掉下来给别人看了去。
有人又问,这将军是不是铁石心肠?其实也不是。解放军部队渡江以前,陈毅和粟裕并肩坐着闲聊,说开国不易说家国情怀,其实也就是唏嘘唠唠家常。陈毅一句话问出口,家里老人还想你呢,你不想她吗?粟裕没答茬,低头不语。陈毅懂,他和粟裕一样,也许有太多难以言说的愧疚。那个年代,不是谁都能理直气壮地团圆。
真正让粟裕情绪彻底崩溃的,是在上海读书的侄子。他天天翻报纸,忽然哪天看见一个熟面孔,激动得拔腿就冲进了军区找人。粟裕一看家里人还在,内心那些压着的酸楚就全都炸开了。老战友陈毅赶紧给湖南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派人协助,把老太太和大哥风风光光带到南京。这场团圆,晚了二十三年。母亲摸着儿子的额头,喊了声小名。粟裕还是纠结着,想笑又不敢笑。
母子俩在南京住了段日子。老太太最初不大适应,毕竟那地方风俗太热闹。她开口就说要回家供菩萨,嘴里念叨着担心拖累儿子。粟裕看出了意思,专门找来幅菩萨画像,供到母亲房里。老太太每天上香,也笑说南京的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家终究还是心里那个老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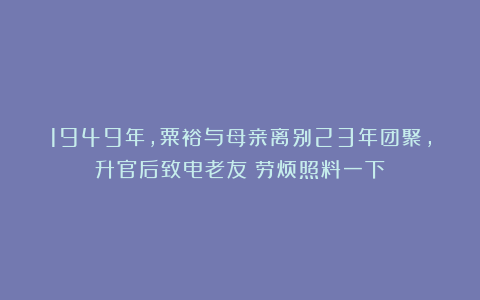
1955年,粟裕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调到北京。可是老母亲,因为久住南京不愿再跟着北上。粟裕打电话托付给战友许世友,叮嘱多去家里坐坐,许世友干脆利落,没问太细,反正只要老嫂子在南京,自己就多操点心。世上什么最难,亲情往往不讲道理。
到了八十年代,粟裕再也熬不动了,躺在病床上瞪着天花板。有人劝他养养身体,可粟裕终究还是提出要回家走走。他写信打电话,一遍遍强调非得回趟湖南,但身体早不听使唤。南京那套老宅也没什么人来扫,枫木村依旧没他的影子。1984年初,老太太已经不在了,他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六十年,没再进过那段弯路,也许是他心里唯一的遗憾。
有人说这很好也很普通。粟裕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国与家之间的拉扯。功绩无数,但家门口那条小路,他再没踩过土。到底是故乡太偏远?还是心底那点愧疚让他一直走不回去?
不见得每个游子都有真正想回去的念头。粟裕当初离开的时候,真想好了要漂泊一生吗?大概率只是觉得读书救国比种田有希望罢了,哪里会想到几十年后落了尘埃的门槛还等着他?
有人说革命牺牲太大,有人说家国本就冲突。不过旧社会多离散,本就没人能双全。南征北战的年代,也许粟裕不是最苦的那个,只是他的故事更容易被记住罢了。
南京那年,老太太怀里悄悄揣着几颗带来没吃完的橘子。见面那晚,她还塞给粟裕两个,不咸不淡地说是家里的老树摘的。粟裕拿在手里,愣是没舍得吃,后来都烂在衣兜里。谁也说不清,是他舍不得那味道,还是觉得那心结根本解不开。
周围多少人家早已断了音讯。有人熬着,有人早早服软了。粟裕算是幸运的,不过幸运也有代价。
粟裕死后,家乡人又提起他。有人说他是枫木村的有出息的孩子,有人只记得当年那几个梨子。其实没人能明白,六十年不归,梨怎么会没烂呢?
现实有时矛盾得离谱。粟裕或许能打胜仗,却永远也没办法在母亲面前喘口完整的气。他做出的选择和牺牲,不是旁观者一两句就能解释清楚的。也有人觉得,他彷徨失措,最后还是败在了情感面前。可实际也许正相反,他赢得所有,最后只剩下一点遗憾。多不多见?也就那样。
家、国、命运、归途,每个人念叨都是一大把道理。该不该回家,念不念亲人,谁能有准确答案?粟裕的故事并不稀罕。只是更深刻罢了。
这情形总让人想起自己。也许谁都有那么一两个想见却永远见不到的人。至于这点遗憾值不值,谁说得明白?枫木村的傍晚总有人走动,粟家的老屋没人再住,但梨树却还开花——也许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