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夏天,淮河岸边的信阳城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老李头蹲在浉河边的柳树下,手里的蒲扇摇得哗哗响,眼睛却死死盯着河对岸——那里尘土飞扬,隐约能听见“轰隆隆“的响声。“要变天喽…”他嘟囔着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浑浊的眼里映出南城门上那面青天白日旗在热风里蔫头耷脑的样子。谁也没想到,这座有着八千年历史的古城,马上就要迎来它最黑暗的时刻。
要说信阳这地方,那可真是块风水宝地。北边桐柏山像条青龙盘踞,南边大别山似白虎蹲守,中间淮河水哗啦啦流过,老辈人都说这是“龙虎戏珠“的好格局。春秋时候楚国在这儿修城阳城,那夯土城墙到现在还能摸着三丈高的残垣。北宋年间因为避讳皇帝名号,把“义阳“改叫“信阳“,取的就是“信义阳刚“的好兆头。城里望京门的青砖缝里都长着故事,申伯楼的飞檐上挂着传说,更别说灵山寺的晨钟暮鼓,南湾湖的渔歌唱晚,哪个不是浸透了岁月的包浆?
可这年六月,日本人的铁蹄硬生生踏碎了这份宁静。那天清晨,卖豆腐的老王刚支起摊子,就听见天上“嗡嗡“响。抬头一看,黑压压的飞机像蝗虫过境,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西大街的粮仓蹿起丈把高的火苗子。街坊们端着水盆往外冲时,城北又传来闷雷似的炮声——日军第3师团的装甲车已经碾到了眼皮底下。
这支号称“名古屋师团“的部队可不是省油的灯。1886年建师那会儿就是日军王牌,装备精良得让人眼红。这回为了拿下信阳,鬼子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天上飞机扔炸弹,地上大炮轰城墙,最缺德的是还偷偷放毒气。守城的桂军弟兄们眼睛被熏得通红,愣是攥着大刀片趴在城垛后头死扛。
要说最惨烈的还得数北门争夺战。那城门楼子是明朝嘉靖年间修的,三丈多高的城墙,青砖缝里能插进铜钱。可架不住日军调来150毫米榴弹炮,一炮接一炮往城门洞里灌。有个叫二柱子的机枪手,肠子都被弹片划出来了,硬是用绑腿把伤口一勒,抱着捷克式扫完最后一梭子。等鬼子冲上来时,就看见他背靠着炸塌的城墙根,嘴角还叼着半截卷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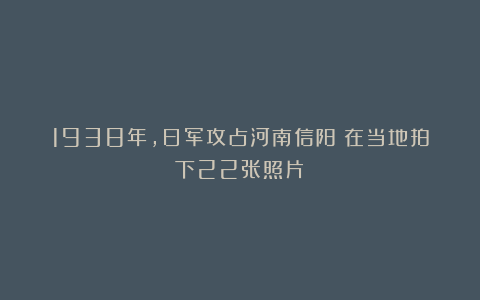
巷战打到第三天,东大街的青石板都被血水泡发了。日军94式装甲车在废墟里横冲直撞,这种三吨重的铁皮盒子在欧洲战场就是个笑话,可咱们缺枪少炮的守军拿它真没辙。有个桂军班长想了个狠招,把五颗手榴弹捆成捆,猫着腰钻到车底下拉弦。“轰“的一声响过,装甲车是趴窝了,可人也被震得七窍流血。后来清点战场时,发现他右手还死死攥着半拉铜哨——那是桂军发起冲锋的号令。
最让人揪心的是浉河大桥。守军眼看要顶不住,连长咬着牙下令炸桥。负责点火的排长老家就在河对岸,他举着火把的手直哆嗦,眼泪啪嗒啪嗒往导火索上掉。等鬼子骑兵举着马刀冲上桥面时,就听“轰隆“一声,三十米长的桥身哗啦啦塌进河里,连人带马全喂了王八。后来日军工兵架浮桥,老百姓就偷偷往河里扔铁蒺藜,气得鬼子架起机枪扫射,河面上漂的都是鱼肚子似的尸首。
等枪声彻底停下来,信阳城已经没个正形了。望京门的匾额碎成三瓣,申伯楼的飞檐塌了半边,灵山寺的菩萨像被炮弹削去了脑袋。鬼子兵举着太阳旗在废墟上蹦跶,有个戴眼镜的军官还假模假式地给小孩发糖,可转身就让人把城隍庙的铜香炉搬上了卡车。最损的是他们专门拍了照片登报,把满地焦土说成是“皇军伟业“,把杀人放火美化成“建立王道乐土“。
不过这帮畜生也没讨着好。战后统计,第3师团在信阳折了2500多号人,有个幸存的日本老兵在日记里写:“支那军的抵抗像桐柏山的石头一样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话说得在理,咱们守城的桂军虽然装备差,可那股子血性就跟大别山的松树似的——宁折不弯!
如今站在南湾湖边上,还能看见当年炮弹炸出来的深坑,现在里头长满了芦苇,风一吹就沙沙响,像是给牺牲的将士们唱安魂曲。信阳城早就重建得焕然一新,可老人们总爱指着某块老城墙说:“瞧见没,这砖缝里还嵌着弹片呢。“这话不是说给耳朵听的,是说给心里记的。
历史有时候就像浉河里的水,看着平静,底下却藏着暗流。那些血与火的故事,那些舍生忘死的身影,就像河底的鹅卵石,被时光冲刷得愈发清晰。当我们漫步在信阳的街头,看着孩子们在申伯楼下放风筝,是不是该想想:这太平日子,可是前辈们用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