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25 01:08
1936年大别山活埋的红军团长,被农妇刮腐肉救回去,他走时只留下一把勺
1936年夏天,大别山那边热得要命,石头一晒脚板都能烫破皮,山里乱七八糟的声响一大堆,知了叫得耳朵发涨。
王氏那天就是拎着个破竹篮,上山给孙子找草药,心里就一个念头,小崽儿高烧三天,再拖说不准人就没了。
她走到一片杂草边上,突然闻到一股怪味,铁锈味夹个汗腥味,还带点烂肉味。
这味道她太熟,村里杀年猪差不多就这味,她心里就咯噔一下。
人老了脚还快,她顺手把地上的烂叶子扒拉开一点,手背刚碰到土,土底下往外渗血水,颜色发黑。
再扒几下,一个人胸口就露出来了,衣服全黏在肉上,胸口一鼓一鼓,嘴边有血沫,肩章上那“团”字还看得清,身上全是飞虫。
王氏愣了半天,嘀咕一句,这怕是红军的人,别是被人埋了个半死半活在这里。
梁从学那时候其实还有点意识,人是他自己让战士半埋进土里的。
三天前打碉堡,他带着三十来个人翻悬崖,左臂先穿了洞,子弹又进了肺,战士背不动他,他自己喊着要埋,说换言之就是少拖累一批人。
战士不愿意,眼泪直挂,他骂得更狠,说要是拉拉扯扯全死光,谁去打下面的仗。
战士们最后只好照他话办,用土把他身子压住,就留了个胸口能喘气,匆匆往山那头撤。
谁都不晓得他在土里熬了几天,反正王氏刨出来的时候,人已经臭到不行了,胸口还一抽一抽。
王氏当时也纠结,她孙子在山下高烧躺床上,这个半埋的人要救,自己老命都得搭进去一点。
她嘴里骂了两句晦气,又扯着嗓子问了句,“红军不?”梁从学嘴皮在抖,声音小得听不见,只点了一下头。
王氏心里一横,反正都活了大半辈子,咽不下这口气,人活着埋土里算啥事。
她用挖草药的小铁锄一点点刨,把他从土里拽出来,手上全是烂肉黏糊糊的,她皱一下鼻子就继续干。
血糊的军装剪不开,她索性拿菜刀划,刀口一开,里面腐肉黄水全往外冒,这味道换谁都想吐。
她没工夫矫情,用袖口随便抹了一把脸,把人背到旁边猎人以前挖的个洞里,那洞里潮得很,墙上有野兽爪印。
王氏家也不远,走回去大概要小半个时辰,她一路走一路计划。
家里有个破铜锅,平时煮野菜用的,可以烧盐水;李老汉那边偷藏了点鸦片膏,说是自己牙疼用,她准备半夜摸过去刮一点。
换言之,她心里是把这事当偷鸡摸狗的活在干,嘴上却牢牢地闭着,不跟任何人提。
夜里,村里人都睡了,她摸黑敲李老汉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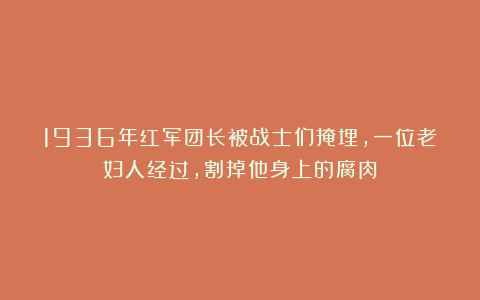
李老汉一开始骂她疯,骂声挺难听,说战乱年头,还救人,命不硬啊。
骂归骂,骂着骂着,人叹口气,还是从柜子底下摸出个小瓷盒,里头鸦片膏也不多,他又从屋梁上抖下半包三七粉,说不准以后自己也用得上,反正给出去就别惦记。
王氏接过东西,连句客套都没说,转身就走。
山洞里她把铜锅架在石头上,盐水烧开,把布条丢进去烫。
鸦片膏抹在他烂得厉害的地方,刀子一点点割掉腐肉,三七粉往里按,梁从学身子一直抖,牙咬得咯吱响。
她手一点不抖,该割就割,嘴里念叨两句,“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就算了。”说穿了,她也不晓得自己在干嘛,只是觉得人放在这儿烂掉实在太难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大概到了第十五天,梁从学能拄着树棍站起来走几步,气息还虚,不过眼睛已经亮了很多。
王氏看他这样,心里算账,孙子那边米缸见底了,就剩两块米糕。
她把米糕掰成三份,一份塞他衣兜里,一份扔进灶灰罐里藏着留给孙子,一份兑水熬成米汤,慢慢舀给他喝。
她嘴里念一句,“吃完你就走,别在这多待,省得连累人。”
梁从学那会脸还憔悴,不爱多说话,只从随身口袋里掏出一把小牛角勺,刻着“从学”两个字,边角磨得润润的,一看就是用了好多年。
他放到王氏手心,说换言之,以后谁拿着这勺找来,你就当是我回来了。
说完背起破棍就往山外走,背影有点晃,脚步却不拖。
再往后事情就乱起来了。
37年鬼子往大别山一带疯狂扫荡,村里人说着说着就跑光一大半。
王氏把孙子塞进猪槽,让人顺河推走,还交代一句,“你要活着漂哪儿是哪儿,有口饭吃就成。”她自己跌跌撞撞回村口,没来得及躲,机枪一梭子扫过来,半个肩膀直接削掉,人倒在地上,旁边泥水都成了红色。
梁从学那时候已经在别处带兵打仗,听说老百姓被杀,急得要疯,连夜带队往回赶,人还没到,村已经烧得就剩黑木桩。
他在灰堆里翻了好久,只翻到那把牛角勺,勺边上裂了一小口,应该是火烤出来的裂纹。
他没多说什么,把牛角勺削平,一半镶进自己的手枪握把,每打一仗就在枪托上刻一道沟。
战士们还笑,说团长这枪有点怪,他也不解释,只闷头刻。
到1945年秋天,沟槽上去了三十七道,手枪都磨得发亮。
那年他带几个人悄悄回到那片山洼,找了个不算太低的坡,挖了坑,把枪和剩下半截勺子埋在一起,旁边种下三十七棵野山楂树苗,手上泥巴全抹不开。
当地老百姓走过,见这片山楂也说不清咋来的,只知道年年七月,果子红得很,酸得牙发软,小娃娃抢着采,老人坐树下乘凉,谁也说不准那下面到底压着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