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 年的北京,市场上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百姓拿着新发行的 ‘当十大钱’ 去买米,店主却摇头拒收,只认旧制钱。这种由清政府推出的新货币,面额是普通铜钱的十倍,实际购买力却直线下跌 —— 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的爆发。长久以来,人们多认为这场通胀是太平天国战乱所致,但翻开历史细节会发现,早在道光年间,一根名为 ‘白银短缺’ 的引线就已被点燃。
白银断供:从全球萧条到中国困境
19 世纪初的拉丁美洲,一场独立战争正在席卷大陆。这场战争摧毁了西班牙在南美建立的白银帝国,导致全球白银产量锐减 —— 而当时的中国,早已成为 ‘白银依赖国’。自明代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 后,白银成为官方货币,其供应几乎全靠日本和南美输入。南美白银断供,如同掐断了中国经济的 ‘血管’。
数据显示,1808 年中国银钱比价突破 1040 文(1 两白银兑换 1040 文铜钱),到 1849 年竟飙升至 2355 文,40 年间涨幅超过 126%。对百姓而言,这意味着税负翻倍:过去卖 3 斗米能缴 1 亩地的税,如今要卖 6 斗才够。江苏巡抚陶澍在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小民以钱易银,亏折甚苦,催征更难’,连富庶的江浙地区都出现欠税数百万两的情况。
更糟的是,英国等西方国家也因白银短缺盯上了中国。为弥补贸易逆差,他们将鸦片作为 ‘替代白银’ 输入中国。1810-1829 年,仅鸦片输华量就超过 10000 箱,直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面是白银进不来,一面是白银往外流,道光年间的中国经济如同被双重挤压的海绵,逐渐干瘪 —— 史学界称之为 ‘道光萧条’。
鸦片战争:给疲弱财政补了一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给本就拮据的清政府财政致命一击。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争,军费开支高达 2500 万两,加上战后 1470 万两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 1842 年全年财政收入的近八成。为了凑钱,道光帝不得不动用国库 ‘家底’—— 战前户部存银还有 1758 万两,战后仅剩 993 万两,几乎腰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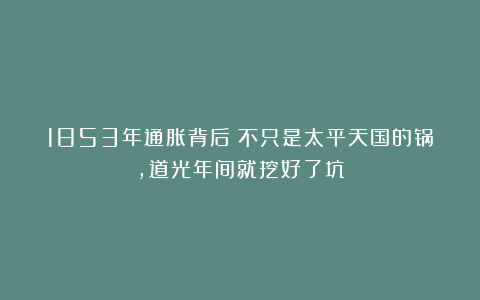
战争还破坏了经济循环。英军在江浙战场抢掠官府库银、勒索富商,仅慈溪一地就强索 40 万两,导致商人纳税能力骤降;五口通商后,鸦片输入更凶,19 世纪 40 年代年均输华超 4 万箱,每年吸走中国白银 1.5 亿元。银贵钱贱的势头愈发凶猛,华北地区银价涨幅超过 70%,农民 ‘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连军队都开始拒绝接受掺有制钱的军饷。
此时的清政府陷入两难:铸钱吧,银价太高导致铸造成本是面额的 3-4 倍,各省纷纷停铸;征税吧,百姓已无钱可缴,1849-1850 年各省欠缴京饷达 900 余万两。户部尚书卓秉恬在奏折中坦言:’部库支绌日甚,应用款项所短实多’,国家财政已到了 ‘拆东墙补西墙’ 的地步。
太平天国: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851 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成为引爆危机的导火索。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军费开支激增:1851-1853 年累计达 2963 万两,而此时户部存银最多时仅 12 万两,连一场中等战役都支撑不起。就像一个透支的家庭遇到突发开支,清政府只能选择最无奈的办法 —— 印钱。
1853 年,咸丰帝批准发行 ‘当十大钱’ 和纸币 ‘官票’。这些新货币材质粗劣,面额虚高:当十大钱实际重量仅为普通铜钱的 3 倍,却要当 10 个用;纸币没有足够白银背书,全靠官府强制流通。起初,浙江等地的当十大钱还能勉强流通,但随着发行量激增,不到两年就出现 ‘市肆交易,半用大钱则物价骤涨’ 的局面。
北京城内,粮价因大钱泛滥一日三涨,而城外数十里因坚持用旧制钱,’诸物价平,民情安乐’,形成鲜明对比。陕西发行的铁制钱贬值更快,1857 年 1 吊铁钱仅能换 1.2 吊铜大钱,到 1859 年竟跌至数百文,几乎成了废铁。百姓宁愿以物易物,也不愿碰这些 ‘官家废纸’。
萧条与通胀:一场跨时代的连锁反应
回望这场通胀,太平天国更像是一个 ‘加速器’,而非根源。早在乾隆末期,川楚白莲教起义虽耗银 2 亿两,却因国库充盈未引发通胀;而道光萧条后,清政府已无 ‘余粮’,战乱只是让矛盾集中爆发。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当白银这个货币核心出了问题,传统财政的堤坝迟早会溃决。’
1860 年代后,随着南美白银产量恢复、洋务运动开展,这场通胀逐渐平息,但留下的教训深刻: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若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就如同在沙滩上建楼。如今,南京博物院仍珍藏着当年的 ‘当千大钱’,那粗糙的铸工和虚高的面额,仿佛在诉说一个王朝在白银短缺与战争冲击下的无奈。
这场跨越道光、咸丰两朝的经济动荡,其实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 ‘阵痛’。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因果往往藏在细节里,看似突发的危机,或许早已在数十年前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