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严凤英一生风光,却走过太多泥泞。
十五岁被软禁、怀孕被抛弃、改名逃亡、恩人娶她又离婚,直到遇到那个导演,命运才慢慢稳了。
可她真的爱过谁吗?
幼年磨难与初遇恩人
1945年,严凤英刚满十五, 安庆小城虽不大,兵荒马乱中人心难测。
她本想学戏唱曲,过个清白日子,却被一个国民党军官盯上。
那人四十出头,混成了个副营长,在当地横行惯了。
一天直接带人闯进她家,说要纳小妾,严家哪敢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人被掳走。
军官把她软禁在自家宅子后院,整整半个月,她滴水不进也不言语,装疯卖傻,白天唱,晚上哭。
军官起初没在意,以为是脾气倔,日子久了开始心烦。
老母亲见她样貌虽好却满脸煞气,心里发毛,找人算命,说她“命带凶煞,不详之人”。
没多久,军官家的马车悄悄送她出城,一封银票当作了了这桩“闹剧”。
她离开时什么都没带,连姓也改了,叫“严岱峰”,想藏住过去那段屈辱。
她一个人搭船去了南京,举目无亲,白天在小饭馆洗碗,晚上进了米高梅舞厅跳舞换饭吃。
南京那时候还算太平,小地方的姑娘来了,脸上有点戏味儿,能唱几句,就容易被记住。
1948年,甘家三少爷甘律之,去了趟米高梅舞厅。
那晚严岱峰穿了身翠绿色旗袍,在台上唱《贵妃醉酒》的小段。
甘律之一听就愣住了,戏腔纯正,咬字带味,这不像是混场子的,是真有根底,散场后他托人去问,知道她出身安庆,还学过黄梅戏,立马就来了兴致。
第二天他登门拜访,说自己在办“友艺集”,是个戏曲社团,邀请她加入。
她一开始不信,有些防备。
甘律之掏出一张邀请函,又拿出父亲甘贡三的名帖,说可以带她去见父亲学正宗京昆。
严岱峰那天晚上没睡,一夜坐在床头。 想了很久,第二天就答应了。
甘贡三是老京剧名家,退居南京郊区,一见这姑娘就说:“你嘴巴干净,有底子。”收了徒,教她唱昆曲,《牡丹亭》《长生殿》一折一折练。
她白天跟着甘律之进出剧社,晚上回宿舍苦练台步,没人逼她,她就自己逼自己。
半年后,“严岱峰”三个字在南京戏圈慢慢有了名气,成了年轻女票友里最能唱的一位。
甘律之呢,每回演出前后都亲自送她回去,风雨无阻,像个影子似的守着。
事业崛起与第一段婚姻
1951年,她回安庆了。“严岱峰”的名头没带走,带的是“严凤英”这个新名字。
这时候她已经能独挑大梁,回安庆戏团唱《柳树井》,观众场场爆满。
一次后台整理衣服,一个年轻编剧过来打招呼,说看过她南京的戏,他叫王兆乾,安庆文工团的创作员,擅写剧本,讲起戏来头头是道。
俩人第一次聊天从黄梅调讲到梨园旧事。
王兆乾嘴上没个把门的,但人干净,对戏也认真。没多久就天天来找她,一起吃饭、讨论剧本、唱小段。
外头开始有人说,王兆乾八成是看上严凤英了。
她确实心动了。干这么多年,第一次碰见一个能跟自己谈戏又不图她美貌的。
两人拍拖几个月,她怀上了孩子。
这事王兆乾知道得晚,他反应不大,脸却黑了好几天。
有一次她去南京演出,照规矩,去拜访了甘律之,还在他家吃了顿饭。
回来后王兆乾直接在后台发飙,当众甩了她一耳光,扔下一句:“你还放不下他?”
这事一传开,安庆文艺圈都轰动了。
她忍了,想好好说话,但王兆乾从此疏远,最后连电话都不接。
孩子快出生前,她托人给王兆乾发了封电报,对方只回了一句:“祝母子平安。”从此再没联系。
临产那天夜里,甘律之赶到安庆医院,守在产房门口一整晚。
孩子出生那一刻,严凤英哭了,甘律之站在窗外,一声不吭,只塞进来一个小包袱——是个银制护身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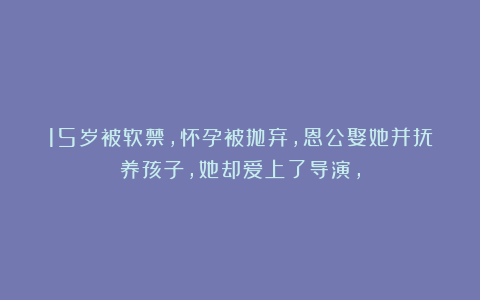
1954年,他们在北京结婚了,梅兰芳亲自证婚。孩子改名甘小亚,从此成了甘律之的儿子。
这段婚姻有点奇怪。她对甘律之有恩情,有感激,但说不上爱。
他也明白,从头到尾,他是捡了一段感情的残片,小心翼翼摆好,却永远拼不齐。
婚后甘律之把全部积蓄都拿出来,替她置办戏服、请老师、跑场子、接演出。
1955年,严凤英唱火了《天仙配》,“董永和七仙女”的唱段红遍全国。
她一夜成名,台下排长队等签名,他却开始躲着观众走。甘家早没了当年的风光,生意失败,债务缠身,连衣服都换不上一件新西装。
1956年,离婚那天,甘律之没来。
一张律师递来的信纸,把婚姻和关系都清清楚楚划清。她没掉眼泪,也没说话,只在信封角落夹了张老照片——南京米高梅舞厅前,两人穿着西装旗袍,一起站在剧社门口,笑得那么轻。
恩情婚姻与离婚
离婚后那年秋天,严凤英站在上海大世界后台,刚卸完妆。
镜子前倒映的是熟悉的轮廓,但她知道,今后再没人替她提包、递水、站在台下看整场戏。
甘律之走了,没带走孩子,只留下了一封手写信,叮嘱她好好唱戏,好好做人。
那信她藏在了行李夹层,没人知道。
婚姻不是没努力过。1954年到1956年,她连轴唱了十几部戏,团里人说她像拼命三郎。
甘律之把仅剩的钱都投进她的事业,不管衣食,只管她能不能登台。
新戏排练时,甘律之守在排练厅外,冻得直跺脚,也要看她最后一遍唱段,她知道,也心疼。
可两人之间,始终缺了点什么——不是戏,不是情,是那点最本质的吸引。
甘律之出身旧商人家庭,从小读书做账、穿洋装吃西餐,讲究规矩。
严凤英呢,从底层上来,讲江湖,爱自由,一句“这个调不对”,能跟导演吵半天,日子久了,连桌上的饭菜都变得沉默。
有一回,她回家晚了点,甘律之埋怨她不顾家。
她脱口一句:“我唱戏就得熬夜,不唱我吃啥?”那一晚,两人第一次分房睡。第二天起床,餐桌上多了一份离婚协议。
她没签,甘律之也没催。可那份纸一直搁在客厅抽屉里,谁都知道,一开就是个结局。
1956年春,终于摊开签了字。她出门,头也没回。街头杨花乱飞,一阵风刮过,裙角像戏服一样飘了起来。
她告诉自己,不回头,也别后悔。
与导演王冠亚的幸福生活
她再站到电影镜头前,是因为《王金凤》这部戏。
1956年夏天,电影制片厂筹拍新戏,严凤英被请去担纲主角。剧本是改编的民间小戏,导演叫王冠亚。
王冠亚人不高,眼神极亮,说话总慢半拍。她第一天见他,就觉得这人“拎得清”。
拍戏第一天下雨,剧组差点临时取消外景。
王冠亚坚持等,撑着伞陪她站在片场一下午。她看着他脚下的鞋湿透了,忽然笑了:“你比那些天天说戏的,靠谱。”
电影上映后,反响不错,但最让人动容的,是两人之间一点点的默契。
那时候她带着儿子王小亚生活,独立惯了,没想再婚。
王冠亚却不急,隔三差五带着点糖果玩具上门,孩子跟他玩得欢。她躲在门后看着,心里乱成一团。
有天夜里,她排练完太晚,回家时天快亮了。
门口灯还亮着,王冠亚坐在台阶上,抱着孩子睡着了。她那一刻心软了——这一家三口的画面,太稳。
婚礼没办,就简单请了几位圈内朋友。她说:“这次不是感激,也不是回报,是想过日子。”
两人婚后日子不算富裕,却踏实。
她专注舞台,他专心幕后,两人像齿轮一样配合默契。
《刘三姐》《江姐》这些经典剧目,幕后都有他策划、她唱演。外人只看风光,没人知这背后多少次熬夜、多少次争执到凌晨。
王冠亚从不干涉她唱戏,也不干涉她教孩子。每场演出结束,他第一个送来毛巾热水,等人散尽,再牵她回家。
晚饭桌上,他会说:“今天那句’你莫走’,你换了气口,好听。”
她嗯一声,低头吃饭,脸却忍不住笑。
这段婚姻,才是真正的安稳和幸福。没风浪,没眼泪,就是白天排戏、晚上回家、厨房有饭,客厅有光。
参考资料:
1. 张振华.《黄梅之路:严凤英传》.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年.
2. 安徽省戏曲研究所档案馆,《严凤英演出资料集》, 馆藏编号: AQ-1956-478.